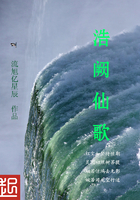中国古代贤哲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拥有的是有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认为有精神物质相互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故且谓之)第三种的东西,“浩然之气”即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它不是纯粹的物质实体,而是精神的物质,所以,它可以超越个人肉体的束缚、限囿,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沟通,相互融为一体。所以,“大丈夫”之有无穷尽的人格力量,不仅是因为它来自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根植于天地间的“正气”,故而“大丈夫”们可以从宇宙大化流行中汲取力量。又因为“浩然之气”不是纯粹的精神,而是物质的精神,所以,它才有无坚不摧的刚性,能够抵御住任何肉体的痛苦、外在的折磨、乃至死亡降临带来的悲哀和失落。文天祥正是具备了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元朝以宰相之位相劝降,被其严词拒绝;元军以肉体折磨相压制,文天祥坚强地挺住了;元军又多次以死相胁迫,文天祥毫无惧怕。他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文天祥在受到奸臣的排挤,贬官外放时,也从未动摇过其爱国爱民之心。在艰苦的囚徒生活里,也从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充分展示出其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质。这一切都衬托出大丈夫精神的崇高和可贵,也使文天祥成为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应该说,“大丈夫”精神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其在文天祥的一生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最为独特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关键之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一个人欲横流的时期,要做一个至大至刚、与天地同流的“大丈夫”实在是不易。人,唯有“无欲”则刚,唯有“无畏”则强,如何教育大众,不汲汲于个人之私利,而以国家民族大众利益为重为先,从而无私无畏,成为一个“大丈夫”,这就是今日弘扬民族精神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三,“三不朽”精神。人不仅有生,更有死。对死亡的深刻认识可以促使人们建构科学健康的人生观,并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中国传统儒家学说认为,人们是寿是夭是善终还是凶亡,为“命”所定,不可违拗之;但是,人为何而死、怎样去死则是“理”所定,是人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因此,儒者们求的是死得其时、死得其所,而不在意于生命的长短寿夭,以及生活性质上的穷与达、贫与富、贱与贵。这样一种生死观念,在文天祥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天祥对生死问题早有思考,且相当深刻。他曾经对“外王父”义阳隐士曾珏之死描绘得甚详。一日,曾珏躺在病榻上悠悠然说:“吾岂不省事哉?形神合则为人,吾形惫久矣。今腰足如断,心火益燥,神思游散,居常谓不识死,死则如是。”又说:“死生如昼夜,不足多憾。”再饮酒三口,连说三声:“吾真去矣”,“声脱口而逝”。天祥感叹道:“呜呼!阴阳魂魄,升降飞扬,气之适至,虽梦寐莫适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从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尝试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据。公去来一息,实天祥所亲见。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呜呼异哉!呜呼异哉!”《义阳逸叟曾公墓志铭》,第425页。曾氏在死亡降临时的洒脱给文天祥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作为一名儒者,天祥意识到,一个人仅仅坦然于“死”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由“死”的必至性进而为人“生”时的积极有为。文天祥写道:“人生天地间,一死非细事。识破此条贯,八九分地位。赵歧图寿藏,杜牧拟墓志。祭文潜自撰,荷锸伶常醉。此等蜕浮生,见解已不易。”《赠莆阳卓大著顺宁精舍三十韵》,第3页。天祥认为,历史上有许多人看破生死,活得极逍遥,如牡牧自己拟定墓志铭,陶渊明生前写下祭奠自己的祭文,而刘伶则常常在大醉中忘却生死,等等。不过,他们的生死观主要是受《庄子》一书中的《齐物论》、《逍遥游》篇的影响,以“生死齐一”的观念为基础,如义阳隐士曾珏的死亡态度基本上亦属此类。但这种只关注自我生死解脱的观念与作法并不完美,儒家自有“圣门大法”,学者们应该习此才对:“知生未了了,未到知死地。
原始反终,终始本一致。后来得《西铭》,精蕴发洙泗。吾体天地塞,吾气天地帅。一节非践形,终身莫继志。舜功禹顾养,参全颍锡类。伯奇令无违,申生恭不贰。圣贤当其生,无日不惴惴,彼岂不大观,何苦勤事寐?吾顺苟不亏,吾宁始无愧。”《赠莆阳卓大著顺宁精舍三十韵》,第3页。“原始返终”的观念源于《周易·系辞上》,是说万事万物皆一气所化生,都处于一种从“始”至“终”,又由“终”至“始”的永恒变化之中,显现于人之生命行程,则为“生”与“死”。所以,站在人生命的立场上看,生与死对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但从宇宙大化的角度看,则其“本一致”。既然如此,人们就可以也应该“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乐天”,即安于生死,其前提是“知命”,亦即对宇宙之理、自然之变的理性洞悉。文天祥认为,在生死的问题上,仅仅达到“乐天知命”还不够,必须进而获得张载《西铭》中的精义方为尽善尽美。张载曾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集·正蒙·乾称篇第十七》,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张子思想精髓是:在生死观上,人们应该也必须从“死”时的“乐天知命”进至“生”存中的积极有为。在人生的行程中,孜孜不倦地推行道德仁义之事,完成自我在人世间的责任,“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活着时积极有为,死时则可以无所愧怍。儒家与道家在生死观上的区别不在于人们是否能从对“死”的恐惧中超脱出来(庄子言“坐忘”,张载云“吾宁”),而在于消解了死亡恐惧之后,人们究竟是只“逍遥”(道家)抑或应该积极有为地“顺事”(儒家)?文天祥当然是一名“真儒”,他认为,只有张载对生死的看法才能使人们在摆脱死亡的痛苦之后,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无日不惴惴”,努力为民为国,建功立业,死而后已。其有诗云:“三生遭际处,一死笑谈中。赢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自叹》,第605页。天祥有如此生死观,才有后来那些可歌可泣的生死实践,而他生死观的核心则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公元前547年,叔孙豹指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人们摆脱个人肉体的限囿,实现精神上永恒的途径与方法。中国古人早就从万物的生死中悟解到人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人人都将或迟或早地面对死亡的降临。既然人们从肉体上无法达到永生,那么在精神领域能否实现不朽呢?叔孙豹认为是可以的,并提出了三条途径:崇高的品德可以使人世世代代传颂,建功立业可以让民众长久的受益,精辟的言论具有永恒的价值,故而三者都能使人超越短暂的生理生命的局限性,恒久地活在人世间,当然,这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儒家大师对这种“不朽”的观念非常赞赏,并大加发挥,孔子指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此“名”之“称”,实指人的声名传之后世。“君子”们不担心别的,只是担心死后默默无闻,追求的是逝世后仍有重大影响,事迹受到世代人传颂。在孔子看来,要“名称”,就必须有极高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生前富可敌国,人人知其声名,但死后却可能很快让人彻底遗忘,是谓朽之;一个人也许生前贫困潦倒、穷苦不堪,但只要他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幸福,那么就可能在死后声名显赫,受到人们的尊敬,是谓不朽。孔子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齐景公因无德死而“朽”了,伯夷叔齐因“仁”德死而不朽。《孟子·尽心上》中亦有言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因此,“三不朽”观念可以说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由死的观念引发出的人生观。文天祥的一生中,尤其是被俘后,对死亡的问题考虑得很多,也谈得很多,其中心旨趣正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最著名的当然是其《过零丁洋》的诗了: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诗表达了文天祥面对受元军铁骑践踏的大好河山心如刀割的悲愤之情,更阐发了他对死亡这个人世间最大的恐惧和痛苦之源的鲜明态度:任何人都难逃一死,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生前的努力奋斗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实现不朽。文天祥所作的绝笔自赞云,极力推崇“义尽仁至”,即是道德品质上的极致,此正可通往“不朽”;文天祥位及状元宰相,是为事功的不朽;而文天祥诗文皆佳,脍炙人口,读之令人血脉贲张,豪情勃发,此为言论的“不朽”。可见,文天祥以自己的心智能力、所作所为,特别是一腔热血实现了儒者“不朽”的理想,成为“三不朽”精神最真实的写照。从理论上来分析,“三不朽”精神的实质,仍然是要求人们跃出“生”的限囿,在生前就立于“死”后来观照人生,用死后的精神性、观念性的所得来促使自己放弃生前物质性的所获。
这种精神与“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的博大胸襟不同,亦与“大丈夫”精神的雄阔豪迈相异,它散发着某种悲壮的死亡气息。一般人都喜生厌死,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则为了道义可从容就死;一般人都贪图生前的物质享乐,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则可弃荣华富贵如蔽履,甘受清贫、痛苦和折磨。这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崇高追求,它可促人灵魂净化,行为端正、思想言论纯洁,使人不断升华到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文天祥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三不朽”精神的民族英雄,所以他才能够超出常人的所爱所求、所趋所避,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以无所畏惧的态度对待死亡,从而给后人树立起一块丰碑。活着的人得到的是一种精神性的鼓励,而逝去的文天祥则获得了“不朽”。从另一角度来看,“三不朽”观念实质上就是一种儒家的死亡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特色之一。儒家认“天地”有“好生之德”,万物的生长、发育,人类的生生不息,都体现着天地的本质——“仁爱”。所以,每个人都应珍惜生命,注重生前的道德修养,好好地生活,用“尽人事”来配“天德”。因此,儒者坚决反对无谓之死,反对人为地结束个人的生命,痛惜战争给芸芸众生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儒家圣贤看来,这不仅违背了人伦道德,也是对天地秩序、宇宙根本大法的亵渎。但同时孔子又有“杀身成仁”之说,孟子有“舍生取义”之论,鼓励人们为道义的实现而从容就死。这是否与儒家的生命哲学相忤格呢?非也,这种“死”法实质上与“生”是相通的。在儒者眼中,一个人若能为道义而捐躯,就可获得永生。此“死”正好是通往“生”的环节,以己之一“死”而成就万古之“生”。当文天祥吟哦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时,他完全参透了儒家生命哲学的精髓,并决心成为这种哲学观念的践履者。事实上,文天祥通过自己的肉体之死,的确换来了精神性的永生,其人其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