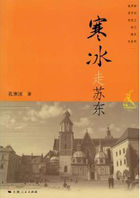李觏(1009—1059),字泰伯,宋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人,学者称其“盱江先生”。北宋中期著名思想家,一生几乎皆为“邑外草莱之民”、“南城贱民”、“建昌军草泽”,但却以政论、易论、礼论而名世,范仲淹赞其“善讲六经,辨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李觏外集卷第一·荐章四首》,《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9页。
下引该书均只注篇名。《宋元学案》称其“俊辩能文”《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88页。,朱熹则“谓李泰伯文得自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盖有取尔也”《李觏集·附录三》,第523页。。李觏科考、举茂才等皆不中,回乡讲学于盱江书院,从游者常百余人。后因范仲淹等人的大力举荐,遂入太学为直讲、说书,并曾权同管勾太学,故而“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东南士人,推以为冠”,俨然“为宋代儒宗”。所以,胡适先生云:“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黃山书社1966年版。本章不准备全面讨论李觏的思想,仅从其生死观的角度切入,以期获得一些卓越的生死智慧。生存智慧:“人事修”人之生首先显现为生命在时间中的延续、空间中的拓展,是为生存。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不仅生存在大自然里,更生存在社会的环境之内。所以,其不仅要经受自然环境形成的生存困难,还必须经受社会环境造成的生存问题。生存之不易使人们无不孜孜于寻求与建构化解生存困境的方法、途径和技巧,是谓生存的智慧。李觏因其艰难的处境,对此更是有着切肤之感,他常称自己一生“落魄不肖”,“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上孙寺丞书》,第296页。,“觏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时,上乏骐骥千里之力,下无铅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虽然用农夫之谷,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无益于人。”《上孙寺丞书》,第296页。生存的不易,当然使李觏对如何克服生存困难的智慧有着特殊的兴趣,并通过解《易》而发挥出来。作为西周初年的作品《易经》,本为筮书,以卦爻辞的演算告人以吉凶事宜。出于战国时代多人之手的《易传》则是对《易经》所做的最古的一种注解。易学专家高亨先生说:“《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第276页。这就形成了历史上解易之象数派。但《易》本身因其神秘性、抽象性、空灵性等而被认为蕴藏有深刻与丰富的义理,于是,又形成了易学史上的义理派。李觏解《易》,开宗明义即声明承自王弼黜“象数”而重“义理”的思路:“援辅嗣之注以解义”《周易大传今注》,高亨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页。,其目的是“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人事修而王道明”《删定易图序论略》,第52页。。当然,李觏与王弼以老庄玄学解《易》不同,用的是儒学义理来解《易》,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使李觏的易论充满着丰富而实用的生存智慧。
第一,“常”与“权”的关系问题。万事万物、社会国家、人生事情等无一不在有规律地变化发展之中,是谓“常”;但事物有时也会脱出常理,发生一些变异,人们顺势而动而行,是谓“权”、“宜”、“通变”。李觏说:“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矣。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履,贞厉。’谓履道尚谦,不喜处盈,而五以阳处阳,正当其位,是以危也。《丰六二》曰:‘丰其部,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谓处明动之时,爻皆以居阳位,又不应阴为美,而二以阴居阴,常于厥位,故幽而无睹,不能自发也。若夫排患解纷,量时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易论第八》,第41页。任何事物都有质的稳定性和发展变化中一定的规则在,一般而言,人们可以将使事物的这种常住性上升为常理性,认识之适应之且运用之。但是,人们在掌握此“常理”的同时,要意识到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和情况下,会脱离原有的轨道,逸出常理,发生不同寻常的变化,此时,人们再以常情常理处之,必受挫甚至失败,造成生存的困难。所以,人们应该“通变”,处之以“宜”,运用非常规的办法来适应事物的变化发展,此之谓“权”,在此意义上,“权”即是反“常”。在生存中,人们若不懂“权”变的重要性,就会陷入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不能通达,形成人生困境。所以,人们只有同时掌握两个方面,并巧妙地应用,才能处事不疑惑、不犹豫、不沮丧、不陷入祸患、不发生谬误,且获得生存之顺利与成功。所以,“度宜而行之”,“通权达变”、“量时制宜”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种生存的智慧。第二,“祸”与“福”的关系问题。有人问:文王被囚,箕子为奴,此之祸“岂其所自取哉”?意思是说,文王与箕子,古之圣贤,何以不能避祸?李觏说:有些祸患是自己不明事理而招致,有些祸患却是必不可免的。前者可用“祸患”言之,而后者却不能视为“祸患”,“是有命焉”。同样的生存灾难,在感觉上认识上却一是“祸患”、一为“有命”,其间之区分在何处呢?李觏运用易理解释云:“《节六三》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谓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违节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故无所怨咎也,此患自己招者也。《渐初六》曰:‘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谓始进而未得其位,则困于小子,穷于谤言,故曰‘小子厉有言’也。困于小子谗谬之言,未伤君子之义,故曰:‘无咎’也……《蹇六四》曰:‘往蹇来连。’谓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然得位履正,当其本实,虽遇于难,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己招,不可免者也。是有命焉,非智之过也。亦有进不违私,志在救难,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义非智者之羞也”《易论第十》,第45页。
李觏此处要说明的是,人生中实存的状态有穷与达、富与贫、平安与祸患等等,但在思想意识上,对这些实存的状况要有不同的认识,从而有不同的接受态度,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存的智慧。违背自然规律,悖逆人事之理,必招致这样或那样的祸与患,这是咎由自取,所以,就要安于所受,吸取教训,避免以后再陷入类似的灾祸之中。但若君子受小人之谗言暂时受困,则并未伤及“君子之义”,所以,人们根本不必以祸患视之,可安然而受。当人们所遇的灾难并不是自己处置不当引起,就应视其为“命”(自然)所致,既如此,也不必忧心如焚,怨声载道。更进一步言之,君子们拯斯民于水火,自然会身处困境险境甚至于死境,但这却是“君子之大义”使然,根本不是其无智所导致,更应该安然受之。所以,李觏言:“天道之变,日星循环,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数也。人事之动,情伪交错,应之而不谬者,以知其势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来,弗可辞也已。噫!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易论第十》,第46页。在此,李觏所提出的生存智慧是:万事万物变化无穷,人间祸福亦变幻莫测。人无不喜福厌祸,但需要明白的是,人间的祸患又是无可避免的。这时,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要拥有三种不同的接受方式:一是面对咎由自取的祸患,我们要从“自作自受”的角度而接受,并吸取经验教训;二是人们受外在不可控制的力量所致而陷入不可免之祸害,只需坚持做人的准则,便无可畏惧地受之;三是人们为了社会和人民的福祉身陷危难之境,那更是可从内在之道德价值的承诺而以“君子之大义非智者之羞也”受之。这就是李觏为世人提供的接受祸患的生存智慧。但是,人生于世,当然不是为承受祸患而活,关键是要消祸于未形,避难于未至,以至转祸为福。设问:
由福而祸,犹如影之随响,要如何才能消灾免祸呢?李觏云:“火之生也,一勺之胜,及其燎也,川流莫竞。
是故君子慎乎始也。《节初九》曰:‘不出户庭,无咎。’谓为节之初,将整离散而立制度也。故明于通塞,虑于险伪,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后事济而无咎也。初九曰: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谓居健之初,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易论第九》,第43页。。所谓“慎乎始”,即是调动人们思维的超前性,从事物刚开始时便预期预感预见到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以未来可能发生的状态来规范现今自我的行为,如此,祸患便可消之于未萌芽的状态。再设问:若人生中“不慎而失之”,祸患已临头,有否补救的办法呢?李觏说:在于人是“明”还是“昧”。聪明者辨别祸患早,即使偶尔处置失当,祸患已临,亦可“过而能改”;而不明事理的“昧者”总是“以智饰非”,固执己见,以至祸患临头仍不知醒悟,终则悔无可及。李觏由《易》推之云:“《讼九四》曰:‘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谓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
故其咎不在,若能反本理,变前之命,安正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也。”《易论第九》,第44页。所以,人们在生活之中,在处理问题之时,对任何事情切忌让其“贯盈”,要慎乎始,让事物的发展保持在可以把握得住的程度,否则,事发展至“极”,大祸必临头,一切悔之晚矣。第三,生存中把握“时”的重要性。“时”是时机、机会、关键点之谓,在李觏看来,人生中把握时机而行止,掌握机会而行动,抓住关键而动作,是趋吉避凶、获得生存中最佳状态的重要方法。他说:“时乎时,智才弗能违矣。先时而动者,妄也;后时而不进者,怠也。妄者过之媒,怠者功之贼也。《蹇初六》曰:‘往蹇来誉’。谓处难之始,居止之初,独见前识,睹险而止,以待其时,故往则遇蹇,来则誉也。《归妹六三》曰:‘归妹以反须,反归以娣。’谓室主犹存,而求进焉,进未值时,故有须也。不可以进,故反归待时,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时者也……《节九二》曰:‘不出门庭,凶。’谓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时之极,则遂废矣。故不出门庭,则凶也。凡此不可后时者也。”《易论第六》,第37—39页。在李觏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是:
面对事物的发展,何时可“进”何时应“退”?若具体到儒者,则是“进”而治国平天下,“退”则养亲修身颐养天年。李觏认为,是“进”还是“退”完全要看其“时”到还是未到。先时而“进”为“妄”,一定凶;后“时”而动为“怠”,必不获成功。而且,在现实的人生过程中,往往是进取之“时”易见,容易把握;而退隐之“时”难见,不易掌握。所以,李觏要求人们“见机而作”,抓住时机而有所行动。若贻误了时机,灾祸临头才想躲避,那是无法做到的。这就叫做:“危至而后求行,难可免乎?”因此,人们不应“矫枉过正”,而要“和而不同”,“身乃无患”;不要因为心中有所欲求而左盼右顾,迟疑不决,这称作“以欲而忘患,鳞属所以死于饵也”,鱼儿因贪口腹之欲,所以上了钓者之饵的当,死到临头罔然不知;人们在生活中还要远“小人”才能“远害”。在李觏看来,人之生存中虽有许多趋吉避凶的方法,最根本的还是“守正”:“若夫分有所定,义不可去,则莫若守正之为利也。《泰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谓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陂,时将大变,世将大革,而居不失其贞,动不失其应,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故无咎也。信义诚著,故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易论第六》,第37—39页。
“守正”者,即坚执儒家道德仁义不动摇。无论是“居”之停,还是“动”之行;也不管是在安居乐业之时,还是处于艰难险阻之境,人们皆要持“义”不怠,毫不动摇,这就叫“既明且哲”,足“以保其身”。所以,李觏所言之“时”,决非是要人们投机取巧,为己之利而“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而是心有所主,虽然也要见机行事,但其根本点还是要求人们持道德仁义而处世。在中国古代,因为有着深厚丰富的易学的传统,也因为人们实际上的生存之不易,“常”与“权”、“祸”与“福”,以及“时”的问题是思想家们常常讨论的对象。李觏的贡献在于:由“易”而窥“天道”——从阴阳二气来释《周易》,实开宋代易学义理派中气学一脉的先河;又由天道而人事——因为阴阳二气的变化、相摩相荡是贯之于自然与社会的至理,故而亦是《易》之核心,由《易》而察之人事,亦必以易理贯之于人世间的一切。这就是李觏生存智慧的方法论和最为关键的地方。人之生存本就在天地之间,生存之智慧本就应该取之于自然天道,因此,人们若师心自用,崇尚人为之伪,把生存的智慧皆立于自我的奇思怪想之上,必不能达到生存的佳境,必陷自己于灾难接踵而至的悲惨状况之中。所以,泰伯先生提供的生存智慧的卓著之处,不在其内容如何丰富深刻,提出了什么特别的方式和技巧,而在其观察问题的视野,在于其生存智慧所由出的方法论。生活准则:
循礼人生不唯表现为生命在客观环境中的存在,更表现为生命体在人世间的生活。生命重要的是存在,而生活中凸显的则是人之感受与感觉。若问人之生活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人在生命延续的基础上,由内在之心、性、情而产生的欲望、欲求、情感等的现实化过程。可是,人皆有生命,生命皆蕴藏心性情,心性情皆要化为人间的欲望、欲求与情感,于是,人们在人生的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为了使人人可得遂其情其欲,亦为了社会的安定和与自然的共存,人们遵守一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成为了必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人生准则一部分归入“德”,一部分则化为“礼”。泰伯先生特别地发展了儒家关于“礼”的学说。人生于世,生命是个我的,生活是个我的,其存在与感受皆表现为是“我”的而非别人的。因此,从人之内心而言,向往的是一种自在自由的、顺情适意的生活。可是人之生命在孕育时便是父母的,出生后又只能在社会中成长,由非自觉到自觉地接受着社会、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的模塑和规范,从这样一种生存性质而言,人又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在与自为。这即是个我性与类我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表现于外、显现于人之生活中,就是人渴望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之生活与“礼”之种种规则规矩规范所导致的应该如此必然这样之间的冲突。为此,有孔子倡导的人们循“礼”应该有内在之仁爱精神为基础的化解模式,也有荀子李觏从礼以养人之“性”的解决方法,其深意都是希望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些紧张与冲突。在儒学发展史上,礼乐刑政是政治学说的核心。孔子救无道之世的利器便是“克己复礼”,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归位、名实相符而正天下、治天下、平天下。但孔子敏锐地发现,典章制度、仪规准则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规范,人们若无一种内在之精神相配合,“礼”就可能成为一种“死”的毫无生气的东西,人们勉强行礼是无法真正循礼的。所以,孔子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译注·阳货篇》,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引只注篇名。“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