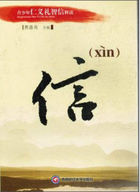毫无疑问,要在大学体制中实现多样化的想法被认为是一件好事。的确,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1983)在写美国高等教育20多年来的历史时,把机构的多样化描述成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具有“很多的道德成分”。在英格兰,政府每年给向大学拨款的机构———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写一封指导信,要求该委员会努力去发现加大学校之间的差异的各种方法。例如在2001年11月,教育国务大臣写信给该委员会说:她指望该委员会“帮助支持高等教育机构中日益增加的多样化”。政府关于英格兰高等教育的白皮书[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DES),2003]坚持认为:希望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出色地履行所有的职能,这是不合理的,每一个机构应该关注其自己所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科学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raining,DEST),2002]最近对高等教育进行考察后,强烈地肯定了多样化在增加选择与灵活性以及创建“一至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的好处。确实,很少能够发现有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把多样化作为其大学体制的一个主要目标。
最近,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已重申:它的重要的战略目标是设计这样一种资助方法,即在允许所有大学有机会发挥所有“核心功能”的同时,又鼓励它们充分发挥其中的某些功能并在这些方面做得特别好,以此形成更大的多样化。但是政府和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政策所宣称的好处,也没有明确地考察多样化的不同类型。多样化可能是指学校类型的范围(特别是由教学和研究之间活动的平衡所形成的特征),也可能是指大学在以下方面的专门化,包括本科的教学大纲或学科门类,或者是研究的领域或形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通常在英国(在其他国家常常也是一样),多样化的概念还没有扩展到质量的问题。对于所有的大学而言,至少许多标准的一种广泛的可比性(尤其是在一种最低或起点水平上的可比性),被认为对于证明其自治和垄断学位授予权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可是在美国,大学标准的多样化比在英国更能被人所接受———有些人可能会说,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比英国人更现实———这种多样化被认为有助于大学应对新的和各种类型的消费者。
尤其是部长和官员们还未解决以下问题,就是:即使当教学或商业化的联系得到鼓励时,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仍将继续成功地争取到满足其在各种活动中所需要的资金———尤其是因为在资金分配时强调“质量”,这有利于传统的关注研究的大学。当公共拨款的基数继续下降时,这样的大学不仅需要维护它们的资金来源,而且也越来越受到来自政府的告诫和鼓励,即要求大学面向社会招收更多的学生并且更加关注它们的教学。此外,资源和学生市场的压力,以及日益增多的来自政府的批评,所有这些已经迫使老大学变得有一些像新大学了,迫使老大学引进现代的管理和营销方法,迫使老大学积极地开设更多热门的与职业性的课程,迫使老大学发展与工业界的广泛合作。较新一些的大学(它们的传统特点是更为关注教和学),还有为那些其家庭或同伴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机构,它们面临来自部长们的强烈的告诫,即要求它们免去研究工作而成为优秀的教学机构,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机构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它们不可能这样做。其结果就是增加了趋同性而不是多样性。尽管各种压力倾向于导致新大学模仿老大学,但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方面各类大学是更接近中间而不是某一端①。
我们需要理解多样化是如何界定的、它打算要得到什么以及获得这种东西的最佳方式。多样化也许看似明了,但是的确好像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例如,如果我们把注意的中心局限于院校的类型,根据什么功能来把大学分类?是根据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是根据研究的类型(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是根据院校的规模?是根据大多数学生的社会阶层?或者是根据别的东西?如果扩大每所大学———也许通过合并———并且每所大学完全一样地都承担全部已被确定的功能,这样做和实现体制的多样化有关系吗?什么可以被称为大学内部的或有规划的多样化?或者院校的专门化是一个更加让人可以接受的结果?什么是多样化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采取什么方法是否很重要?
奇怪的是,来自英国的———可能还有别的地方的———大学的证据表明:大学并不很关心大学的体制是否多样化。许多大学的副校长都曾公开发表相反的言论。在寻求更多的研究经费方面和在吸引更多的本科生方面,各大学似乎非常相似———甚至前多科技术学院也是一样。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新的大学被创建以来,它们一直在追求老大学的研究基础和声望。考虑到新工党(New Labour)的高等教育政策通常支持那些注重研究和有科学基础的老大学,而不是支持那些声望低并且主要发挥对学生的教学功能的大学,也不是支持那些吸引了许多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的大学,我们也许就不会对某些情况感到奇怪了。政府给大学附加的拨款大部分是被用于研究而不是教学。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用于教学的公共资金被压缩了(一种类似的模式在其他国家中也能找到,例如澳大利亚)。因此,学习中创新的范围一度减小了,经费减少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尽管在诸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中,自费学生的增多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收入,但这往往限于数量有限的专业,诸如商务和信息技术学科等。在英国,工党政府迷上了“顶尖”或者“一流”大学,还包括公众要求牛津和剑桥扩大招生的强烈呼吁,好像在扩大招生方面做出更大成绩的其他大学根本不值得考虑,以上这种情况与政府宣称的所谓更加普遍地希望整个大学体制“现代化”、并且促进大学不同特长的发展的辞令是相悖的。新老大学都很难拒绝任何可能增加其自身收入的动议,而不管这种动议的任务是什么。当资源紧张并且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对金钱说“不”是很困难的。各大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申请到从日常经费里划出并指定用于特殊用途的公共资金,并且这种资金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财政,今后被迫需要争取这些资金,而不管这些资金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这不仅增加了大学争取资金的办事成本,而且严重妨碍了政府实施体制多样化的战略。
这并不是说,新大学的领导人在谈论多样化的时候夸夸其谈,而在实际策略上则试图模仿较有名望且偏重研究的大学。更确切地说,要求体制和机构的多样性是合乎“公共利益”的言论,但这种言论和在一种日益市场化的秩序里所要求的行动是不同的(如果学校想要生存并且更加繁荣)。各大学不可避免地选择对自身有利而不一定使公众受益的行动。这种秩序源于为了自身利益的行动和系统中各个单位———大学(尤其是大学的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各自分散的努力不是为了创建一个富有特色的“部门”,而是为了用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促进一所大学的利益(更好的声望、增加的收入、更好的教职员和学生)。这种机制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的自助,而不能创建一种受欢迎的大学体制。这些结果的本质———市场秩序、“部门”———主要表明:它们并非是有意而为的。但是,它形成了一种大学副校长所不能忽视的有推动力的结构,而不管大学副校长的公开言论怎样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