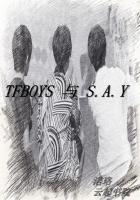癸丑年,腊月初七,宜嫁娶,乃是黄道吉日。
天公却不作美,一连几日乌云阵阵,黑云低低的压着城头,像极了暴风雪到来的前兆。
昭国宫殿中却是张灯结彩,红艳艳的喜字贴满了整个宫室,阖宫上下一派洋洋喜气,中央九重璇玑塔的祥和钟声在此时却显出一种殊异的奇诡。
鸾飞的鎏金屋檐下,听澜殿中一众宫女内监忙进忙出的团团转,人人脸上都透露着喜庆的笑颜。
腊月的冷风吹过殿堂,纷飞飘舞的重重红色绞纱帐幔后,云纹金漆的铜镜中少女乌发披散,眉眼柔和娟秀,皮肤白皙水嫩若娇花照水,稚嫩的脸庞难掩雍容华贵,如水杏眸中泛着点点娇羞涟漪,似沉浸在幸福之中。
“一梳梳到尾,二梳梳到白发齐眉,三梳梳到儿孙满地,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
“阿芜,出嫁从夫君,万不能如在昭国那般任性。”锦衣华袍的****宠溺唤着少女的乳名,手中拿着一把檀木梳子,轻柔的梳顺少女的及腰长发,慈爱的眼中满是笑意,正是聂太后。
少女听闻粉颊微红,娇嗔道:“哪有,母后惯会取笑儿臣,宁玉他,”似想到那个温润俊美身姿,她不禁唇角扬起难掩的笑意,转头对母后笑道:“宁玉他待儿臣极好,况且,儿臣哪有母后说的那般模样。”
少女撒娇般笑倒在聂太后的怀中,今日是她大喜的日子,耳旁似响起宁玉温柔话语,想着她觉得自己脸颊微微发热,又往母后怀中蹭了蹭。
“傻丫头,”聂太后笑着刮下她的鼻子,眼中忽而闪过不满:“你是昭国最尊贵的嫡长公主,又得先帝赐名高令月,即便不良与行,宁玉不过是姜国庶出的皇子,又曾在我京都做过质子,若非你执意,母后和你皇兄定不会将你嫁与他。”聂太后说着,雍容华贵的脸上泛起无奈的微薄怒意。
这时代的女子不比男儿,即便贵为公主大多也是没有名讳,只有小字,尊贵些的便多了封号,而她得父皇便赐名令月,一出生便封永安长公主,此种殊荣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高令月看一眼自己的右腿,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原因她已记不清楚,而她却非地道的古代人,她是穿越来的,与其说是穿越不如说是没有喝孟婆汤,前世的记忆记得清清楚楚,虽她从小却是个跛子,但宁玉并不嫌弃她。
高令月见母后面色,心恐母后临时变卦,上前娇笑道:“母后,儿臣会想你的。”想了想又补充道,“也会想皇兄的。”
“你啊。”聂太后宠溺笑着摇摇头。
轻碎的脚步声传来,宫婢端着红木雕花托盘,上布一精致嫁衣,恭敬的举过眉心小心呈上。
红绸艳艳,攒金线绣着高贵凤凰,明丽张扬,栩栩如生,凤眸中缀着明晃晃的夜明珠,只此一颗便可买下数座城池,这件嫁衣是宫中最好的匠人花费七日七夜,赶制而成。
高令月展臂由宫婢服侍着穿上,凤凰在身后振翅欲飞,她转身看见铜镜中少女乌发红衣,倾城的脸庞泛着粉嫩的微光。
“过来,阿芜,母后为你绾发。”聂太后手中拿着一柄金钗,笑盈盈的看着高令月招手道。
高令月敛眉顺从的缓步走到铜镜前,端庄跪坐下来,仅仅几步便是仪态万千。
高令月跪坐在铜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渐渐挽起的长发,眼角含笑,心中泛起无止境的甜蜜,从此后,她,昭国嫡长公主,髙令月便是宁玉的妻子,一生不悔。
“禀!”
殿外传来侍卫急速的脚步声,踏着慌乱的节奏。
一黄门侍卫低头跪着急急秉道:“禀太后,姜国突袭京都!已攻至城外!”
金簪哐当一声落在地上,一屋子的宫婢吓得呼啦一声跪伏在地,颤颤发抖,高令月将要绾起的头发瞬间如瀑布般散开。
聂太后霍的站起身,急急的问道:“陛下现今何在?”
“陛下亲率北屯卫军出城迎敌!现在京都城外!”
聂太后身子颤了颤,几乎站不稳,向后退了两步,一旁的宫婢将她扶住。
“南屯卫军呢?陆卫尉何在!”聂太后稳住心神急问道。
“屯卫军抵抗不得,陆卫尉失踪。”
聂太后心下一沉,帝都南北两屯卫军是皇城的最后一道防御,两军中将士均骁勇精锐,怎可被轻易攻破!
“阿芜,怕是宁玉告知的昭国关防,否则姜国兵士不可能攻至京都毫无预警!”聂太后抓着高令月的手恨恨道。
高令月站在铜镜前,一脸惨白的不可置信,她拼命的摇头,宁玉,怎么会是宁玉!她一个字也不要信!
聂太后见高令月恍惚神色,眸中闪过痛心哀色。
前方战报接二连三的送达,每一道都像是昭国的催命符。
“禀!”
“外城已被攻破!”
“禀!”
“姜军已攻至昭宫外!”
“禀!”
“陛下,陛下战死外城!”
“什么!怎会,澈儿……”
耳旁似是侍卫悲痛的声音,又似是母后震惊哀伤的声音,眼前恍惚划过几个匆忙的身影,合着杂乱的脚步声,高令月愣愣的站在铜镜前,耳旁杂乱的声音好似从遥远的地方出来,缥缈而不真切。
眼前似浮现初见那日,风吹梨花飒飒,梨花树下宁玉广袖素服对她温柔一笑,耳畔是他柔和深情的话语。
他说,“在下宁玉,幸会长公主。”
他说,“月儿,嫁给我。”
他说,“十里红妆,此生不负卿。”
高令月看着铜镜中昔日倾城容颜,如今瞬间灰败如尘埃,稚嫩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双手攥皱了红绸布,为他穿上的鲜红华美的嫁衣似无声嘲讽。
不!宁玉不可能骗她,不可能!
宫中的宫婢内监早就乱作一团,各自奔命,再顾不上礼仪等级,四处抢掠着宫中值钱物件。
天阴的愈发厉害,乌云低低的压着宫城,昭宫中四处弥漫着灭亡的窒息味道。
“皇兄呢?皇兄在哪!”
高令月拖着跛足踉跄着奔出听澜殿,随手拦着一个宫婢焦急问道。
宫婢紧抱着一包东西,面有难意急急道:“长公主,陛下驾崩了连头颅都被人割下挂在城头!您也快些逃命罢!”
说着挣脱她的阻拦,向外急急跑去。
驾崩!
皇兄,皇兄怎会……
高令月像是瞬间抽去了力气般绝望地看着宫城中瞬间破败的景象,前刻张灯结彩,下刻破败颓圮。
母后……还有母后!
至少她还有母后,高令月猛地想起,像溺水中捉到浮木般急切,一步一瘸的向母后的寝殿方向跑去,一路四处可见坍圮杂乱花架,轿子仅仅一刻的路程,可她养尊处优多年,加之跛脚,才跑了几步便已气喘吁吁。
腊月寒冷,脊背浸出的冷汗打湿嫁衣,冰冷的贴在身上冷得发抖,她扶着墙壁急喘几口,咬牙再次向聂太后寝殿跑去。
含光殿,三个字映入眼帘,她似乎看到一丝希望。
“母后,母……”高令月踉跄跑进殿中,声音卡在喉咙中。
进门处一人高的青瓷花瓶摔的粉碎,妆台矮几四处翻倒,含光殿如同遭遇洗劫般,杂乱不堪的宫殿正中房梁,红绸布悬着一名绝美的妇人,苍白雍容的脸低垂着,华丽的裙摆在风中微微飘荡,正是她的母后!
“不!不……”
高令月眼中泛起绝望的哀色,想伸手却又像是不能触碰般拼命地摇头,不住喃喃念叨着,却不知在否定什么,眼泪不停的奔涌而出,寒风中冻得脸生疼。
“月儿,”
熟悉的声音在她身后低低响起,犹如在耳边炸起的惊雷。
高令月怔怔的回过头,只见寒风中,一人月白锦袍身披黑色狐裘,少年面色温润携风而来,手中染满她亲人的鲜血,笑着向她伸出手。
他说,“月儿,我来接你了。”
“不,你不要过来!”高令月浑身颤抖的向后退急退,此刻已不想再问他什么,她害怕他将要说出的话,脚下一绊摔倒在地,手掌按在地上,花瓶的碎片插进掌心染红了白瓷。
“月儿,你怕我?”宁玉轻笑着,缓步走近高令月,低头看着她苍白的面色,唇角勾着一抹笑意,温润的神情一如初见般柔和。
高令月猛地抬头,却正撞进宁玉骤然狠厉的眼神中。
“昭国最尊贵的嫡长公主,高令月,如今也如丧家之犬般屈于人下,哼,真是可笑呵。”
一娇笑女声和着呼啸的寒风传来,声音娇弱婉转如黄莺出谷,寒风腊月颓圮破败宫闱中竟刺人心骨的阴冷。
高令月向后看去,寒风吹起窗棂呼啦作响,火红的绞绡纱幔凌乱飞舞,一鹅黄锦缎深衣的少女唇角噙笑缓步走来。
“阿阳,怎么是你?”
高令月惊呼一声,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少女,竟是她庶出的妹妹舞阳公主,可她明明和亲敕勒,怎会在这里!
舞阳公主厌恶地斜睨一眼坐在地上乌发披散的高令月,轻笑一声眸中含着复仇般的快意,柔弱无骨地轻靠在宁玉身上吐气如兰。
“我呀,自然是跟着夫君了。”
宁玉伸手拦过舞阳公主,俯视高令月清润的声音中带着刻骨的冰冷厌恶,“如今若你肯低头,阳儿心善许收你做个洒扫婢女,待年老时许配个小厮。”
高令月震惊的看着眼前亲昵相拥的两人,那个亲昵叫着自己姐姐的人,那个在自己耳旁说情话的人,怎会?怎会!
“你还不知罢,高澈是怎么死的,聂太后又是怎么自尽的?”
舞阳公主娇笑着睥睨着她,走到她身前伏在她耳边如同女儿家的悄悄话般。
高令月身子一震转眸怒视着她,“阿阳,你怎能这般忘恩负义!”
却见舞阳眼中燃着复仇般汹涌的快意,如同舔信的毒蛇般狠毒的恨意,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般阴惨惨冷笑着。
“忘恩负义!”她冷笑一声,继而捏着高令月的下巴狠狠道:“高令月你总高高在上,享尽荣宠,可知寒风凛冽想要冬衣御寒都要受人白眼是何感觉!你可知被强迫送去蛮荒之地为了活命辗转蛮夷身下是何感觉!”
“哦,对了,阿阳还有件事情没同皇姐讲,”
她睨着高令月嘴角翘起,眼中波光转动,眼光扫到宁玉似有千般媚色,伏在她耳畔小声道:“夫君说他早就恨极了你,在你身边无非是逢场作戏,在他眼中你不过是蠢笨的跛子!”
高令月身子一颤,脸色苍白,嘴唇血色尽褪,咬牙颤抖眸中恨意渐浓不可置信的看向宁玉,却见他此时仍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似毫不在意她的死活。
“你还在期望什么!你高令月此时不过是阶下囚,身背骂名的亡国奴!”舞阳公主见高令月看向宁玉,眸中寒意骤冷,厉声道。
大喜大落的落差使高令月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一点点吞噬着她的理智,那是恐惧,是仇恨,是厌恶,是愤怒,还是,后悔……
若非她自负拥有超出时代的记忆,若非幼时摔断了腿,父母溺爱,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也不会落至如此境地,以至于昭国亡国,母后悬梁,皇兄战死,都因为她信错了人,爱错了人!若能重来,呵,若能重来呵……
想着想着,高令月忽的仰头笑了起来,一声大过一声,笑得眼泪横流,声音嘶哑,墨发遮挡令人看不清神情,只余凄厉绝望的笑声回荡在含光殿中,久久不散。她猛地站起身来,在众人惊惧的眼光中冲了出去。
舞阳公主被她披头散发疯魔模样骇住,而宁玉看着发疯般的高令月皱紧眉头,欲言又止,却挥手制止阻拦的侍卫。
天下起鹅毛大雪,寒风呼啸着吹卷起高令月的嫁衣,如火般艳烈,她拼命爬到九重塔上,站在围栏后这里能俯视昭国。
北风吹乱佛铃声,如同一个社稷的衰败。
漆黑的佛塔上,高令月红衣如火,风吹乱她的头发,悲哀决绝。
铁蹄踏碎了山河,京都中四处燃起汹涌烈火,空气中灼烧尸体的血腥味弥漫口鼻,往日繁华如今破败流离,烽火连天。
她不想再见宁玉道貌岸然的嘴脸,不忍再看被烙上亡国之名的昭国。
风吹得衣袍猎猎,夹风带雪刮得脸颊生疼,她虽有现代人的意识,可十几年来的熏陶早将她磨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古人。她是昭国的嫡长公主,荣辱生死都与社稷一体,昭国亡,皇兄崩,母后薨,亲夫叛,她,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人世!
从璇玑塔跌落而下,她自嘲一笑,高令月此生不过是一个笑话,天真无知。她重重摔在地上,眼前弥漫起无边无际的红,她想,真是喜庆的颜色呵,她却以此作了死结。
癸丑年腊月初七,这本是她的新嫁日,却作了亡国祭,身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