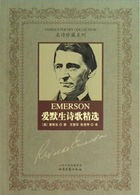是哪一年的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一个晴朗的夏天的午后,我的爷爷——啊,不,应该说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在帮着自己的父亲犁完地主家的田后,就赶着唯一是自家财产的那条大黄牛,来到离稻田不远的一片草场。
草场很宽,也很长,几百条牛并排从草场中间头也不抬地吃到草场边,也要吃上七天七夜。更何况,只要牛低着头吃上一个小时,就能饱得不能再饱了,就能促使牛躺在草场上一边休息一边反刍了。
那么深的草,那么肥的草,那么嫩的草,那么富有营养的草,即便再饿的饥肠,也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填充,得到满足。所以,少年才把饥饿的牛赶到草场中间,牛就不理睬少年了,就自个儿把头埋在深深的青草里,品味着仁慈的大地馈赠给它的精美的补品。
吃这些嫩嫩的青草的时候,牛摇头晃脑的,那样子就像是天使在天堂里采摘长寿之果,蜜蜂在天堂里追闻花朵之香。
牛还很挑剔,有很多嫩嫩的青草,它竟然只用肥大的舌头把尖尖揽进嘴里,其他的部分,比如养分更加充实的草的腰部,比如从草的根部新发出来的更加肥嫩的叶子,牛居然闻都不闻一下,就把一只大脚重重地踩在了上面。
太可惜了!
这句话是我少年的爷爷说出来的。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红红的一个大太阳像是要把人类蒸发到天空里去,差不多快把能够吸干人类血汗的热量都散发出来了。
少年忍不住了,就把那顶他爷爷少年时候戴过的,现在已经破得不能再破的破草帽戴在头上,想借此减少一些头顶的燥热。他知道牛在犁完地主王大富家的那一大片稻田后,早已饿得直咽口水,进入青青的草场后,已经顾不上到处撒野了。于是,少年就懒得管它,就自个儿抬起头,看着天空中那个热烘烘的大太阳,一心盼着这个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火球早点滚到西边的山背后去。
下场雨就好了,哪怕把我的衣服全部淋湿了我也愿意。少年在心里对自己说。
假如你当时也在草场,你一定会笑少年真的是在白日做梦。天空压根就没有一点乌云。
不过,还真的让少年兴奋了一回。就在少年刚说完话大约十七分钟后,他突然感到身上有一种彻骨的凉爽。
挡住太阳光的,是一片洁白的云。大大的一片。就因为这片云的出现,蓝蓝的天空一下子更加动人起来。少年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着这有点慑人心魄的天空,激动得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按理,就在眼前这片田野里长大的少年,对这类悬挂在高空的美景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少年今天却显得有些异常。
是啊,偌大的一片天空底下,偌大的一片草场之上,居然只有少年一个人和一条牛在!不同的是,牛在吃草,少年在挨饿。少年当然不知道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少年毕竟才十二岁,知道的事太少。假如真要找出一件他知道的事,那就是其他的人都睡觉去了,因为他的父亲一遇到这样的天气就会在家里的破床上睡上一觉。
是呀,那么热的天气,自己家又没有田地,闲在家里又没有什么好消遣的,还不如睡上它一大觉。即便是干地主家的活,也应该这样,等养足精神了,晚上再出来干活,岂不是更好?说不准还能做上一个可以让自己从梦中笑醒的美梦呢!少年想。
少年的想法当然是对的。晚上太阳已经睡觉去了,就剩下月亮、星星、清风、空气,就剩下蛙声、风声、虫鸣声、情歌声。即便地主的管家把鞭子使劲抽打在身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陪伴着,也不会感觉有多疼人。哪像白天,已经被太阳晒得疼进心里的皮肤,再受到没有一点人情味的皮鞭的抽打,真是要人的命。
少年的心里突然一亮,像是从牛身上发现了什么,居然一下子羡慕起牛来。
是呀,牛虽然也同自己一样,时时遭到主人的毒打——当然,更多时候是遭到我们的毒打,但毕竟有那么大的一片草场为它随时提供养分。牛那么大的力气,每天要犁完那一小块田地简直就是小菜一碟。饿了,更是再容易解决不过了,只需往草场中一站,分分钟就遏制住饥饿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少年想。不信你看,牛还可以在草场里挑三拣四,看着不顺眼的草,就狠狠地踩上一大脚。
正因为这样,每当牛吃草的时候,少年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像在欣赏艺术一样欣赏牛吃草的样子。
看着牛吃草时美滋滋的样子,少年的嘴里便像夏天的田埂一样潮湿,时时渗透出淡中泛酸的水流。这水流还真怪,才把它咽下去,它马上又冒出来,像安了弹簧似的。
少年曾想出很多方式来制止这股水流,却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制止。
后来,少年以为是自己水喝多了,便想方设法不喝水,嗓子干得冒烟了,也不愿喝上哪怕是一小口。可是,即便少年三天不喝水,只要一见到牛吃草时的情景,那股水流还是会立马从喉咙里冒出来。
要是我也是一条牛该有多好!还有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哦,还有我那才七岁零三个月的妹妹!
看着在草场中吃得津津有味的牛,少年感觉有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要说。可是,在这片草场中,除了他一个人外,就只有那条自从走进草场后就再也没有抬起过头来的牛了。少年还能去对谁说这些话呢?
少年一直在想,怎么牛能成为牛,而人不能成为人呢?吃草的牛都有那么多长满青草的草场,怎么吃粮食的人就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栽种粮食的土地呢?
不知是哪里射来的光线照亮了少年的心眼,短短的一个下午,少年竟一下子想到了那么多曾让他想不通的问题。
想不通也倒不管它了,只是口中的这股水流时时让我感觉不舒服。要是家里有钱,去药铺抓服中药来治一治,或许能把它治好。如果能治好,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我就不会这般不舒服了。少年的眼睛突然湿润起来。
少年哪里知道,治疗这种病的唯一药方就是他家里最紧缺的粮食,就是被地主独自占用着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无数的人真正成为了人,并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粮食,少年——啊!不,应该说是我的爷爷——才完全明白过来。
当然,刚开始时爷爷还奇怪:怎么有了粮食后,想要点原先那种水流来润润嗓子,怎么就是要不来呢?可惜的是,这不会再有水流从口中渗透出来的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爷爷就带着瘦弱的身子离开了让他饥饿了差不多一生的尘世。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没有见过爷爷是什么样子的我问奶奶,怎么爷爷那么早就离开了你?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他?奶奶揩着眼泪说,你爷爷早早地离开我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经常挨饿,造成早期营养不良。还有,你爷爷不是不喜欢你们,而是担心你们看见他瘦小的身子会害怕,不愿意叫他爷爷。
当时我还小,弄不懂奶奶这些话的意思,更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流眼泪,也就没有什么出奇的想法,等到后来长大了,才理解了奶奶当时的心情,还会在回想起这些话时使劲把泪水往心里咽。
关于爷爷,除了他看着一条牛在草场中吃草这件事外,有关他的很具体的事情我就知道的不多了,而在他的一生中——当然是在他进入大地深处之前,唯一对我有一丝安慰的,就是在他永远地躺下那天,家里为他宰了一条大黄牛。
这条大黄牛是不是爷爷少年时对着说话的那一条,我就不知道了。问奶奶,奶奶只是说她是在爷爷十八岁时嫁给爷爷的。
我想,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斯人已去,知道再多又有何用。
2002年3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