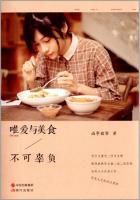琛哥死了,葬在了大武口的西山上。
这是我们魏家车门老魏家的人死后,安葬在异地他乡的第一人。
乍听这一消息,我的意识有些恍惚,怎么会呢?还不到70岁,去年去大武口,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喝酒呢,他那健健康康的样子,怎么看也不是身体有毛病的人呀。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再说了,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人死了,即便是死在他乡,也是必须魂归故里的。况且他的哥儿弟兄都在,来世团圆也有条件,为什么葬在了异地他乡呢?有言道,何处的黄土不埋人。莫不是琛哥走出故乡的时间久了,对故乡淡漠了。
疑云在我的头顶盘旋。
我不能解,顺着他一生走来的路往回追寻。希望在流逝的岁月中,在飘散在故乡上空的浮云里,寻找遗失的蛛丝马迹。
琛哥大我10岁,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的知识分子。他经常穿着蓝色的中山服,梳分头,脸洗得白净白净。他在大队的小学有一份国家正式教师的工作。因为他是吴忠师范毕业的。至今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前后的几年里,他带领的学校的花鞭队,在我们大队的各个村子表演的情景。“咔咔、咔咔,喀喀喀、咔咔……”一米长的花鞭在他的手里翻转成了花朵,尤其是花鞭的两头分别往两个肩头上一磕,昂首往前一跳,再磕到脚上的动作,潇洒极了,流畅极了。把他那英俊的相貌、近1米80的身段张扬得风都为他鼓掌了。至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半大孩儿们,那简直是眼馋极了,羡慕极了。几乎人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梦:长大了,要成长为琛哥的样子——形象、气质,还有能领工资的一份工作。
不仅如此,琛哥还在我们村子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家有了电灯,第一家有了收音机。当然,这是在他调入灵武地震台以后的事。他的收音机也是自己买材料装配的二极管半导体。就这样,也已经让村里人羡慕的不得了。在那些年,他就是我们村前卫生活的代表,文明传播的使者。
让别人羡慕,自然是好事,能够提高自己的自豪感和幸福指数。可是,羡慕也同时产生了嫉妒。而且这种嫉妒被有些人扩大化了,变成了对他们家的挤压和祸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琛哥的妻子是个漂亮贤惠又十分能干的人,见人不笑不开口。那个时候的农村,男人不在身边,自己觉得比别人短了半截。人家为难她,她总是忍着,逆来顺受。她不想给丈夫心里添堵。
那是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半边户”们所共同遭遇的不幸,在她们家却越演愈烈。你男人不是能挣钱吗,你不是穿得比别的女人光鲜吗,一家三亩地的稻子你薅去吧!一家五亩地的粪土你送去吧!琛哥心疼了,可是他毫无办法。他只能利用星期日休息帮妻子多干一点。每当他与妻子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他的脊背正遭受着生产队长芒刺一般奚落的目光。忍受吧!这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乡里乡亲的,能挤兑到什么程度呢?何况是为了妻子,他说服自己。可是,渐渐忍耐变成了好欺辱。什么活累,什么活脏,什么活就是你的。
那几年我也参加了工作,一般一个月才回一趟家。断断续续听生产队上的伙伴们说了一些队长有意为难琛哥家的事。虽不是眼见,但我宁愿相信。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生产队长,那个破芝麻官的唯利是图,专横跋扈我也是能感觉到一些的。至于有的地方生产队长利用那点小权利侮辱知识青年,侵犯漂亮女性的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就曾很诚恳地对我说,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在那个队上,凡有一些姿色的大姑娘小媳妇,没有逃过他父亲手心的。我不知道是生产队这个体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政治,在新体制下发生的新变化。许多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对生产队长的揭露真是触目惊心!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琛哥的斯文无法回避地被剥落了。由一般性的吵架上升为粗俗恶毒的人身攻击。据说为了他父亲的庄台地甚至打了起来。中国农民狭隘的劣根性欺辱得他在故乡没了尊严。也正是这种欺辱,给了他奋发的力量。因为他看明白了自己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带着妻小离开家乡。家乡因为小人的当道,已经失去了包容他的胸怀,不给他立足之地,他必须离开。而离开的途径就是努力地工作,实现“农转非”的目标。
他成功了,先是当了灵武地震台的台长,后又提拔为石嘴山市地震台的副台长,退休前还解决了正处级待遇。在国家政策农转非的年月,他的妻小也适时地解决了城市户口。他把根从故乡彻底拔走了。厄运成就了他,或许他把家搬到大武口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再也不会给生他养他的家乡添堵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近几年他只是在清明节,或者他的弟兄们家里有大事的时候,才偶尔回到家乡。其实他已退休多年,大武口到吴忠,两个小时的路程,多简单的事呀!但是,他很少回去。难道他对故土就没有一点点眷恋之情吗?
然而,琛哥客居他乡永远地安息了。
我明白,故乡的一些人和事把他伤得太重了,他心里的坎没迈过去。其实人活一辈子,谁心里没有个越不过去的坎呢?除非那个伤害了你的人亲自出面,与你解这个结。
故乡成了他的伤心之地。为什么非要回去呢?
魂兮难归!
201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