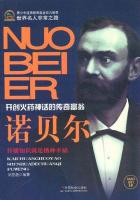母亲对于莫言的疼爱还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许因为父亲是读过书的,莫言家不看重眼前利益,都要孩子们上学读书,而不是去集市卖点小玩意儿赚钱。还是山东自古就重视教育,所以女人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我母亲在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无论家里有多困难,都会满足我买书的要求,她平时为了几毛钱都会跟小商小贩计较,吃东西也很俭省,但只要我说我要买书,她眉头都不皱一下,立马买下来。记得看过一本商人刘雪红的传记,她也说自己把一笔不小的零花钱都买了书,父亲本来要惩罚自己乱花钱,但得知买了书,反倒说,以后这个孩子要钱,可以给。莫言小时候为书痴迷并不是新鲜事,难得的是母亲对自己的支持。
1972年,村里有个青年淘换到了一套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共五本,定价五元。他就问莫言是否需要,70年代,五元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他就问母亲可不可以买,母亲就说你看吗?你看咱就买,他说看,母亲就坚决地说,那就买,我跟你爹商量。后来莫言提到这五本书的时候,说是母亲当掉嫁妆买的,还说对自己很有用,自己的历史知识都从里面来的。1976年参军,莫言就只带了这套书走。
1994年,母亲的死也深深地震动了儿子的心。莫言因为母亲的死万分悲痛,所以写了小说《丰乳肥臀》,住在故乡,那离母亲最近的地方,仅仅用了83天,就写出了50万字的初稿,在书的卷前:“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莫言其实想把这本书献给天下的母亲。小小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他故事的缩影,承载着他的野心,他试图用这片乡土写出共通的人类情感,来祭奠那些应该祭奠的,缅怀那些理应缅怀的,以及悲悯那些可以悲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这个男子,想有母亲一般的胸怀,至少在写作上,他很努力做到一种大爱,或者唤起一种大爱。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土地为对象,土地,多么像母亲,或者,土地就是母亲。
奶奶·婶婶·姐姐
1
大奶奶在莫言的叙述中出现的很少,只是在一次“文革”的批斗中,莫言姐姐也上去喊口号,大奶奶气的要命,跟四叔说,“嫚竟然说要我灭亡,气死了。”四叔连忙解释这是做给人家看的,大奶奶还是气的要命,几十年不跟她说话。姐姐辩称自己是在要求进步,说家人应当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莫言大哥提起大奶奶的时候,说,小学五年级放学回家,大奶奶就对他说,你娘给你生了个拉小车的。拉小车的就是男孩,大哥当然不高兴,“难道你要我们兄弟一辈子但农民吗?这小车我不想推,也不用弟弟拉。”
莫言的奶奶姓戴,人称管戴氏,20岁的时候嫁给了19岁的爷爷,当时肯定算是晚婚了,因为我的姥姥16岁的时候,就嫁给了我姥爷,可见在解放前的山东农村,嫁人是很早的事情。莫言奶奶生于1894年,卒于1971年,终年77岁。虽然,奶奶不像《红高粱》里的“我奶奶”戴凤莲那样“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样“杀伐决断”,而是接近于《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她很有智慧。没分家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生活,不免有些私心。大爷爷开药铺,收钱的时候把铜钱投进一个竹筒里,到了晚上,奶奶就用一个麦秆伸进竹筒里量一量,就知道竹筒里大概存了多少铜钱,第二天开门营业,奶奶又用一个麦秆试,发现少了一大截,就说明里面的铜钱被大爷爷拿走了。
奶奶的娘家是极普通的农民,据管谟贤回忆:
“因为她的父兄会竹器手艺,所以生活过得比一般农户强。小时候曾听奶奶发牢骚说,她和爷爷成亲后,爷爷的以及后来子女们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负责的,我们家一概不管。我们奶奶虽然极普通,但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奶奶的手极巧,我不止一次地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菜好吃,针线活漂亮。村里有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操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在小说《扫帚星》里,奶奶既是有名的媒婆,又是接生婆,“还是屯子里替死了人的家庭料理丧事的司仪”,给儿子相媳妇也有板有眼,能干的很。只是小说里村里的孩子对奶奶的评价却不高:“红眼睛,绿指甲,腚上拖着灰尾巴。”
这个奶奶的胆子也大一些,日本鬼子来的时候,爷爷被那些伸脚就踢人,举起刺刀就要杀人的恶魔们吓坏了,所以很害怕日本人。爷爷被踢到在地,是奶奶向前扶起他,爷爷想跑,子弹就在耳朵边飞过。从此,鬼子未到,爷爷先溜走,倒是奶奶留守,每每有军队召集村民们开会,无论是八路党还是解放军,都是奶奶去开会。奶奶其实也害怕,她总说“一有动静就想上茅房”,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们恶作剧似地喊“鬼子来了”,她就提着裤子想往茅房跑。
2
奶奶有时候很可爱,60年代,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奶奶听从上海归来的孙子管谟贤说起楼房。她怎么也不明白人是怎么爬上楼去的,她总以为是用梯子,更不懂什么是电梯,越听越糊涂的她只有感叹:“看不到真楼,越听越不明白”,说来悲哀,直到奶奶去世的70年代,高密的县城也才只有两座二层小楼,她至死也没明白高楼是怎么回事。
奶奶有时候也会偏心眼,偏爱婶婶,干活最多的母亲反倒常常被欺负。莫言坦言:“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奶奶更是常常用锥子一样的目光扎我。莫言说,奶奶有时候也会虚伪地表白:“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咬咬哪个哪个痛!”莫言戏称自己顶多算个骈指,就是多余出来,被大家笑话成畸形的指头。有一次奶奶表扬了莫言,还给了他一滴香油吃,原因是莫言本来因为贪玩,掰奶奶上厕所的柱子,不料柱子腐朽,连累莫言掉进了茅坑里,奶奶认为莫言若不掰断,掉进去的就是她自己,所以表扬了莫言。
母亲为什么不着奶奶待见,八成因为莫言讨厌,还有就是奶奶欺软怕硬,婶婶干活比较滑头,对奶奶也不很尊敬,奶奶反倒小心俯就。一个不受待见的儿媳妇,自然吃了不少苦。比如奶奶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母亲生病,比如心口痛,也就是吃几片止疼片,疼着也要干活;胃痛得了偏方,生姜鸡蛋饼,连鸡蛋都不敢让奶奶看到,是母亲的姑姑偷偷送过来的。后来脱肛、妇女病、腰上生毒疮、带状疱疹,都是能忍则忍,即使呻吟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
莫言的三奶奶死得很早,三奶奶跟三爷爷生了五个孩子,在刚生完小女儿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孩子刚生完,三奶奶就看到一个日本兵拿着他那裸露的生殖器,对着她走过来,她当场就吓得仰面跌倒,随后就得了妇女病,产后血崩。四十多天不吃不喝,大喊大叫,像是鬼附身。她喊三爷爷:“管三,我要吃小鸡,小公鸡!”三奶奶的灵魂仿佛在那一场惊吓中出离,她疯掉了,她那令人心悸的叫声,彻夜未息,农村会叫来山人做法,挂字符、贴黄表纸,往她嘴里灌池塘水,用铁犁镇住她的胸口,折腾死了算完。
三奶奶的死使莫言对日本人的罪恶有了另一种认识,在生育面前,只有最没有人性悲悯的民族才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也正是那个时代日本人了无人性,才让最能吃苦、但凡有丁点可以做奴隶的希望都会隐忍的中国人揭竿而起,成就了一个个《红高粱》的故事。
3
婶婶永远是轻松的,她选择去生产队劳动,磨一天洋工,回到家等着吃饭,功臣一般。莫言记忆里,有一股野菜的味道。困难时期,糠菜是全家的主食,十几口人的饭,每次都要把野菜在石头上捶烂,把绿水攥出来,再掺上糠和红薯面。这样的饭当然劳动量巨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做。婶婶还冤枉莫言。一次,弟弟从树上摔下来,把腿摔坏了,自己怕婶婶责骂,就告诉婶婶是莫言推下来的。婶婶当着母亲的面骂他:
“你从小就这么坏,你什么时候能坏到死啊。”
说起话来很是尖酸刻薄。当莫言抢堂姐的饭吃,大家哭成一团,母亲还要给婶婶赔不是,把自己碗里的省给莫言吃。
母亲自然是没享什么福的,婶婶也没享到福。堂姐突然肚子疼,就去世了,撇下来年两个孤儿,自然要婶婶照顾。她的小儿子又胡闹,开旅游品加工厂,欠了一屁股债。七十多岁的婶婶还要给人家打短工,严寒中去摘辣椒,摘一天才挣两2元钱。当我们给她钱资助的时候,婶婶对我们感激涕零,恨不得掏出心来给我们吃。她终究没有活过80岁,要说妯娌之间,也没差到哪里去,在那个年代,妯娌之间打的头破血流的也是有的,况且妯娌之间本就有些天然的彼此不待见,比如近来热播的电视剧《妯娌的三国时代》,就是妯娌间不可避免的是非展现。如此看来,母亲和婶婶的关系还是好的。母亲去世之后,三日圆坟,婶婶教我们兄弟三人每人左手抓一把谷子,右手抓一把高粱,围着母亲的新坟走,“一把高粱一把谷,打发先人去享福……”看到这里,我想,莫言母亲的勤劳和不与人争执,抛开了过往是非,都让她足以得到每个亲人的尊重。
4
堂姐就是五叔的女儿,管谟华。堂姐很年轻就死了,大概是1987年左右,当时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肚子疼,用小车往医院送,路上脖子一歪就断了气。当年,五叔顶替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所以堂姐手里有零花钱。学校里来了照相的,堂姐拿钱出来照,这在当时是每个孩子羡慕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撺掇着莫言上去跟堂姐一起照相,莫言果真上去了,摄影师就问,这是怎么了。
莫言说,“我们是一家的!”堂姐这时候给了他应有的支持,并没有否认,于是,一个漂亮小姑娘的花棉袄和一个邋遢小男生的鼻涕棉袄一起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这张照片后来还被婶婶撇着嘴奚落。母亲也说,看你这幅邋遢样子,照得什么相?把你姐都赖丑了。我想,堂姐早夭,如果不是因为与莫言合影,大概不会留在那么多人的脑海里,或者冥冥中,人的生命历程是有定数的,上天不让你在这个世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让你仅有的痕迹放大开来,那么多人认识莫言的堂姐,也因为此时,她善意地默认“我们是一家的”,后来,在散文《从照相说起》中莫言写到:
“这是我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时间大约在1962年春天,读者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袄,下穿单裤,头顶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胸前闪闪发光的,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裤腿一长一短,不是裤子的问题,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照片也就不必发表。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早四个月出生。”
小时候,一家人围着低矮的饭桌西里呼噜喝野菜汤,孩子们夹在大人中间,坐在爷爷做的各式各样的板凳上,喝难以下咽的野菜汤。因为年龄太小吃不下野菜汤,母亲就单独为这莫言和堂姐煮东西,两个地瓜或者蒸一个不加野菜或者少量野菜的玉米面饼子,莫言饭量大,但也跟堂姐一样,不能多吃,堂姐吃饱了,莫言却不饱,吵着饿。
莫言还会盯着奶奶黑瓷碗下发霉卷曲的黑色红薯干,不断地咽口水,母亲会拿筷子抽莫言一下,让他快喝汤.后来,奶奶会只好分给莫言和堂姐一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结果他总认为是奶奶偏心,把大的一片给堂姐,所以就抢堂姐手里的,抢过来一看,又觉得自己那一片大一些,于是再换回来。几次争抢,堂姐就哭了,婶婶的脸就沉了。莫言在《猫事荟萃》里写道:
吃完了就把姐姐手里的薯干抢过来塞到嘴里。她抖着睫毛,流着泪,看着她的母亲我的婶婶。婶婶也流泪。母亲举着巴掌,好像要打我,但只叹息一声就把手放下了。
有一次,他和姐姐每人一个小板凳,吃耗子肉。这只耗子可是从猫嘴里夺过来的,足足有九两,倘按照新称,估计一斤还要多。祖母兴奋地把耗子烧了,往地上一摔——
撕下一条后腿,塞到姐姐嘴里,又撕下它另一条后腿,塞到我嘴里。……鼠肉之香无法形容,姐姐把鼠骨吐出来给了猫,我是连鼠骨都嚼碎咽了下去,然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祖母的手。
莫言自然还是觉得姐姐吃的那块儿多。这样的野蛮抢夺自然让奶奶站在堂姐一边,父亲要打,母亲也常常跟奶奶、婶婶陪着不是,说千不该万不该生下一个大肚肠的儿子。红薯干不饱自然只能吃野菜团子,那是扎嘴的东西,只能含着眼泪吞下。长大后,莫言对姐姐提起这事,姐姐却笑着说:
“哪有这事?俺不记得了。”
《牛》里面,“我”在姐姐出嫁的时候,偷吃了一碗肥肉,可见儿时因为“抢吃”受得不痛快在《牛》里彻底解恨了。莫言爷爷那时候总是给孩子们精神会餐,说一些可口的食物,比如嫩黄瓜拌猪耳朵、单饼卷大葱,说得孩子们直流口水,奶奶就反对,说爷爷会让孩子们更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