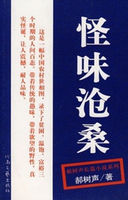夜晚的空气中还有雨后的味道,那是一股淡淡的鱼腥味。仿佛有千万条鱼在风雨中落回大地。我嗅了嗅鼻管,感觉自己的嗅觉还是那么灵敏,心中便觉得安慰。楼下时不时传来葡萄架下的用水声,从哗哗水响中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一个少妇的手在不停的甩动,然后自来水的开关被拧紧。我坐着,我在想这篇东西是什么时候到达我的手上的。《致命的小说》,作者洪劬颉。完稿时间是1997年9月7日。小说稿的封面上写的十分清楚。大概这就这么呆呆的想了大约一刻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3年前的一天中午,好象是年根了,我去单位拿苹果,然后在我的桌上便看见了一封信。确切的说是一篇小说。因为洪劬颉惜墨如金,并没有给我一个字。我的脑海里终于浮现出当时我站在办公桌前抖动稿纸的样子了,我以为他会在小说稿中附纸一张跟我说上几句,事实上,半个字影子都没有。我记得他跟我在那个难忘的中秋之夜是提过一篇小说,不过不是叫《致命的小说》,而是叫《闯入者》。很显然,我可以毫不费力的判断此篇非彼篇也。这篇小说,我当时是认真的看了,觉得这是篇很有意思的试验小说。说实话,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这是当时看完后的印象。可是时隔三四年之后的今天,我读来却觉得如嚼橄榄,味道非常。我很感谢自己两个小时前的手忙脚乱,使它从我的一堆故纸中遗落在地,我感到一丝意外的惊喜。它就像几年前横在我的书案上一样,静谧中一股淡淡的墨香自久远中扑面而来。小说家K的故事透出了执著、疯狂、写作、爱着。
我要说的是,在这篇小说中有两个场景令人难以忘怀,一个是K和他的女友接吻,一个是K的自杀。接吻一节是我看见的最为眩目的一幕。我愿意在我的小说中腾出一些空间,让给那两个被欲望的火焰燃烧的人。"……费丽达尽管感到很疲惫,四肢乏力内心发慌仍表现的坚韧刚毅,乐于听命的应邀而来。她首先翻过木板然后匍匐在这块粗糙的木板顶上敲k的门,然后k打开了门,站在小房门底下,预备好拥抱的姿势。这可是他们两个人花了五六年时间精心排演出来的,可谓炉火纯青,百玩不厌。K今天他要玩一个新的花样,当费丽达如往常头先下来时,k不用手去拥抱,而是用唇直接迎上去。费丽达很会意的一笑,然后用手环住了k的脖子,唇像蚌壳一样合了上来,脚却勾在上面的顶板上,像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般那样雕塑的定格,然后是一阵潮湿相濡的声音,k显然对这种高难度的接吻动作很满意,那是一种不期而然的创造,一种诗意,一种想象力。费丽达的腰肢像一根竹篾条轻柔优美的缠绕着k,k感到兴味盎然,在自己的余光中他看见女友白皙的颈项上突出的锁骨,心里一阵热流于是不断的向上涌着……"而K的自杀方式则显得不可思议,我的脸上现在的狐疑还没有消失,是的,一个人竟然选择了这么奇怪的方式解决自己。这个K和其他赴死的人一样,都几乎从"TO BE OR NOT TO BE ,THERE IS A QUESTION"开始的。这没有新意。其实死亡是没有新意的也无法有新意。我倒以为死亡是一本旧帐。K的自杀是从咀嚼自己的头发开始,"他开始沉思,并不自觉的将自己的头发拔下--起初是--放进嘴里咀嚼。他的下鄂部的错动和牙齿间咬合的声音使他还明了自己--活着,活着真好--错动的鄂部具有阵颤般的快感,在他的身体内弥漫开来,像一股棉细的电流迅速流向血管,神经。头发很快在他的牙齿下断裂,他在这一刻脑海里是费丽达的子宫美妙的收缩。慢慢的,他发现自己吞下头发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到临了,他以为那丝丝黑发犹如白汁源源不断的流淌进了他的口腔,奔向了他的心脏。他咀嚼着,费丽达的白金躯体在自由的尽情的扭动,翻转,那美的蠕动中释放着热量,K感到这股热量裹向自己,自己先是慢慢的缩小了身子,然后缩小了自己的知觉,一直到最后这个涅磐之火中化为一落灰烬。"
上文中带引号的部分引自原文,没有作任何改动。这是我以为两个非同寻常的段落。好了,我不想再去叙述那一场情与爱带来的死亡厄运。我只不过捡出其中两段给你看看而已。死了,已经死去,活着的还得生存。我愿意和你说说下面的事。下面的事实是我零零星星的从朋友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基本属实。据说,洪劬颉在一段时间内经常光顾八里敦酒吧,在那里拼命的喝酒、聊天、还有劲舞。那是一个很有名的酒吧,1998年我曾经在那逗留过,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所谓的作家朋友,她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女,画着赫人的眼影,目光迷离,肚脐与透明装极具挑逗性。她们一会儿在摇曳的灯光里晃动她们的头发和肢体,在猛烈的节奏中,仿佛一群红绿怪兽。所幸的是我仅仅在那儿逗留了两三天,便离开了,那绝对是一个堕落的地狱。我想象着洪劬颉,我的朋友他是如何走进了那一片灯光灿烂中去的。洪劬颉的劲舞性感十足,这还是一个叫兔子的美女在十月份邮寄给我的明信片中提到了他,她的意图只是告诉我她不再需要我。当时我心里蓦然一松,那又是一段游戏的开篇。我眼前出现了那一条昏黄的沉睡着在灯光中的大街,街上只有两个人的身影,他们向前走着,灯火和身后的清晰可闻的音乐在振颤,闪烁。
洪劬颉和那些美女们一样也尝试写作,将那些自认酷毙的盛会带进了文字。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扎希布达告诉我,我感到非常吃惊。扎希布达是我的朋友,因为是我的缘故他在1990年春天认识了洪劬颉,这个西藏人给过我和洪劬颉许多灵感。更确切的说是西藏引起了我们的幽思。他今年5月份在去成都的火车上遇见了洪劬颉,两人都深感意外。他们在火车上聊了很多,洪劬颉告诉了他他在写作,和他的笔名。而扎希布达也有幸读过一个叫忘川的人的作品,扎希布达没有想到这个忘川就是自己大学老友。扎希布达告诉我当时在火车上他给他提出了忠告。希望他不要写滥了笔头,这不是一件好事。洪劬颉的反应显得很迟缓,他搬弄着手指告诉扎希布达自己完全是身不由己,生计所迫。原来洪劬颉的辞职要比我想象中得快得多,也坚决得多。扎希布达两天后从成都坐火车来到了我居住的G城。而洪劬颉从成都转车去了南京。扎希布达感到非常吃惊与无奈,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火车上的邂逅是他与洪劬颉的最后一次碰面。第二天,我和扎希布达一起去了G城图书馆,复印了所有署名忘川的文章,打算汇集成册作为纪念。扎希布达在G城呆了一个星期后就离开了,他必须前往北京与他的妻子相会合,然后一起奔赴美利坚作陪读丈夫。朋友走了,周遭静了,心脏似乎也变得寂静了下来。出于一种责任,我认真的阅读了那些文字。阅读的最后,我放弃了汇集成册的想法。文字实在粗糙不堪,其中的叙述几乎是一个模式,劲舞、吸毒、性交、无所事事、纸醉金迷、情人、同性恋、痉挛、恋母或者弑父等等。此后我的另一个想法变得坚决,那就是尽快的将《希腊哲学之生死观论》贴上因特网。我以为这是洪劬颉最好的文字。
洗却尘埃,了由世界。
洁白身体,有新世界。
这是洪劬颉临死时手里捏着的纸条上的文字。似乎是一个偈语。洪劬颉在盐城乡下那块黄瓜地自杀的消息传进我的耳朵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打点滴,天气特热,我竟然还患了感冒。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洪劬颉回到了乡下,更没有想到黄瓜地上的那一口莫名其妙的多起来的缸中人正是洪家第三个孩子。他在缸中放满了水,他慢慢的进去,冰凉的水包围着他的肢体。水慢慢的淹没了他。据推测,洪劬颉是在深夜里完成自己的自杀的。他自己将圆口锅盖板盖上。盖板上还有很重的石头,他使足了劲,沉重的盖板终于给他带来了完全的黑暗,水立即向盖板迎了上去。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了他,他坐在缸中,肢体已经膨胀,长长的头发飘满了水面犹如一层密密的水藻。他全身一丝不挂,只有手上一张纸条。人们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他的衣服。他真是赤条条的来,又赤条条的去。我赶到盐城乡下时,葬礼已经举行过了,一个年轻俊俏的农妇告诉我,他们就用那口缸埋了他,那口缸权当作棺材,她还指了指那个在黄瓜地上微微隆起的部分。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年轻俊俏的农妇就是洪劬颉的二姐。黄昏的光线中,我看见一丝白亮的头发从她的刘海中飘逸出来。她用铁锹在那个隆起的土包上拍了拍,一把新土腾起了一股尘烟。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在我的这篇小说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生活的真实纪录,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虚构,真实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那没有什么威胁,无论是道德的,还是生活的秩序感,对号入座,完全自由,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你能看到你,你们能看到你们。只是虚构的部分请原谅我的虚构。记住,因为那一部分是小说,才使整个的部分更像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