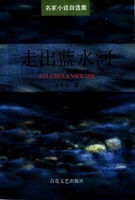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热爱小说。这个说法令我自己都冒冷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对小说从没有放弃,从来都是心怀之,念之,只是从没有到妄执状态。
其实我想说的是狂热,那种非理性,甚至病态的执着,我没有过。我甚至觉得自己过于理性,那种一泻千里的激情写作向来与我无缘,我希望也喜欢安静的叙述,慢慢走远。在小说里走远,但并不迷失。
小说和诗歌完全不同,小说安静迷人,自我完整,而诗歌热烈飞扬,处处迸裂,因此在很多时候,我变成了互不干涉的两个人。这样的转换,因时因地而异,毫无规律可循。只是对于诗歌,我关注内心,视其为内心的修辞术,它不仅仅是这个世界在内心的简单投射。而对于小说,那有太多的关目,技术,甚至伦理和态度,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说,诗歌需要的是一个仰仗灵感的懒汉的话,那么小说需要的是一个勤勉的农夫。
我是从千禧年正式写作的,这十来年,因为小说,我在记忆里似乎找不到一个通宵达旦的夜晚。相反,阅读倒是有过。从某种程度上讲,阅读也是一种写作。这不是偷懒的一种托辞。愿你相信我,这是我的诚恳之言。
在写作上,我不算多产,多能,我甚至写不来专栏文字。也没有那么辛劳,信奉勤垦细作,慢工出细活。我一次次的要自己有耐心。让故事扎实,让小说从容。故事和小说是两个概念,他们是一个母体,打个比喻的话,故事就如坯胎,而小说则是上了釉彩,火候恰倒好处的陶瓷艺术。却是正反两极。因此可以这么说:小说家不是故事家,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有自己的伦理,态度,逻辑和气味,以及氛围,当然还有叙述。
有太多的小说并没有诞生在纸上,而是在心里。或者说,主动地让更多的小说胎死腹中。出于严苛,警醒和自我审判。我们的世界,已经有太多的语言垃圾。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写作小说不太多的原因之一。对于业已写出的小说,他们浑圆自成一个小宇宙,有着他们尘世法则,爱欲情仇,以及他们的运命和轨迹。里面的人物自此也不再属于我,正如库切所言:
“每当有人跟我谈起‘我的人物’,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在公共广场上兜售商品的流动小贩形象,兜售些铅做的小士兵、上发条的小狗小马之类的东西,让这些小玩具在地上爬来爬去……我希望我的人物根本就不属于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2013年6月22日帝都·慈云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