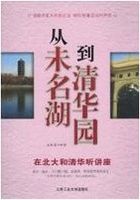一本书中这样写:“来到地球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你们愿意来到宇宙中这狭小的空间做实验。在地球的每一个人都应自尊自傲。”
那么,就带着自己的自尊、自傲,以壮丽的乐观,像君王蝶一样,穿越生命,振翅而,翔。
视死如欢
不是“视死如归”,是“视死如欢”。
元才子赵孟頫,年近五十,慕恋年青女子,意图纳妾,其妻写了一首《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样的情份在,这死,也便真的如欢了。
1935年,瞿秋白到达刑场,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此地甚好!”时年36。一死酬了这一生志向,死也必定是欢的。就牛虻死后留下的一封信,信的末尾,引用一首小诗:“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面对庞大、杂乱的旧世界,化身火种,烧掉污秽,跳跃的火焰带来了死亡,也迎接着喷薄云天的朝阳,这样的死,有什么不欢的呢?
小说《亮剑》里,赵钢和冯楠一见钟情,冯楠问赵钢:“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二十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与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时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是的,死亡为的自由和尊严,为的鲜明的反抗,这样的死亡,让人由衷感觉如欢。因为死的有尊严。
德普禅师性情豪纵,宋哲宗元佑五年十-月十五日,让弟子对他举行生祭,因人死后再受祭,死去的人是否能够受到香火,吃到供果,谁能知晓。
众人戏问:“禅师打算几时迁化?”
他答:“等你们依序祭完,我就要去。”
于是大家煞有介事,设好帏帐,安好寝堂,禅师坐于其上,弟子们致祭如仪,上香、上食,禅师一一领受自如。
弟子们祭后,又是各方信徒祭。祭完之日,天正降雪,他说:“明日雪霁便行。”
次晨雪止,德普焚香,盘坐化去。
他不是因为信徒能升天堂才不怕死,他并不知道死后有没有另一个世界,他的不怕死,是因为他已经活过,一生活得透彻,明白。就像赵朴初临终一偈:“生固欣然死亦无憾”,不独无憾,且是如欢。
“视死如归”,归,是游子归家,柴门草庐迎候疲惫的脚步,长出一口气:终于回来了啊。从今以后,就挣脱世间牵绊,独自抚孤松而盘桓吧。
“视死如欢”,欢,是眼见对面的爱人张开怀抱,展开笑颜,纵使脚下万水千山,荆途无限,却挞伐笞楚都喜欢,哪怕膝行过钉板,因经过长长的一生时间,如今终于得见爱人的欢颜。欢,是心下有所欢的欢,是“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的欢,是一生相思概已酬的欢。
有那么一群人,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生活在一切如意的乌托邦,空中飞着烤熟的火鸡;不需寻觅就可找到情人,顺利地白头偕老;“在这种地方,有些人会无聊而死,或上吊自杀,有些人会互相残杀。如此一来,他们为自己制造的苦难,比在原来自然世界所受的还多……苦难的极端反面是无聊。”
无聊地生,无聊的死,生亦无趣,死亦无欢。
其实,死不过是生的一个折射吧。一个人,若活过却不曾爱过,想过,思过,念过,追求过,反抗过,为着心中那一点萤火,和邪恶、阴暗、腐败、贪馋、懒惰,冒死作战过,死便死了,欢,又在哪里呢?
而一个人活过,爱过,想过,思过,念过,追求过,反抗过,为着心中那一点萤火,和邪恶、阴暗、腐败、贪馋、懒惰,冒死作战过,最后,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因为做了,所以心安,没有遗憾。也就视死如归了。
假如,一个人活过,爱过,想过,思过,念过,追求过,反抗过,为着心中那一点萤火,和邪恶、阴暗、腐败、贪馋、懒惰,冒死作战过,最后,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心里都当自己是赢了,纵使事不谐也,也没有什么了,一生义务已尽,如今终得解脱,于是欢天喜地拥抱死亡去了,此,便为视死如欢了。
尘外佛如花
去洛阳,看牡丹。
来接车的司机在他的座椅旁斜插了一枝牡丹花,感觉很震撼,别处看不见。
然后去一家叫做克丽丝汀的大酒店,安置好,出房间,好奇研究摆放走廊的一盆牡丹花,左看看右看看。一客人从旁经过,指点我:“勿看啦,假的罗。”我伸手摸摸,叶片是软的,花瓣是绒的,试着掐一下,把一小片叶子掐下来了,我拈给他看,宣布自己的发现:“呶,是真花。”
旁边保洁员经过,彬彬有礼地说:“我们酒店摆放的全部都是真花,这是我们这里最普通、最常见的洛阳红。”我看着它,绿蓬蓬的叶,紫红红的花,百层千层的瓣,这样的花,原来,是最常见、最普通的吗?
及至到了国花园,才发现是真的很普通啊。
偌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红的花海,黄的花海,白的花海,橙的花海,绿的花海,蓝的花海,紫的花海。以前读话本,晓得牡丹里有魏紫,有姚黄,一心寻访,却是花深不知处,兜兜转转,扑鼻只闻牡丹香。叠瓣重楼的花居多,居然也有单瓣的,也敢把花瓣张得那么大。
爱那黄花,只是蕊处有黄,花片则远看有一抹晕黄,近看又若白缎,这样的黄含蓄,不嚣张。也爱那紫花,淡紫深紫的花片,娇黄如黄雏鸟喙一样的蕊。也爱那豆绿的花,花片淡绿,嫩蕊娇黄。
到此方知李白真国手,“一枝红艳露凝香”多贴切。“红艳”,最俗的一个词,却无它无以形容牡丹的国色天姿。牡丹花地潮湿,虽是阳光热烈,却仍旧叶片及花片上露珠凝聚,且远远行来,一阵扑鼻甜香,“红”也有了,“艳”也有了,“露”也有了,“香”也有了,真的是“凝”上去的,我若是唐明皇,也要为贵妃心醉,为牡丹心折,果然名花倾国两相欢啊。
唐有王睿作《牡丹》诗:“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果成无语自成阴。”他骂牡丹妖艳惑乱人心,招得举国如狂,其实牡丹只管漂亮自己的,又与世人何干,与人心何干。檐头旗动,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帆动,是你人心自动,又与牡丹何干。
丰子恺自言不喜花,在旧书里见到“紫薇”、“红杏”、“芍药”、“牡丹”等美丽的名称,亲见却往往失望,因无非“少见而名贵些,实在也没有甚么特别可爱的地方”,我一向亦是如此,总觉得真花倒不如臆想来的花活色生香,偏偏这次看见满坑满谷的大牡丹,这样的花,的确是怎样的形容都不够,怎样的描摹都不能尽然--真花竟然漂亮得像假花一样。
这话是这家酒店的老总说的,我原要想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却发现词穷。以前看人家裙幅上绣的,壁上画的,绢纸扎的牡丹花,只觉庸脂俗粉一般的艳,想着世上怎么会真的有这样的花呢,及至真见,才发现真有,万花如绣,倒不如说万绣如花。
终于来到姚黄与魏紫的所在,却是姚黄如此,魏紫如此,不禁失望--花盘不大,花瓣不艳,植株亦少,东开一两朵,西开一两朵。可是很奇怪,周围朵朵牡丹朵大花鲜,游人如织争相探看,它们只是静静开在这个万花园里面,却愈看愈让人不敢轻慢。
因为它们开得静。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开篇便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顾恺之又说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也因前者是动,后者是静。人亦如花花如人,心动易,静心难。
深山古寺斜阳,一僧独卧眠床,那种静不算真的静,若是所有美女都在争奇斗艳,描眉画鬓,施脂抹红,却有那么一位两位,朴衣素颜,静立在灯火阑珊处,仿似身边的繁华热闹统统与我无干,这样的静,才是真的。
这,大概就是姚黄、魏紫有资格称为花王、花后的原因。
后来去白马寺看牡丹,这个感觉越发得到印证。
白马寺里的牡丹也多,却是原生,不曾嫁接,安本固生,是以开得并不夸张,人潮汹涌,它们却自顾自地静静开,静静谢,树下一片凋谢的花片,厚厚一层。姚黄与魏紫在这里也开得更静、更舒展、更从容。飘逸和紫罗兰和种种异色的郁金香,放在别处亮眼动心,在此处却只宜陪衬。佛祖拈花微笑,未必只肯拈一朵静莲。世间诸花,岂非皆有佛性。
不过遗憾的是白马寺古建筑多已无存,新建的屋舍楼宇还没来得及在光阴里浸润,是以处处是粗浮的新。
午后去龙门石窟,那大大小小的佛像被巧手的工匠从石头里一一解放,在石壁上或合掌,或闭目,或狞厉,或从容,或二人对站,或一人端坐,或有人随侍,或独自清修,或高有数丈,或矮不足三寸,间或有断头,缺掌,衣褶打烂,面目不清,不过还好,毕竟没有被光阴、贪心和暴戾一扫而光,留待这里与众人相见--原来佛与你我,竟如此有缘。
自此知道,古时候是真的能够诞生“即心即佛”的伟大人物的,是真的有人为了求得真理不惜断臂立雪的,这些都是真的,这里的大大小小的佛、菩萨、力士、金刚为证,这里的卢舍那大佛为证。那样柔软流畅的衣褶,那样恬静从容的面容,那样悲悯沉静的气息,那样的不悲、不喜、不怒、不嗔、不思、不虑、不忧、不惧,那是怎样的一张脸。
世间花如佛,尘外佛如花。
独一无二的花
读《圣经》,上面说:“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
心存疑虑,为什么不能说:“爱自己,就像爱你的邻人?”
朋友是虔诚的基督徒,最爱讲的故事是亚当和夏娃背负原罪流放茫茫大地,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养活自己。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神啊,请宽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对自己太爱,而是过于苛待。
食荤是罪,溺色是罪,肥胖是罪,矮小是罪,残疾是罪,口出狂言是罪,展望未来是罪,爱金钱是罪,爱官位是罪,饮酒是罪,作乐是罪,骄傲是罪,甚至女人生子受的痛苦亦是罪。所以要清净,要断荤,要戒色,勿贪吃,勿滥言,要超尘,要无欲,要宽谅,要穿马毛衬衣,要谨小而慎微。因为我们不完美。
完美,就是流云在它该在的位置,每一花一叶都在它该在的位置,每个人都做着它该做的事,每一个表情的绽放都无懈可击,一切一切,都循规,蹈矩,像一朵极致美丽的假花,不再生长,无需栉风沐雨,安放在水晶盘里,漂亮,却没有香气。
这样的完美怎么可能会存在。
可是就算不完美,也不妨碍我们骄傲地做自己。
就算不完美,也不妨碍我们谦虚地做自己。
骄傲,是因为我们活得过,死得值,对陷在泥渊里的人肯伸出手去,我们种出的粮食,不单是为了自己吃。
谦虚,是因为我们藉着帮助别人,实际上却帮助了自己。我家的猫,挠坏了我的沙发,挠破了我的脸颊。先生说它的命好,被我大雨之后捡回家,可是我倒觉得被成全的是我不是它。透过它我看见自己的善念开成花。
是以没有自我牺牲这回事,如果一个妈妈对孩子说:“我为你放弃了我的一生”,这种说法无意义,因为母亲并没有那么多可以放弃的东西,而这个“放弃”给了她想要的一种生活范式;如果一个小孩说:“我为我的父母放弃了我的生活,而一心的去照应他们”,这种说法亦无意义,他在“放弃”所谓的“自己的生活”的时刻,却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爱别人不是伟大,爱自己亦非自私,人便是这样的口是心非,似是而非。
而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礼遇:接受自己,喜悦地做自己。越接受自己,越喜爱别人,否则只会在口头上发表赞美,心里的那张脸早已经嫉恨得铁青,口生利齿,要吞肉饮血;越喜悦地做自己,越宽谅地待世界。有的人既奸诈又愚蠢,既残暴又嗜血,既冷酷又阴狠,既短视又无能,而你也未必不是里面的一分子。你越喜悦地做自己,就越宽谅地待世界。
所以,面对你的上帝,请不要做这样的祈祷:“我什么都不是,如果我做了任何善事,那是因为上帝的灵,是他赐予我大能与慈悲。”上帝通过你彰显它自己,是因为你的身上闪耀着神性的光辉。而你对自己的价值的否定,便是对他的价值的否定--上帝也不存在了。
一本书上说:“腿会跑而跃过一片土地,它们本身不能诠释在它们脚下的实相。脚对被它们踩碎的蚂蚁并不觉察,它们可能感觉得到那些草或人行道或道路,但草的本身或蚂蚁的独特的个别感受却不为脚所知,而脚是卷入于它们自己的实相里,只关怀那些与它们作为脚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的视角就有这样局部和片面的尴尬。
即便如此,每个人也是开在宇宙间的独一无二的花。
所以,不要轻信上帝、牧师、神父、上师、科学家、心理学家、朋友、家人的话--如果他告诉你,你是邪恶的,或是有罪;如果他告诉你,必须做些什么去赎罪,比如苦修,比如奉献,比如对自己大加贬斥,比如对命运俯首低眉。
人生是你的,去爱你自己,就像一棵树爱它绽放的每一片花叶,因为每片花叶都笼罩着神性的光辉--世界、宇宙、茫茫天际,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