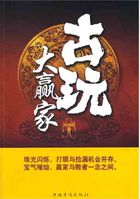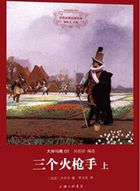雨下得很大,窗外的闪电有时立在山脊像一排栅栏,泄水道的铁皮被从房顶落下的水撞出了嘣嘣的鼓声。我合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快要睡去时,却被一个重雷震醒。足足有十来分钟,我静静地听着窗外豆大的雨滴落向地面的声音,穿过厚密针叶的沙沙声和落在柏油路上的啪啪声,它们像一个撩人的欲望,催促着我起床。
这是我住进医院的第三个月。住在明湖边的医院里,我并没有不幸的感觉。那年冬天,校医发现我得了肺病,直到元旦过后我才答应住进来。我刚庆祝完自己的十九岁生日,心里还留着一丝甜滋滋的感觉。因为家境困难,我能带到医院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两套换洗的衣服,十来本书,一条不常系在脖子上的素格围巾,和从同学手中借来的盒式录音机。值夜班的医生例行公事地绕完一圈,撇下病人,去值班室打盹去了。在睡意蒙胧的后半夜,医生习惯没有病人来打搅他。约莫有一刻钟,我站在门口,无法决定是否该到走廊上去?这时,同屋的病友吱吱嘎嘎翻过身,警觉地昂起头来。“你要出去吗?”他把手从被窝里探出来,瞅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表,“都这么晚了,你不舒服吗?”正当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时,走廊尽头的木门咣当一声,被大风吹开了。白色的碎花瓣被乱风裹挟着,在门槛上边飞舞。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我心存感激地应声跑了出去,木门被用捡到的脚栓重新插上。
扭头向后望,昏暗的走廊像一条低矮的望不到头的隧道。我缩着脖子,倒吸了一口气,心又扑嗵扑嗵地乱跳起来。我的腿几乎像被人拖着,向走廊中段慢慢踱去。她的病房门口没有装警示灯,使人想到她可能病得很轻,只会在这儿呆上寥寥几天。想到她可能就要离去,我马上有了一丝痛楚的感觉。病区娱乐室里亮着灯,却空无一人。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听见窗外的雨声停下来。我站起来,把电视机打开,浏览了一遍频道,又关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看什么。不久,走廊里响起了急促的“叭哒”“叭哒”的脚步声,朝这边奔过来。到了门口,来人似乎很诧异屋里有人,好奇地收住脚步。我没想到来人是她。雪白的脚下趿拉着一双平底拖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似乎意识到她手上的一大团卷纸怪难看的,马上跑开了。随后我听到了厕所马桶的冲水声。她再次路过时,又瞅了我一眼,眼睛深处有一种东西让人打颤。她的房门最后响了一下,走廊便沉寂下去。
看上去她的年龄与我相仿,个子很高,虽然穿着平底拖鞋,我刚才几乎不得不平视她。她回来时空着手,不可思议地用完了刚才的一大团卷纸。我想象她笑起来的样子,结果徒劳无获,也许是她的神情过于严峻的缘故。我怀着既喜悦又茫然的心情回到病房,吊在屋中央的灯竟然亮着,病友斜倚在床头,似乎在等我。“睡不着吧?!我也一样。本来这是个睡觉的好季节。”他边说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
“你刚才碰见她了?我听出好像是她的脚步……你觉不觉得她很漂亮?”他的语速很快,略显焦虑和不安。我立刻尴尬地脸红起来。他是北方人,说话一向无遮无拦,不像我这个南方人,喜欢心底藏着曲曲折折的秘密。不过听到病友提起她,一丝欢愉的感觉还是马上传遍了周身,心情也愈加激动起来。风吹打门窗的声音小了,我脱下拖鞋,又换上皮鞋,提议一块出去走走。那晚,我和他下到坡下的长长湖堤,话题一不留神便回到她身上。他比我更清楚她入院的确切时间,他抖搂的情况我几乎全是第一次知道。放射科医生向他透露的秘密,他忍不住说了出来。后来他唠唠叨叨用“白艳”、“丰润”形容她的身体,就好象他是那位医生,亲眼目睹过她的肉体一样。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对这样露骨地谈论她,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她得了一种奇怪的急性肠炎,教我们用警示灯的那位高个儿护士向他透露,她的住院期还会延长。
睡觉前,我一直被这个消息激动着,想到她还不至于很快离去,心里的痛楚便大大缓解了。
次日我起得很晚,几乎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朝南的床头、桌子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护士在床头柜上细心摆了两个瓶盖,里面搁着早餐和午餐应服的红、蓝、白三种药片,瓶盖下还压了一张检查表格。看到这个表格我才想起,今天是进城复查的日子。远处清清朗朗传来病友和高个儿护士的嬉戏声。不一会,我看见伙房的张师傅扛着一根晾衣杆,向声音方向匆匆走去。我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把羽毛球打上了房顶。
我从病房出来时,在花园的小路上碰见张师傅。他双手已经闲着,老远就向我大声打招呼:
“书生终于起来啦?!”
“嗯。”我局促不安地应了一声。
“你今天的气色很不错啊。”
“是吗?可能我睡过头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大个子对你真是不错啊。”
“是是,他老帮我打饭,他为我做得实在太多了。”我又一次不好意思地说。不到两个月,他已经习惯用绰号来称呼我们。这是我和大个子开的头。住院不久,我们给病区许多人起了绰号。高个儿护士叫白杨树,她是护士中把背挺得最直的一个。有位圆脸、轮到说话脸就涨得通红的护士,被我们称作“红药片”。还有两位护士因为爱笑和不爱说话,分别被称作“猫眯”和“花瓶”。我们送给两位主治医生的绰号,虽然有些不恭敬,却被护士们在背后兴奋地叫着。那位浙江籍医生戴着七百度的眼镜,因此被我们称作“三环”。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医生,因为那句著名的谚语,被称作“九头鸟”。我和大个子的绰号是白杨树起的,虽然平淡无奇,他们仍当面叫得起劲。后来我和大个子怀疑,她起两个无伤大雅的绰号,是不是有意讨好我们?
张师傅是医院聘来烧饭的临时工,家住安徽霍山。他老婆不能生育,是他头等烦恼的事。他说来这里打工,是为老婆挣些医疗费。有一阵子他老婆成天熬偏方,喝得脸儿蜡黄。不过,我觉得他来这里,更多是为了躲避在乡下遭受的断后的耻辱。他没有绰号,属于医院里少数几个例外,也许大家不忍心在他遭受断后的重创后,再刺激他了。
他夸完大个子才告诉我,病区的小澡堂下午三点供热水。我没想到事情这么凑巧。那个年代,医院的煤是定量供应,大约一周病人才能洗上一回澡。我咂着嘴,十分着急地说:
“这可怎么办,我下午要进城去复查。”
“噢?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师傅把脑袋稍稍低下,沉吟片刻,又说:
“这样好了,下午还有个女孩也进城,我干脆给你俩留五十升开水,怎么样?”
我马上高兴地拢住他的肩膀,“你真是个大好人,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说完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大个子给的香烟。
“不好意思,虽然拆了封,但没抽几支,这是地道的好烟。”
我把香烟塞到他手上,但他不肯收。他推辞了老半天,见我的态度更坚决了,才把香烟拿在手上。我借口三环在等我,顺着小路出了花园。
太阳这时被低矮的疾云遮住了,空气中有了一丝凛冽的寒意。路旁几株低矮的梅树下,落了一地的花骨朵。我不禁为尚未盛开的梅花惋惜起来。到了有石阶的坡顶,我停下来。站在坡顶崖边,能直接看见明湖对面的大学校园,朦朦胧胧的雾气中,隐约浮现出几个垂钓者的身影。
这座医院建在明湖西边的台地上,有三条石路从台地蜿蜒到湖边。湖边春色让睡得昏沉的脑袋变得清湛起来。我一屁股瘫倒在岩石上,再也不想动了。我计划就这样躺上半小时,似乎期待能让心头一跃的那个声音出现。就在这时,吃午饭的哨声像女人的一阵尖叫,划破了湖边的宁静。哨子一声比一声紧,催得我不得不站起来。我见过张师傅使劲吹铁哨的样子,两个腮帮鼓得像青蛙肚皮。不见到病人从病房踱出来,他的哨子是不会停的。我的脚步越迈越快,我忽然想到,这回不能再让大个子帮我打饭了。
没到病房门口,我的心又倏忽乱跳起来。她的声音分明来自我和大个子的房间。站在门口,我一下愣住了。平时摆在窗前的一张桌子,被抬到了屋子中央。大个子、白杨树和她各占了桌子一边,没人的那边不用说是留给我的,上面摆着大个子帮我打好的午饭。大个子站起来向我打招呼,我脸红地说: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
“这回可是蒋惠蓉帮你打的。”大个子指了指她,然后装着我对她一无所知的样子,介绍起她的情况来。我向她道了谢,有些疑惑地坐下来。我想着她帮我打饭的情景。渐渐地,一丝痛楚又从心头掠过。从打饭这件事,我感到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们后天乘三环不在,可以去一趟汤山温泉。温泉后面有一个碑林,也值得一看。除了我们,还可以叫上轮休的花瓶,不过人不能多。我就怕后天有雨,南京的春天一天一个样,所以大家都注意听着天气预报。如果没什么天气意外,我想出游就定在后天吧。不过,这回可不能再让三环知道了。”大个子把筷子往桌上一扔,表明他的午饭已经吃完了。
“为什么不明天去?三环明天刚好要进城开会。”白杨树有些迫不急待地说。
大个子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明天是清明节,上坟的日子。再说也不吉利,我妈特在乎这个,我觉得不管信不信,还是避开这天为好。”白杨树一听,忙改口道:“那就按原计划吧,到时候午餐我来备。”
下午两点,我们一行五人,随医院的救护车进城。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人。随行的放射科医生,一路上拿她开玩笑。在车上,她把始终盘着的头发放下来,有着微黄光泽的长发马上遮住了她的脖子,给人格外丰美的感觉。直到这时,我才想到“缘份”这个字眼。上午张师傅提到进城的女孩,我的脑海曾倏然闪过她的形象,没想到事情果然如此。她坐在和司机同排的座椅上,本来前排的沙发座位是特意留给病人的,但我装着毫无兴趣的样子,走到后排。放射科医生高高兴兴占据了那个位置。他说俏皮话时,她一直咯咯咯地笑,有时还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捂着脸。我虽然望着窗外,注意力却始终在她身上。起先我为从后排始终看不到她笑的样子,感到遗憾。后来,我为医生的话在车内激起的每一阵反应,感到格外难受。
途中,又下了一场小雨。远山显得更朦胧了。从车窗望去,一切都像悬浮在云中。车子距目的地还有一小时。大概路失修颠簸的缘故,原先起劲说话的人,都疲惫地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只有她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不时向司机打听车子的去向,还有多远。实在无聊了,她就问司机车上操纵杆和表盘的用途。司机的嗓音不高,她不得不把脑袋凑过去,长发几次卡进了操纵杆的螺纹里。后来,她索性把长发重新盘起来,这样看上去她像添了两三岁。
车子持续地颠簸,对患肺病的人是一个考验。我疲惫至极,却没有心事睡觉。我把那本在手上翻了几页的小书,又塞进上衣口袋里。大概想到她想聊天是个机会,于是鼓起勇气向司机打听几点。果然,听见我的嗓音,她把头扭过来,双手趴在椅背上,下巴陷进柔软的皮革里。
“怎么,你也没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笑了。我没想到她笑的样子如此生动,与昨晚或上午那种严峻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她的脸第一次跟我凑得这么近。我第一次放肆地直视她的小酒窝,大眼睛,流星一样划过眉骨的细眉,我真的说不出究竟哪个更美。
后来,她看到我口袋中露出一角的小书,便叫我拿给她翻翻。这本《圣歌集》的歌词倒不吸引她。似乎她对我为何有这个意想不到的爱好,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我明白,向她直接解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娓娓道来,给她讲起了圣经故事。因为夜间受凉而变得沙哑的嗓音,居然让她听得津津有味。她忍不住拿起小书翻了翻,接着央求我再讲一个。这样一连讲了三个故事,那些睡着的人才陆续醒来。
“小意大利,你快看窗外!”放射科医生醒来时顺手拍了拍她的背,我觉察到她的身子在往前躲。同时,这个绰号也让我大吃一惊,似乎生活在她的圈子以外的人,只剩下我了。窗外爆发出一阵掌声,一群人昂着脖子,团团围住两个表演气功的人。我们的视线越过了黑压压的人头,看见了圈内的表演。也许那种吞食玻璃的场面,实在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竭力闭上眼,仿佛为了挡住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远处不时有被阵风掀起的蒙蒙尘土,地上没有丝毫下过雨的迹象,这种小面积降雨的情况,在江南倒是常见的。
救护车开进省立医院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那里的医生似乎等得有点不耐烦,放射科医生挟着一摞资料,诚惶诚恐地跟他们进了片库。那位搭车者和司机一起出了医院大门。一阵风把放射大楼的玻璃窗吹得哐当作响,天上有几团低云压了过来。我没想到,她觉察到了我刚才的一丝不安,和我说话时,好像还在尽量地回忆刚才的情景。
“我和你一样,也怕看那种场面。”她用安慰的口吻说道。
“可能以前太受家人保护吧。”
“你是不是从没打过架?”
“是的。”我有些羞愧地承认道。
“我爸也是的。”她的声音变小了,柔美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你爸?”我不敢相信地望着她。
“真的很奇怪,你和我爸简直就像是一个人。”说完,她的脸上露出了吃糖似的甜滋滋的表情。但我并未因此得到一点宽慰。想到她对我的好感另有原因,我不由地沮丧起来。
这时,大楼的走廊里传来了放射科医生的喊声,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小意大利!小意大利!”他把她的检查安排在我前面。我离开墙边,踱来踱去,最后听见楼里嘭的一声门响,检查室那扇厚重的大门关上了。我的额头冒出汗来,好像我就在她身边,会亲眼看到她受辱一样。想到那双贪婪的手,会在她身体上摸来摸去,我的心里平添了几分烦恼。
全部检查完,天色暗淡了下来。救护车在颠簸的公路上,打开了防雾灯。车内漆黑一片,谁也看不清我板着脸。像来时一样,车内热闹了一阵,又归于平寂。看着她瞌睡中渐渐倒向医生的背影,一股寂寞向我袭来,好象眼前是一个揪心的往事。
第三天,我没有参加去温泉的出游活动。大个子清早在屋里折腾时,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躺着不动。但他们走了以后,心里又非常难受。无论是用被子蒙着头,或掀掉枕头,我都无法继续睡下去。碎花窗帘蒙着的窗户,仍亮得晃眼。我把那本《圣歌集》轻轻在手上掂量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猫眯十点来拖地时,我问她是不是有谁住进来了?她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神情,她说那个书商很怪,是自己花钱住进来的。
“他疯了,为什么不去住城里的医院?”
“听说刚离婚,又非常害怕得这种病。他知道三环治好了几个学生,就跑过来了。”
“噢?这人倒挺有意思的。”
“听说他老婆就因为他疯疯癫癫,才和他离婚的。”
中午吃饭前,我像笼中的一只鸟想找到出口似的,找到他的门。心想在这个无聊的地方,碰上个怪人倒是挺开心的事。他显得很疲惫,并不请我坐下来。他指着身边的一堆书说,得我们这种病的人实在很不幸,一生都要受它拖累。他坐在一堆医学书旁边,脸儿蜡黄,声音缓慢却让人感到他的不安。通常这种天气根本用不着取暖,屋里却开着一台石英管取暖器。
“我这样子,是不是把你吓着了?”他忽然有些歉意地指了指凳子,请我坐下来。
“最要紧的,是找到能对症下药的医生,这跟医院大小没关系,也许救你命的医生,就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医院里。不过,他治好了别人,未必就能治好你。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种病的治愈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就连那些自愈性的疾病,也经常有死亡的例子。所以,每种病都有人治好也有人死亡,治愈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怎么样?”
他说话的样子令人担忧,明显带着偏执。我想,他不会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他见我不吭声,便有些着急地打听:
“你吃了刘医生的药,效果怎么样?”如果三环站在我面前,我也会像他那样毕恭毕敬地称呼“刘医生”。
“你没必要这么紧张,这种病有特效药,疗效很确定,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带你去看我住院以来的胸片,病灶都快消失了。”
“唉……你太乐观了。”他为我叹了一口气,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我带他去放射科。
“你看,我这里有这种病的资料。”他随手抓起一本书递给我,但我没有一点要看意思,原封不动把书摆在了桌上。他无奈地对我一笑说,那我们走吧。
他计划看完胸片后,邀我去镇上吃饭。路上,他竭力打消我要回来打饭的念头。我们到达放射科二楼时,从门缝瞥见她正慌乱地整理着衣服。我大为震惊,但听见她在屋里喊:“在门外等一会!”我的心才放下来。她没去温泉!这个意外让我又惊又喜。一刹那我又想到了“缘份”这个字眼。我们在门外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屋里才又喊:“请进来!”
高脚凳上规规矩矩坐着放射科医生,他埋头写着病历,就好像他是男主人,让女主人穿戴好了来迎接我们。
“真是怪事。”
放射科医生自言自语嘟噜了一句,然后抬头跟我们打招呼。今天她穿了一件棕色男装,又盘了新的发式,让人觉得那片晴空就在她的脸上。看到我时,她把嗓音压到别人难以听清的程度:“怎么,你也没去?”她的样子比刚开门时显得更高兴了。那个怪人和医生趴在灯箱边上看胸片时,我乘机问起她下午有什么安排,问话的口吻似乎能让人觉察到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不料她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似乎为了不让人看到她的表情,她马上俯身下去系鞋带。等到重新站起来,她向我解释,下午有个亲戚要来看她。听了这话,我感到再难以开口问她什么。我茫然若失地加入到灯箱那边的谈话中。
午饭后,我拉上窗帘又睡了起来,心乱如麻,像上午一样难以入静。躺了不到一小时,又犯起了偏头痛。下午三点,那位怪人过来回访我。进来时他高兴地直嚷嚷:“喂,喂,我们那边总算有点动静了。”自从看了我的胸片后,他的情绪似乎有些好转。见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就把我推到门口的走廊边。走廊里没有一人,轻微的啜泣声隐隐从尽头传来,不时被一位男人的说话声打断了。我渐渐辨出是她在哭,心里又担忧起来。
“没事,只是小吵,这种事别人可不好管。”他未经我同意,就动手拉我床头柜的抽屉,翻出来一副扑克牌。
“你听清他们说什么事了吗?”我焦急地问道。
“没有。单听声音,估计事情不大。”
等我无奈地坐回到床边,他在桌上把牌分成了三沓。
“来来,我们打‘跑得快’,小赌一把,怎么样?”他提出被关住的每张牌赔一毛钱。话刚出口,我点过两次头了,可见我的心思根本不在打牌上。有几回,我抓到好牌,竟也打输了,最多一次被关了十一张。每次出牌,都要被他催促再三。走廊尽头的声音一直牵动着我的思绪,后来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淹没了。之后的寂然无声,使我更加难受。
“好了,到此为止吧。”我把牌往桌上一摊,站了起来。他脸上露出十分遗憾的神情,把牌整齐地摊在桌上:“你看,本来我又要赢的。”这时,走廊里重新响起了脚步声,朝我们这边移动过来。最后,是她站在门口,神情有些黯然。看到散了一桌的扑克牌,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求我们陪她打几圈,我、怪人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她打牌富有灵气,每张过手牌都牢牢记在心上。每次赢了,她都灿然一笑。她的形容很能打动人,连身上的香皂味也屡屡叫人分心。我和怪人不便在她高兴时,去问刚才那件让她伤心的事了。我好不容易开始嬴牌,她突然抬头问我几点。
“不好,我得走了。”她连忙把牌摊开,慌乱地跑了出去。怪人和我面面相觑,接着怪人也跟着出去了。
吃晚饭时,大个子没有回,我帮他打了两碗饭菜。我从台地下到湖堤上散步,看见远处的垂钓者纷纷收竿,准备回家。我走到石桥前折了回来,在湖边坐了一会,又攀上台地。进了花园,碰上了气喘嘘嘘的大个子。
“总算找到你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票,塞到我手上。
“今天晚上,你、我、白杨树、小意大利,一起去镇上看电影。她们在电影院里等我们,你快先去,我擦个身子就来。”
也许我的表情让他感到不踏实,他过来抓住我的肩膀:“别犹豫了,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我虽然没彻底弄明白他的话,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去小镇的路上,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影片放映了五六分钟,我才到达那里。借着银幕的反光,我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没想到座位上只有她一人。
“白杨树呢?”几乎我问话的同时,她也问我大个子怎么没来?不来的原因似乎是一样的。影片实在糟糕,让人感觉购票者根本不在乎影片是什么。借着跃动的光束,我看见她咬紧牙关,神情严峻。
“我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她忿忿不平地说。然后拉我一起出了影院。她谈起以前也遇到过这类事情,总有被人耍弄的感觉。我看见她的脸上,生气的线条竟格外生动。每逢她数落大个子不该这么做时,我就想,是不是她为只看到我感到特别失望?
入了春,湖水开始慢慢上涨,这种涨势会一直持续到夏天结束。走在湖边,眼睛也感到清亮起来。从低处眺望灯火通明的医院,它就像挂在高处的一盏枝形吊灯。起先我只在被问时,才答上几句。后来她把话题朝我身上转,谈话就亲热起来。我告诉她,自己学的是造纸专业,她便感慨读大学对她来说,是上天的难事了。接着,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她的坦率让我吃惊不小。我不敢相信,今年她有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位三岁男孩的母亲了。她的婆家在离这儿不远的小石镇,高考落榜后,因为家境困难,她草草嫁到了这里。
月光下,她的脸、洁白的脖子,更加使人魂牵梦萦。她说十三岁时,一个歌舞团相中了她,她跟着歌舞团练了半年舞蹈,后来又主动离开了。她嫌团里的男女关系过于随便。我放弃了一度想问她下午那件事的念头。看到她还怀着从前的愿望,心里不忍揭她的旧疤了。过了石桥,我们到达了台地东侧,她的步子慢下来。我走在她的前面,但她像等后面什么人似的,越走越慢。见她陷入沉默,我更不知该说什么。脚步声使空气凝重得透不过气来。到了花圃的玻璃房,她忽然停下来,她说:
“想不想知道,那些护士对你的看法?”起初我非常惊讶,然后又提心吊胆地点点头。
“她们背后都挺维护你的形象。”
“是吗?不过,我,我倒挺在乎你的看法。”以前我可没这么大胆过。
“我?我……对你印象当然不错。”说这话时,她的眼睛转向另一边的玻璃房。听到张师傅在后院哼黄梅戏的声音,她又挪动了脚步。段子哼完,万赖俱寂。我怀着不安的期待,在通往后院的小路上站住了。踌躇中,她的眼里似乎也闪着期待。忽然她大方地伸出手来,待我上前握住,她说:
“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以后欢迎你和大个子到我家里来作客。”
她说话时喘着气,仿佛胸口哪儿不舒服。当我把另一只手也搭上去,她拘束又礼貌地把手抽走了。她一溜烟地往病房跑,让人感觉她似乎快要撑不住了。
我根本不管屋里有谁,在干什么,两眼一闭倒在了床上。大个子摸了摸我的额头,确认我并未受凉发烧。放射科医生好心查看了一下我的瞳孔。然后两个人千方百计想引我说话。他俩彼此猜测:我和她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医生为平时检查中不得不触摸她的身体,表示了礼貌性的歉意。他用这话开导我时,我的心又像针扎似的难受起来。医生走后,大个子从壁柜里拿出一包东西,说我的同学晚上来过。包里有一袋藕粉,一盒巧克力,两盘邓丽君磁带,一本小说。看到这些精心选购的物品,一种忧伤又亲切的感觉仿佛被从远处的校园唤到了床前。
上午八点,我被大个子叫醒。他穿得出人意料的讲究。他把我的衣服朝我床头一堆说:“快,小意大利要走了!”这个消息一下把我震懵了,刚刚醒来的平静的心,一下又难受起来。我几乎在他的帮助下才穿好衣服,懵懵懂懂跟他到了户外。张师傅拎着网兜,和她并排走在前面。后面五、六米远,跟着个拎着皮箱的男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虽然穿着体面,满面却胡子拉碴。估计是她昨天说的那位亲戚。我和大个子在花园追上他们时,她似乎又惊又喜。
张师傅递给她一张字条,托她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他在小石镇的一位姑妈。她如数家珍地说,他姑妈是镇上以前拉洋片的那家,现在他姑妈家里还有不少那样的小画片。后来,她看着我,主动和我搭话。似乎她特意着了淡妆,稍稍加黑的眉梢,使她的脸有了一种不可冒犯的神情。那位男人走近时,她表情自然地向我们介绍,那是她的丈夫。我和大个子礼貌地点点头,似乎在他面前我们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本来我兜里有一盘圣歌磁带,想送给她,可是当着她丈夫的面,我死活没有勇气拿出来。
张师傅回去烧水去了。我和大个子坐在崖边的岩石上,继续目送他们。湖风又起,差点吹落了她的丝巾。到了人影模糊的石桥前,她停下来向我们招手。过了石桥,他们的背影就被拱形桥面和一排刚刚泛青的垂柳,彻底挡住了。
20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