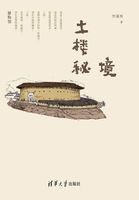那是三十多年前夏初的一天,父亲去县城的一个爷爷家,他是我爷爷的叔兄弟,在当时的一个公社里做领导。父亲临回,那个爷爷让父亲捎一瓶酒给我爷爷喝,这瓶酒就是古贝春。当时我们这儿喝的酒一般都是代销店里卖的散酒“八毛辣”,就是八毛钱一斤的地瓜酒。招待贵客也就是一块二一瓶的“兰陵大曲”和“景芝白干”。像古贝春这样高级的酒,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眼里,就相当于茅台了,那是只有高级人物和贵客才能喝的!
父亲刚到村口,遇到了我们的村支部书记庆余。庆余是我们村的一把手,骑着辆大轮泰山自行车,看样是刚从我们公社开会回来。他问父亲干什么去了,父亲说去看我那个当领导的爷爷了。庆余和父亲是平辈,叫父亲哥哥,就问:“咱叔给你回了点啥?”父亲实话实说:“回了瓶酒。”一听是酒,庆余来精神了,父亲就把那瓶酒从书包里拿出来,庆余看是古贝春,发出一声惊讶:“好酒啊!”接着对我父亲说,今年过年时,他去公社书记家拜年,书记就用这酒招待的他!之后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问父亲:“今天大方瓜说他媳妇的爹来看家,你知道不?”
父亲摇摇头。
庆余说:“听说闺女的爹要来看家,大方瓜的爹昨天就安排我,让我今天去陪客。所以,会没开完我就回了。”父亲问:“大方瓜也有25了吧?”
庆余说:“28了。这个只咱知道,对外人,只说23!”父亲说:“我家和大方瓜那边还沾点亲,知道,大方瓜长得不怎么的,家景也不好。当然找媳妇就难!”
庆余说:“是啊,所以他找媳妇咱们都得帮他!昨天,大方瓜家里的布置都是我给他借的。三屉桌是借葫芦家的,红灯收音机是借欢乐家的,洋车子是喜红的,手表也是喜红的,就是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喜红的。喜红是柴里煤矿上的工人。可巧,今天喜红歇班。这些都是我昨天出面给他借的,不然,别人借,喜红不一定给呢!”父亲说:“是啊,你是一把手,面子大,你去借,谁敢不给?!”
庆余裂开大嘴笑了,说:“今天为了让大方瓜媳妇的娘家爹满意,我考虑了,还得向你借样东西!”父亲说:“我可是个穷光蛋,你向我借什么啊?”
庆余问:“你要有,是否给?”父亲说:“咋会不给呢?只要有,一定给!”
庆余用手指了一下古贝春,说:“今天得借你这瓶酒用用!”父亲一听忙把酒抱在怀里说:“这是我叔给我爹的,要是借给了你,怎么给爹交代?”
庆余说:“你就说借给我了,借给我给大方瓜待客了!”
父亲手里抱着酒,不想给。庆余哈哈一笑:“你放心,你这一瓶酒,我只借你二两,多了不要,行不?”
父亲不相信,说:“真的?”
庆余说:“我啥时骗过人?”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酒瓶的脖子处,说,“我说到做到,就喝到这地方,多一点也不喝!”
父亲不相信:“真的?真只喝这么一点?”
庆余说:“就喝这一点,要多喝一点,谁就是这个!”说着用手学了一下乌龟爬的动作。
父亲看庆余已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并且不是给自己喝,是为大方瓜待客才借的,要是再不借,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说:“那我借给你,就按你说的,我只借那么一点!”
庆余听父亲借给他酒,高兴地一拍父亲的肩膀说:“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点酒,我敢保证,大方瓜的媒保证没问题!”
父亲问:“真的?”
庆余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真的!”并说我父亲是个识大体的,他只要在台上一天,就不会亏待我父亲!
那天晚上,庆余把那瓶古贝春酒给我父亲送家来了。果然只喝到他指的那个地方。当时我爷爷在,就问庆余客陪得怎么样,大方瓜的媒定下了吗。
庆余说:“定下了!说起来多亏了你的酒!”
爷爷说:“只要能定下,你就是把这一瓶子都喝了也没关系!一瓶子酒能给咱们村进个媳妇,值!”
庆余说:“哎呀,说实在的,今天要没你的古贝春,还真的定不下呢!”
爷爷就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庆余就说开了,说:“今天来相家的是大方瓜的老丈人。老头子一辈子就爱杯中之物。当我把酒拿过去,当然了,只拿了二两。”我父亲问:“不是一瓶吗?你怎么只拿二两呢?”庆余说:“这么好的古贝春我怎么能一下子让一个人喝了呢?这一瓶子,能办好多的事呢!我先从这瓶里倒出八两,倒在我家里的一个空酒瓶里,之后我就拿着这装着二两酒的古贝春去了大方瓜家。老头子看样是不多满意,想要走,大方瓜正在劝留呢。我给老头子说:‘这个酒是咱滕县县长招待贵宾稀客的招待酒,你老人家来了,我今天专门给你拿来了!’我拿出了这瓶古贝春,大方瓜的老丈人直盯着酒瓶子看。我说这瓶酒可是待过好几个大人物,最低的也是公社书记,你老人家是贵客,我知道大方瓜的老丈人是喝家子,就拧开了瓶盖子。那酒可真香啊,马上就漫开了。大方瓜的老丈人使劲地抽搐了两下鼻子。要没这个酒,大方瓜的老丈人有可能就要走了。就是这个酒把老头留下了!”
“这么说来,大方瓜的老丈人是个喝家子,这二两酒怎么能管用呢?”我说,“咋也不够你们喝的啊?”
庆余说:“我能喝,那得看在什么地方。我是去给大方瓜陪客的,再说了,就二两酒,我能喝吗?一喝不就没了?!”
父亲问:“那你是怎么用这二两酒陪的客呢?”
庆余用手指了指脑袋说:“要用这个。客人一般是很谦虚的,我就在谦虚上做了文章。”
爷爷说:“快说说,你是怎么用二两酒陪的客人!”
庆余说:“一上酒桌,大方瓜的老丈人就给我客气,说他不能喝,我就把瓶里的二两酒都倒在他杯子里,说:‘我知道你老人家不能喝,可今天是喜日子,我不要你喝多,就这二两!多一点也不叫你喝!不然你喝多了,别人不得说我,说我没正经心眼!不会陪客!’大方瓜的老丈人想说的话让我一下子堵到肚子里,就给我客套,说真的喝不多。我知道他那是客套,就说:‘我今天来陪你,表叔,你别忘了,我是这个村子的一把手,别说是这二两酒了,就是敌敌畏,六六六药水,你也给我干了!’那老人先是一点一点地喝,边喝边咂舌说好酒好酒!最后一饮而尽,然后咂咂嘴,说:‘好酒啊!’我一看老人喝了了,就说,我一上来就给你说:‘只让你喝这二两,多一点也不让你多喝!不然咱就说好了,你只要愿意这个媒,下一次来,还是我来陪你!还是给你喝这古贝春!’大方瓜的老丈人一听说:‘好,那咱就说定了,这个媒,本来我心里有点含糊,既然村里的一把手来陪我,并且又拿来这么好的酒,我要是再拿捏,就有些不地道了。好,这门婚事我应了!’你看,叔,这个事就这样定的!”
庆余说得绘声绘色,说得爷爷笑逐颜开。庆余说:“这酒没进家,就撮合了一门亲事,真是有缘分的酒啊!”
爷爷把酒瓶盖子打开,浓郁的酒香漾了出来,庆余抽搐几抽鼻子说:“好香啊!”爷爷看到庆余闻酒的模样,从一旁拿起一个杯子,倒了满满一杯,端给庆余,说他陪大方瓜的老丈人有功,奖给他的。庆余说什么不喝,又把酒倒进瓶里说:“这么好的酒,还能办好多事呢!我要喝了,那可是糟蹋了!这可是咱乡下的茅台啊!”临走时,庆余又回身安排我爷爷我父亲,说:“这酒你们尽量不要喝,给留着,村里以后用这酒的事多着呢!这酒能办好多事呢!”
爷爷就把这瓶酒交给了父亲,他知道父亲不喝酒,要是放在他这儿,不知什么时候酒瘾一上来就把酒喝了,交给父亲,安全!
父亲就把这八两古贝春拿到我们家放着。没多久,一把手庆余到了我家,说县里下来个领导,来村里蹲点。这个领导是县民政局的,掌握实权,给咱们村批点钱了物了什么的,他说了算。今天给他接风,来借二两古贝春。父亲找来了一个酒瓶,就从古贝春那瓶里倒出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交给庆余。之后庆余就拿着这酒瓶子走了。还没出大门,父亲就追上说:“喝完了,你要把酒瓶子还回来!”
庆余说:“这个你放心,我还指着这个酒瓶子办事呢,咋会不还呢!”第二天一早,庆余就把古贝春的空酒瓶子还回来了,说:“这二两酒起作用了,民政局的领导答应了,说只要他回去,就给咱们村多批一些救济物质,每家多批一点布票和粮票。你放心,我用你的酒,到时候,多给你家三尺布票!”
之后庆余又安排父亲,一定要爱惜酒瓶子,保证像新的一样!父亲就把庆余还过来的古贝春空酒瓶擦了又擦,把剩下的六两酒又倒了进去。后来这六两酒又给我们村办了几件事:进了三个媳妇;一把手还用剩下的一点酒招待了县里粮食局的两个领导。领导一高兴,给我们村多批了一千斤粮食。那年秋天,大方瓜就成亲了。年后,大方瓜的老丈人来走闺女,指名要上次陪他的一把手庆余来做陪。那时候,古贝春早就只剩下空瓶子了,天天被父亲擦得锃亮放在八仙桌上。庆余来我家拿酒瓶,一看没酒,忙从兜里掏出五毛钱,让我拿着古贝春的空瓶子去打代销店里打五毛钱的“八毛辣”,打了六两多。之后他就拿着这半瓶多酒去了大方瓜家。
没想到,大方瓜的老丈人喝着一个劲地说好酒好酒。说得庆余的脸红得像猴腚。好在有酒遮着,不然,能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