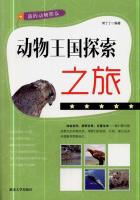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年青人因为人家说他“不觉悟”,气的三天没有吃饭。“不觉悟”算是最不名誉的一件事,每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交朋友,谈恋爱,都要先看对方是不是觉悟了的。趣味相投的年青人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要考问彼此的“人生观”;他们很干脆地看不起那些自认还“没有人生观”的人,虽然对于“人生观”这东西他们自己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在当时,也就有些大人先生们看着不顺眼,嗤之为“浅薄”,在今天看来,也觉得不免“幼稚”。然而,何尝不是幼稚得可爱?罗丹的有名的雕像叫做“铜器时代”,我们那时的青年就好比是“铜器时代”;这是从长夜漫漫中骤然睁开眼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异而狂喜,陡然认识了自身的价值,了解了自身的使命,焦灼地寻求侣伴,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这样的义无旁顾,一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正是古代哲人所咏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难道还不够伟大?
在那时,“觉悟”与“不觉悟”的,如同黑白一样分明。鄙夷权势,敞屣尊荣,不屑安闲,对于那些抱着臭老鼠而沾沾自满的家伙只觉得可怜,掉臂游行于稠人广座之中,旁若无人的发议论,白眼看天,意若曰:“你们这一套值得什么,我有我的人生观!”这是“觉悟者”的风格。诚然这不免是“幼稚”罢?然而何等可爱!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幼稚”的人们,冲锋陷阵,百炼成钢,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
在那时,没有这样的青年:听他的议论,头头是道,看他的行事,世故深通,一则曰:“这是应付环境”,再则曰:“为了生活,不得不然”,真人面前说假话,放一个屁也要“解释”出一番道理来;你说他是“罗亭”么?他没有罗亭那样热情坦白,说他是“阿Q”么,他比阿Q多些洋气,多会一套八股,多懂若干公式。而尤其不凡的,他会批评二十多年前的年青人:幼稚!当然,他是老练的;可是也老练得太可怕了!
在那时,明明是“少爷出身”的人,总想人家不当他是“少爷”,忘记了他是“少爷”,总想从自己身上抹去这“少爷”的痕迹。在今天,有些明明不是“少爷”或者当不成“少爷”了的,却总想给人家一个印象,他是世家子弟,他是百分之百的“少爷”,好象他那一套漂亮的前进词令唯有在“本来是少爷”的背景之前乃更漂亮似的。
二十多年前的少女视涂朱抹粉为污辱,视华衣盛饰为桎梏;二十多年后,少女成为中年妇人了,可又视昔之以为“污辱”及“桎梏”者为美,为“场面”,而且说起从前那样厌恶那些“污辱”和“桎梏”,总带点忸怩,总自谦为“幼稚”,若不胜其遗憾。而且还有理由:“你看苏联女人也都浓妆艳抹!”五年计划以前苏联女人的妆饰如何,当然不谈。《官场现形记》描写一位“提倡俭朴”的巡抚大人,属员们穿了整齐些的衣服来见他便要挨骂,结果是省城里旧衣铺的破烂官服价钱比新的还贵。二十多年前屏华饰而不御的那些女青年当然和这位巡抚大人在动机上大有差异;至多只能说那是“幼稚”,然而这样的“幼稚”在今天的女青年群中可惜太少见了。
我想起这一切,真有点惘然,我并不愿意无条件拥护二十多年前那种“幼稚”,然而我又觉得,和那时的“幼稚”一同来的坦白,天真,朴素,勇敢,正是今天若干极想“避免幼稚”的年青人所缺乏的。不怕幼稚,所可怕者,倒是这一点欠缺!
1945年“五四”前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