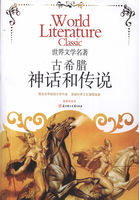爱情故事看起来应很空灵,尤像欣赏天际的彩云。
1995年初春的雁城,天上却没长出彩色的云骨朵儿来。一层层烟云雨雾像一首首离愁别歌的韵脚浅浅地游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天空里,睁大了可视的目光,却见不到一丝鸟儿的片鸿。
那时的他,长发可束。可是他却让它很飘很柔地挂在脑后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很难说得清自己此行的目的。望着窗外变幻莫测的境致,他觉得自己是那么轻飘,像一片云,而又更像一眼风。
车过株洲,车过了长沙。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什么呢?陡一发现,他还以为自己在问自己呢?待他回神来,抓住了这一句问候言语的留香,他惊奇地发现它来自对面的又一袭长发。
我在想什么呢?他把眼从女孩芬芳的长发移开,再落到女孩的手上,那是一双很纤细柔亮似乎裹着一层浅浅羊脂的亮色的手!哦!他说,我在想手有时会说些什么呢?他想笑出一个久违的笑的模样来。
真的么?女孩先笑。好看的手很弧线地把手中的书本悄然无声的合上,一股浅蓝色的墨香从她手指间跳落开来,很空灵地柔伏在他俩的面前,她桃面样笑,你想象了什么呢?
他看见了春天里第一朵云骨花朵儿!
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至少会在这个孤寂的旅行的过程中,它会带给自己一点有目的思考的快感。
他那时是一个很诗化的作家,很不幸的是他正经营着一个已经肯定不诗化的故事。他给她写了几封长长的信却留不住她,她明天就要飞离这个国家。
我在想,他终于笑了,一只手与书本告别的语言:哦,亲爱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女孩又笑了,是那一种很有诗意的浅笑。车,铿锵铿锵──流动的气质里,女孩的眉角荡漾。你会很快乐!女孩轻莺。
冷不丁又一句,吓了他一大跳,睁大了眼再看,女孩仍掬笑,你一定很快乐!
我会很快乐吗?他问自己。
此后,他俩不再答言了。他的眼又转向了窗外,她的手又轻轻的翻开了书页,车过武汉,女孩下了车,却给他留下了一本书。他没想到,那竟是一本徐志摩的诗集。他想叫住她。告诉她,我会快乐,那么我的快乐在那里呢?他又怕惊住女孩来,就让一个久远的神话降临吧,他想。
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北方的天仍冻在冬天的季节里,站在月台上,他竟然没有直奔她而去,而是一一地在那座城市与自己曾留过的身影握别后,又匆匆地踏上了归程的列车。
北国的雪很洌,很厚。逐渐南下,天竟也硬朗许多,山显出来了,水凹出来了。
他心情颇佳读着诗集,却有了意外的欣喜。他像一个开悟后的诗人:眼前的春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溢光流彩的秋天也来临了。他看见了一个女孩很长很亮的秀发,很浅很丽的笑容,很柔很洁的素手。她正站在1995年秋季的城市广场上,广场上开满了南方的无名草花,花香洌人。暮色轻合,他有力地呼吸着这个城市的韵味。我想知道快乐的源头在哪里呢?他很有些惬意地喃喃。
这很不重要。
我知道,他笑着对女孩,但是我想知道这不重要的缘由。
女孩的回答或者是注重动作——
女孩的手拈着一朵淡黄的花放在掌心。捂着。又轻轻地把它贴在胸前,她的神态很痴迷,真的——
女孩的回答或者是既注重动作又钟情于语言——
女孩的神态很痴迷,她拈着一朵淡黄的花放在手里,声音柔柔地说,真的——我们可以把它轻轻地捂住,然后贴在心口……
他很欣赏自己此时介入的这种意境,他想让它重来千次、万次,让那种痴迷像春天的花带露儿挂在自己青春的腮边。
现在再来看他,他完全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因为他在临下车前,把女孩送的那本诗集又送给了一位精神曾像他一样颓废的女孩。他想,自己是不是会像一朵春天里带露珠的花铺开在小女孩走过的路旁呢!还想,花儿就这样开放着,那又是多么美妙的花香遍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