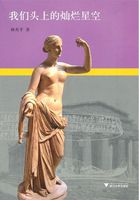花的艺术水平与精神魅力如此巨大,不是单独一个庙底沟遗址所能够辐射完成的。庙底沟遗址发现以后,又有大批的同类遗址被发掘出来,也使庙底沟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考古发现证明,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力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要超越与之同时、或早、或晚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空前绝后、一统天下,它的分布区北达内蒙古南部、西到甘肃陇东一带、南及汉水流域、东越河南中部,它的文化因素的传播则更远达数百、上千里之外。正因为庙底沟类型有着这样的影响力,所以现代人都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与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拉近,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还有人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华胥古国联系起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反映出今人迫切想要将这种英雄的历史归功于英雄人物创造的复杂思绪。
在中国古汉语里,“花”与“华(華)”是同一个字,本义都是指花。仔细品味庙底沟人的花卉大观园,虽然千姿百态,但也有自己最爱的两个种类,一种是卷曲的玫瑰形,另一种是盘状的菊科形式,以前者最为显著。玫瑰的花季是春季,预告春耕,菊科的花季在秋季,预告收获,庙底沟人选取与其生活最密切的花朵作为装饰,要表达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可以想象在庙底沟人的周围,房前屋后、聚落内外、从村边到河边、从平原到山冈,必定生长着漫山遍野的鲜花,庙底沟人在享受这种美好生活的同时,还不忘以花来命名身边的许多事物:盛开鲜花的群山称为“花山”,自己的部族称为“花族”,对自己的称呼也就成了“花人”,这些名称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最后就变成了今天的华山、华县、华阴、华族、华人等称谓。
华山可能是华族最初所居之地,它的得名源自其百花繁盛,因此考古学家指出: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必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里华族的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与分布情形非常相像。所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它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之名由来的依据,而“华山玫瑰”也成了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及庙底沟类型本身的最贴切指代。至于华族与华夏族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华族与夏族融合以后的合称并沿用下来的称谓,也有人说是华族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同阶段的名称等。可见“花”与“华”由史前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超乎人想象的复杂关系并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人类爱花是共性,但爱花爱到庙底沟人这样的程度,是绝无仅有的,称中国人为华人是再恰当不过了,有其历史的必然。庙底沟是首个被揭露出来的典型遗址,填补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诸多空白,找到了解开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关于华夏族由来诸多疑问的金钥匙,学术意义重大。它以崭新的文化面貌刷新了人们的视线,也透射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历秘密,吸引着今人不断探求关于远古人类生产生活情况的细节,从而丰富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
古代氏族——大汶口文化
巍巍山,五岳独尊,悠悠汶水,源远流长——这几句山水感怀比较贴切地道出了泰山与大汶河在自然和历史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这两者之所以被相提并论,缘于泰山南部、大汶河畔著名的大汶口遗址以及曾经遍布今天山东境内、辐射豫、皖、苏三省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距今6 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前身。作为一支势力强大的新石器文化代表,大汶口文化有自己的文化专利,它有一批特点鲜明的精美陶器、发达的手工业加工技术以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奇特习俗。
陶器是大汶口文化内涵的主要标志物,除常见的红、灰、黑陶外,还有白陶,非常与众不同。陶器上经常饰镂孔、划纹、鼻钮等,并有绚丽的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可能是为了适应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或者遵循某历史传统,这里的三足器、圈足器非常发达,多见各种形式的鼎和帮——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实足鬻、袋足鬻,在大汶口人的理想中似乎要把所有器物都装上腿(足),这种现象成为该文化的一种特色。此外,漏缸、豆、背壶、觚形杯、大口尊等也带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与鼎、鬻等共同构成了大汶口文化完整的陶器群体。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这时期显然出现了专业的工匠。从陶制的日常生活器皿到生产用的工具,直到显然非实用器的各种原始礼制用品,都从大汶口人灵巧的双手中创造出来,其技术的精湛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后世。大汶口人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开始使用轮制技术,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一时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被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继承并发展,制造出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令世人惊叹不已。大汶口文化还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器,反映出工艺技术的纯熟和制陶业的兴旺发达,如猪、狗和龟形的容器,其中的兽形提梁鬻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制作业也比较发达,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通常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石料,石器造型规整,器类丰富,在一些墓中常见随葬成套的大、中、小型石器,还出现了精致的玉质工具及大量的玉、石装饰品等。
大汶口人的制骨工艺十分出色。墓中经常出土精巧的小件骨雕品,如雕花骨珠、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器柄刻有纤细花纹的獐牙钩形器等,剔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比较成熟,其中的透雕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骨雕筒等,都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彩陶豆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有一些独特的习俗。原始人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习俗,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他们平时嘴里还喜欢含着小石球或小陶球,每天在嘴里滚来滚去,由于长期含着这些小物件,所以有人的臼齿外侧已经严重磨损甚至内缩,颌骨也跟着异常变形,不但模样奇特而且充满神秘感。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钩形器及龟甲等物品,在其他新石器文化中非常少见。
大汶口人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粟。在遗址内窖穴形式的粮仓中出土了成立方米的腐朽粟粒,表明这时粮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产量。大汶口人也有石器制作的工具,铲、斧、刀、锛、凿等器具数量众多,另外还有骨镰、蚌镰以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等。其中的有肩石铲、有段石锛、石镐头和鹿角锄等工具标志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也比较发达,遗址里出土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而且用猪下颌骨、猪头、半只猪甚至整猪随葬的风俗非常盛行,墓地中用猪随葬的墓占三分之一以上,随葬猪下颌骨最多的达30多个一方面说明这时猪的饲养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表明大汶口人对猪情有独钟,生前死后都离不开猪的陪伴。有很强的宗教意义。大汶口人也捕食大量的獐、斑鹿、狸和麋鹿等野味,还有扬子鳄、鱼、龟、鳖、蚌等大量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发展得比较成熟,除了简陋的小型单间建筑外,也能建造规模宏大的连排多间建筑。在大型聚落里,外有围壕环绕,宽二三十米,深五六米。聚落内部广场、房址、兽坑、祭祀坑等密布。房址均围绕遗址中心而建,以2间、4间或5间为一排分列。房址为浅地穴式,由主墙、隔墙、门、居住面、室内平台和室内柱构成,一般面积为10平方米,大者近30平方米。墙体为木骨泥墙,与地面同时经烧烤,墙面光滑,有的抹有一层白灰面。门向朝南,设有单门或双门。
大汶口文化墓葬多为土坑墓,少数墓圹不清。墓地往往沿用很久,有的地区墓葬层层叠压近十层,年代至少在千年上下。墓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简陋狭小,随葬品很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百余件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鱼皮鼓”残留下来的成堆鳄鱼鳞板。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还发现有折头葬,死者系骨盆内有胎儿骨殖的女性,像是因难产而死的孕妇。还有把死者双臂双腿盘折于胸前的葬式,可能是对凶死者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些大墓无墓主、墓主身首分离或尸体无头部却随葬品相当丰富,可能是对在部落战争中为本氏族利益牺牲的首领或成员的一种厚葬。合葬墓分一次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墓两种形式,多为同性合葬,最多的合葬人数多达20多人。
大汶口文化早期贫富分化不十分明显,有多人合葬墓,氏族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纽带比较牢固,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到了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私有制也逐渐形成,父权制已确立,完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它的发现及其与山东龙山文化传承关系的确定,证明当时山东、苏北一带。是一个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自成系统的文化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中心起源中的一元。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而得名,距今7000——5 300年。河姆渡村位于风景如画的宁绍平原,杭州湾南侧,四明山北麓,流经平原的姚江把村庄一分为二,主要的考古发现也集中在江畔一带。
河姆渡遗址的重要发现非常丰富,有房屋、水井、农具、稻种和大量原始艺术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主要为防潮湿而建,是江南地区的特色建筑形式之一。它的屋顶是长脊短檐式的,以适应多雨地区的需要,建筑底部不是房基,而是许多成排埋在地里的竖立木桩,木桩顶部用横梁连接,构成高出地面的木质底架,在底架上铺设木板形成平面,再于木板上构屋建房。河姆渡文化中干栏式建筑已非常盛行,技术也相当成熟,所以留下遗物甚多。遗址中发现了与建筑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若干件,其中不少构件的端部带有榫头与卯孔等结构,有的还相当复杂,如双层榫头、燕尾榫、企口板等,表现了建筑材料之间接合方式的新奇创意。最完整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有200多根,整齐的排列成互相平行的4行,长约23米,宽约7米,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建筑的室内可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且带有廊道等设施,显然不是一般的房屋,不是公共住宅,就是氏族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这样的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内还有好多处,形式、大小各不相同,往往是集中在一起连成片状,有明显的布局,呈现聚居的状态。在建筑遗迹范围内,还出土有芦席残片、陶片以及人们食用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证明人们在这些建筑里居住生活的时间相当长久。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早的木质结构水井,井口呈方形,边长约2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井口外围有28根栅栏桩。排列成一个直径约6米的圆圈。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芦席残片等,这些是与井上建筑有关的材料。由此可见井上还应当有井亭建筑。
骨耜河姆渡居民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作遗存。主要栽培晚稻型籼稻。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1米多厚的堆积层,据资料统计总量达到150吨之多。由于长期埋藏于土壤之内,与空气隔绝,遗物出土时色泽光润、外形完整、有的稻壳上陛脉、稃毛仍然非常清晰。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在一件陶盆上还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使人能够想象出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对于水稻有多么深的情结。连制作陶器时也没有忘了将它们的形象刻画上去。为了更好的耕作,河姆渡人发明了很多农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骨耜,仅在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了上百件。它们采用鹿、水牛等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向的孔,或者是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两侧各凿一孔。柄用分杈的树枝和鹿角加工而成,呈曲尺形,杈头部分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下端嵌入槽内,横孔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这些农具的发现表明,河姆渡人的耜耕农业是非常先进的耕作形态。
除农业生活以外,河姆渡人还兼营采集、畜牧和渔猎。遗址中出土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都是人们从自然界中采集回来食用的。这时期已有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有较多的水牛骨头。野生动物骨骼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鹿科动物,仅鹿角就发现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等温热带动物遗骸。发现数量较多的骨哨,可能是狩猎时用以诱捕动物。大量骨镞和鱼骨表明渔猎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也很重要。
河姆渡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夹碳黑陶,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陶器的胎泥纯净。但以大量的稻壳及稻茎、叶碎末为掺和料。工艺技术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画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器形多为平底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支脚、宽沿浅盘、垂囊式盉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人的主要炊器。
原始艺术中也有不少精品,象牙制品中有刻画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与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木器中有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一层朱红色生漆涂料,虽历经几千载,仍微显光泽,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此外,还有憨态可掬的陶猪雕塑、刻画于陶钵上的猪纹和稻穗纹等图像,表现了河姆渡人乐观的心态。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突破。大量干栏式建筑和人工栽培稻谷及农具的发现不但显示了河姆渡人稳固的定居生活与先进的农耕技术,而且以最具说服力的实物标本表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繁荣,它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家窑文化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甘肃又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新石器时代的甘肃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尤其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这项艺术的巅峰。是中国彩陶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