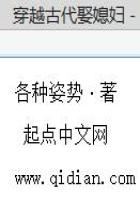序言:群山易崩,天命难违,水何澹澹,尽书风流。当今天下,分为五地,以方向为名,故命为“东境”、“南境”、“西境”、“北境”和“中境”,五境各划边界,不交兵险,不通友谊,各自为国。
第一章
风抚大地,万物尽尝太阳气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珍珠之邦”——南境独有的芬芳。莺歌燕舞,群臣共赏箜篌,偌大御花园内,是南境皇帝的设宴。身着轻纱,下穿裙,柳叶弯眉,樱桃嘴,这是南境美女特有的翩翩起舞,伴随着中午和煦的阳光,真让人想发出“此生足矣”的感叹。
“好,好。”一曲作罢,皇帝鼓掌,随后众臣亦跟着鼓掌。皇帝饮完一杯酒,看了看旁边眉清目秀的少年,笑对其言:“天珉,朕之图治方得这天下归心,此情此景,尔不如,作诗以赋。”
此言一出,众臣都望向少年,少年故意表现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情,引得皇帝哈哈大笑,举起酒杯欲饮。
“大风吹漠雄姿挺,春风鸣雀懒洋洋。壮士扔耕捡戈去,金碧墙里燕舞齐。”趁着大家不注意,少年倒酒,面无表情,又似有不屑地吟了一首诗,众人顿时雅雀无声,连皇帝也差点被呛着,待他反应过来,顿生闷气,“哼!”随即挥袖而去,宴会不欢而散。
“是他欺人在先,明摆着想让我出丑,我已让他三分,他却不依不饶,岂不是找辱?说什么天下乃其治理所得?算了吧!”这位忿忿不平的少年,正是南境的九岁神童【艾臻字天珉,南境秦王】当今皇帝的二弟。
“可是殿下,毕竟陛下早就对殿下放心不下,此一来,恐又徒添君疑。”【何思贤,艾臻师傅】劝道。
“他不来惹我,我自不会去惹他。”艾臻说道。
南境皇帝艾闻,在位三年,碌碌无为,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气量狭小,又非一母同胞处处排挤艾臻,故为艾臻所厌恶。
次月,适逢艾臻胞弟【艾瞻字天弘,南境齐王】寿辰。艾闻举杯致辞,众人饮酒,面带喜色。宴近毕,【李贞南境太师、当朝国丈】举杯走到艾瞻面前,笑言:“臣祝殿下寿比南山”,言语至此,李贞举杯而饮,年仅七岁的艾瞻也站起身来,以茶代酒,微笑谢之。
“殿下与秦王乃陛下手足,衣食无忧,理应效忠于陛下,维护于陛下,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年近七旬的李贞,用他那年老的肥音,故意拖长的字眼,伴随着他平淡的语调,反而激起了千层浪。
艾瞻有些不满咬了咬牙,李贞看着艾瞻的样子,得意地回过身去,嘴角一弯,给艾瞻送去了羞辱,一旁的艾闻也是轻哼了一声,似乎等待已久的出了口恶气。
艾瞻身旁的艾臻随意坐着,将手放在躬着腿的膝盖上,见此状,微微一哼笑:“尔等食皇禄、辱皇嗣之人,我等若身在福中不知福,则尔等岂非死在福中不知道么?”李贞猛一回首,艾臻有些歪着头,嘴角上扬,似在挑衅地看着他,艾闻亦不禁握拳气愤。
气氛僵滞,众人久久不语,何思贤见情况不妙,恐生变故,于是站起来敬酒解围:“今日乃齐王殿下寿辰,酒醉之极,玩笑耳,众位均乃气量大儒,怎会因此事而牵肠挂肚,来来来,共举杯,并同乐!”
“来来来!”其余众人赶紧附和,这才缓解了尴尬。
事后,“哼!艾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毛孩子,太过无礼!”艾闻很生气。
“陛下,秦王年少即成名于天下,先帝若不是因为其年幼,恐早已立其为太子,陛下应该小心为是。”
艾闻切齿:“依太师之见,朕当如何?”
李贞捋了捋胡须,继续说:“依臣之见,可去掉其心腹何思贤之官职,加封以伯爵,架之以虚衔。”
“如此,甚妙。”艾闻点了点头。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臣领旨谢恩。”
待御史走后,何思贤看着手中的圣旨叹了口气,艾臻靠近,一双杏眼看了看圣旨,又看了看何思贤:“明升暗降,想必我已成他眼中钉了。”
何思贤皱眉,忽然跪下,苦苦劝道:“殿下,先帝有恩于微臣,老臣不忍心就这样看着殿下白白送死,老臣请殿下不要再露风头了,能忍就忍吧!”
何思贤满头的白发令艾臻有些回避他如炬的目光,艾臻抿了抿嘴,点了点头,勉强回答道:“恩。”
之后的三年里,朝廷也没有大事发生,平日的宴席,艾臻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依照他的性格,又怎会自甘平庸下去?
三年后,艾闻的一个儿子得了重病,每况愈下,此时又适逢一位秀才写谋反之诗触怒了艾闻,众臣求情,让皇帝为其子积德,不要杀这个秀才,艾闻想杀却又爱儿子,于是问李贞,李贞献策:“臣斗胆,若皇子去世,届时陛下再起杀心,天下定认为陛下乃以情用事、公报私仇之人。”艾闻恍然大悟,点了点头。次日,秀才被杀。
消息传到艾臻耳朵里,吃饭的时候,艾瞻议论此事:“你说皇上真不怕上天怪罪?”
艾臻正欲饮水,闻言,微微抬头,看了一眼艾瞻,一笑,饮之,轻轻放下爵,微笑回曰:“若陛下等皇子仙逝,再杀这人,群臣百姓定会认为陛下这是找人泄气。所以,先杀后杀,衡量一下,自有分辨。”
“哦~”艾瞻顿悟,“皇上真周全。”
“呵,”艾臻不以为然,“当今圣上若真有如此之脑子,还会纠结于是否杀一秀才乎?”
艾瞻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艾臻亦笑之。此时,站于窗帘后的一位小太监乘着别人不注意,偷偷离开了……
“什么!他竟然敢如此说朕!”艾闻暴怒,一拳头砸向桌子。
“是的陛下,小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正是那位小太监将这一切告诉了艾闻。
“岂有此理!”艾闻气不过,又对小太监言:“你做的很好,下去领赏吧!以后,也给朕盯着他!”
“是。”小太监得意洋洋地下去了。
当晚,艾闻找李贞商议,于是下圣旨警告艾臻,罢免其秦王之爵位,降为“秦侯”。
次日,艾臻接旨后闷闷不乐,也很生气,饮酒数杯,众人劝阻,不成。
酒醉之后,艾臻噘着嘴,眼睛紧闭,叫嚣道:“吾若为皇,何阻!”此言一出,何思贤赶紧堵住其嘴:“不要命啦!”
不巧,这句话传到了艾闻耳朵里,适逢皇子去世,艾闻忍无可忍,起了杀心。
“不可,不可啊陛下。”李贞劝道。
“有何不可!那艾臻狂妄之极,先是妄猜圣意,再是口出大逆不道之言,十个艾臻,都够朕杀的了!”艾闻气不过。
“话虽如此,但陛下不要忘了,秦侯年方十二,一黄口小儿,若杀之,则群臣百姓作何感想,若不杀,则可体现陛下宽容大度,体恤手足之情。”李贞劝言。
“可,可不杀他,岂不是便宜了他,这艾臻平日里的所做作为太师也知道啊!”
“不杀,并不代表不降罪,陛下大可以下旨,说其大逆不道,而陛下念骨肉之情,将其驱逐出去,至于驱逐出哪里,当然是越远越好!”李贞奸笑,双手合袖,握拳弯腰,迎合艾闻。
“哦~”艾闻露出笑容,似乎十分满意,“就依你所言。”
二日一大早,皇宫侍卫气势汹汹地闯进了艾臻府邸,艾臻闻声,从床上爬起,眼见侍卫已经闯了进来,领头的高块头侍卫趾高气扬,眼睛也不看着艾臻,提着圣旨,叫道:“请秦侯接旨!”
艾臻伸了个懒腰,有些不耐烦,慢慢吞吞从床上下来,跪下,舔了舔嘴,懒散言:“臣艾臻接旨。”
侍卫轻轻哼了一声,左手将圣旨拉开,用他雄浑的嗓音念道:“奉天成运,皇帝诏曰。秦侯艾臻,目无王法,先是对朕不敬,公然在朕身后议论纷纷,再是出言不逊,苟怀篡逆之心,证据确凿,罪不容诛,理当问斩,”念至此,艾臻突然清醒,脸色突变,抬头看着侍卫,“但朕念尔为先帝之子,朕之亲弟,不可不顾及,所特赦尔一死,驱逐出南境,永不录用;齐王艾瞻,与其兄似,助纣为虐,亦不可留,并一同放逐;其余府邸师爷、家奴等,一概流放,钦此!”
圣旨读完,艾臻有些呆滞,两眼巴巴地望着侍卫,一颗豆大的汗珠从一鬓滚下。“接旨吧!”侍卫将圣旨快速地推到艾臻面前,艾臻抿了抿嘴,双手举过头,接过圣旨,侍卫又言:“皇上还说了,请艾臻速度离去,先帝的灵位前不需要逆子再来拜别。”侍卫说话很冲,这让艾臻有种狗仗人势的感觉,“呵,”艾臻的头低下去,不禁自嘲,“虎落平阳被犬欺。”
一上午,秦侯府哀声一片,墙倒众人推,府中上下,都是仆人匆匆收拾细软、草草准备逃跑的身影,唯艾臻坐在正厅,翘着腿,呆呆地看着这荒唐的一幕。
艾瞻、何思贤闻讯赶来,艾瞻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不停地流泪:“为什么,为什么我连父皇母后的灵位都不能去拜一拜!”也是,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罢了。
艾臻的眼眶也已经红了,他抬头望了望窗外来把泪水强忍回去。何思贤走近,跪下言:“殿下,如今大势已去,幸得保全性命,老臣愿意倾己所有,陪殿下去中境,继续侍奉殿下。”艾臻久久不回应,也许是没有想到自己的才气竟会惹出这样的祸端,也许是没想到自己的亲哥哥竟然会这样的小肚鸡肠,亦或者是满心的愤怒,更多的是无尽的悲伤……
“殿下,圣旨不可能再收回,事已至此,请殿下速速动身吧!”何思贤劝道。
“既然他和我动真格,那好,那就玩真的。”艾臻站了起来,红红的双眼多了几分坚定,艾瞻不解其意,艾臻又对何思贤说:“带好要带的东西,去中境!”“是。”
没有人知道艾臻在想什么,收拾行李的时候,他的目光时而呆滞时而坚定,仿佛在下一盘棋,一盘以自己性命为赌注的棋,但也许,他只是想去中境从头开始而已。
由于艾闻的不断催促,当天傍晚,艾臻、艾瞻、何思贤等一行寥寥几人,乘着与其身份并不相符的船只,向中境开去。
夕阳西下,暮光洒满了江面,顿成金黄一片,何思贤回首,望着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不禁老泪纵横:“哎,天意不可测,犹如这余晖,让人分不清是傍晚还是黎明啊。”
艾瞻一直在哭泣,艾臻强拧微笑地摸了下他的头,再回首,不愿意再回首,眉头紧锁,充斥着少年的忧愁,此时此刻,十二岁的少年正经历着二十岁、四十岁甚至六十岁所不能体会到的痛楚。梦想的破灭,对于艾臻这样的才气,就这样灰飞烟灭,直叫人扼腕叹息。波翻浪涌,海鸥留声,何思贤的悲哀,几乎到达了顶点,本来希望能辅佐艾臻能够对南境有所贡献的他,现在只有可惜了,他看着艾臻幼小的背影吟道:“血泪集千秋,白鸟空悲鸣,生死不能,理想不能,肝肠寸寸断。”掩面哭泣,顿回舱内。江风将这孤舟推送,送往遥远的他乡……
“放眼旧土去,三里一断肠。白衣渡南洋,不再回故乡。”艾臻吟诵着,回过身去,不再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