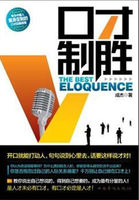因子进亭子的脚步是很轻的,因此她没有惊醒那些疲倦了的雪,甚至连在树叉里的找食的鸟都并没有因她的到来而迅速飞走。她悄悄的坐在亭中的石桌旁,将包摆在自己的腿上,然后有点虔诚的从包里面取出了那封外表很平实的信。“他会在里面说些什么呢?就象那服务员说的那样向我提婚?这可能吗?”因子好奇而又激动的反复的盘问着自己。
信终究是打开了,一张很平常的办公用纸,上面写上了半个版面的字,内容是这样的:
因子小姐:
首先请原谅我在不经得你同意就擅自做主把你带回了我的房间,但你放心,我没有伤害你,我也不会伤害你的,这一点我想请你相信我。另外,我请你原谅我在你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不辞而别,但这其中原委我也不便在此向你诉清,如果你乐意知道的话,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如果跟我交往久了也自然会清楚的。我想让你了解的是,我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打滚的人,作生意就是我生命的激情所在,这一点你能理解吗?我希望你会的。因子,我以后就叫你因子好吗?你也可以直接叫我莫科。你快要毕业了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在你毕业后就结婚,你考虑一下,以后见面再答复我。另外,我的手机号码还有家里的电话号码都付在这张信纸的背面,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在这个省我想我还是有一定的处事能力的。好了,因子,我爱你!你也许不信,认为这只是所有男人欺骗女人一贯的伎俩,但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信不信,你是我这十几年来唯一看上的女人,也是我决定不再放走的女人。也许你并不清楚我心里在见到你那一刻起就多么深切的刻下了你的影象!因子,请不要说你还不了解我这样的话,我相信即使现在你不了解我,但在不久的未来你就会的,真的,我相信你会的,我有这信心,也请你相信我有这能力。
莫科
1月1日
因子将这封简短的信连续看了五六遍,直到她觉得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已经熟记于心了才将这张单薄却充满温欣的纸折进了包里。她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迷人的,在这个元旦晚会之前她还是个灰姑娘,每天早晨起来后草草的在脸上涂了点油,用梳子随意的将头发里顺,另外就不再去管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了,直到昨天,马云怕自己的手下在台上给自己脸上摸黑,怕别人说他手下没人,因而在中午开最后一次会时特别将形象问题做了个强调,作为晚会主持人,因子自然的成了他重点要修整的对象。
因此,当因子在化装间里精细的描绘了一番自己后,一向不想正眼瞧她的马云却呆呆的站在她身旁近十分钟,若不是外面有事要应付,还指不定他会在那里呆多久,看多久呢!
人靠衣妆!这一点也没错。因子觉得自己以前只知道死读书,然后就是努力的工作,从来就不大乐意多在打扮上花费一分钟时间这是个多么愚蠢而傻气的做法。她若不是在昨天被逼着去修饰自己,她又怎么能令台下所有的观众倾目惊呼,她又怎么能让莫科这样的社会名流在意自己并把住不放呢?她在内心里暗暗的庆幸着,庆幸着自己确实是在关键的时刻以美天鹅的形象出现,庆幸着自己确实得到了这些连自己想都不曾敢想回报,她甚至有时会想到莫科信里提到的那个事情——在她毕业后马上结婚,如果这样的话,她就不要象所有的师哥师姐们一样的南下广东四处奔命了,因为据有些回校考研的师姐们说,她们虽然是重点学校的本科生,但由于学校深处内地,沿海地带对它不很了解,因此好的工作并不容易找,她们也由于不满现实的工作条件,不得不回校继续考研。对于因子她们这些学校的专科生来说,想在本地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都很难,更不要说去那些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了。在昨天晚会之前,因子在打电话回家给爸妈报平安时她爸爸还关心的问她,“因子,大二快结束了!大三一开始就得找工作了。你想好了要到哪里去了吗?”因子最怕听的就是别人这样的问她,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应该到哪里去,她能到哪里去?她能干什么?在平时若同学问起她时,她一定会不耐烦的扔下一句“以后再说吧!着什么急呢!”而现在是她爸爸问她,她是极端的敬重这个老人的,因为这个老人之所以这么快的衰老都是因为他要供因子读书,因子也是知道这些的,每当她想起自己的爸爸心就如刀割一样,她有时也觉得没有什么脸面去见她的爸爸,她怕看到他那慈祥而又充满了期盼的脸盘,她怕他会问她“因子,你打算以后找什么工作呀?”这样的话,因此,在每次放假要回去时,因子总是会在寝室里安静的卧上一晚,想象该怎样去设计自己的理想,让它即不太夸张得难以实现,又能让自己的爸爸欢欣。“爸爸,你不要操心。相信你的女儿,她有这个能力找到好工作的。再说了,你是知道我在写作方面有特长的,大不了以后我呆在家里写作,这样也能养活一家人!”因子的爸爸高兴的说:“爸爸知道你行的,但写作也不是个长期谋生的办法,你最好还是找份稳定的工作吧!好了,你要准备晚上的事了,爸爸不打扰你了。”说着就挂了电话,不等因子跟他说上一句再见。
现在因子感觉是很幸福的。虽然她跟莫科还只是见了一面,虽然他还只是给了她一个纸上的承诺,但她却对他有着百分百的信心,她也决定若是莫科当面向她提出结婚,她一定会很乐意的接受,并也象他告诉她的一样对他发誓“我一定会永远的爱你!我也不会放走你的。”是的,因子是绝对不会放走这个送上门来的男人的,她是懂得机会是不容许有人轻易将它错过这个道理的,错过了一次,想要有第二次,然而这个第二次也许以后一生都不再能遇得到的。因子到现在还不曾喜欢过一个人,更不用说去爱上一个人,她总是觉得跟她相处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平凡无奇,都是那么不值得自己去托付一生,因此她在大多的朋友和所有的有点容貌的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所谓的幸福后,依然是孤零零的,但她自己并不觉得这很凄凉,相反,她觉得这是一种资本的沉积,因为只有在所有那些肤浅的、眼光短浅的女孩都有了自己的男朋友后,象她这样容貌的女孩才会成为抢手货,到那时,她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还不是顺她随心所欲的事。
因子并不确定以后是否会爱莫科的,但这并不重要,她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长久的爱,或是有什么坚贞不渝的情,她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那些暂时相爱的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在某种激素过度分泌的时候而不理智的说出了“这个世界上有永恒的爱情,有永恒的幸福,有家庭一生的快乐和美满。”这样偏激的话语。她只相信着人生本不是什么都能拥有的,得到了这些势必就将失去那些,人活在世上不要太贪得无厌,要学会见好就收,懂得到了何时就该满足。她对爱情的概念远比不上对整体生活的渴望,爱情对于她来说最多是有助于她能更快更顺利的达到自己生活中追求的目的,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渴求。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去,寻食的鸟儿也已经归巢,但因子还不舍得离去,不舍得在自己第一次接到进入社会的特别通行证时天还没有全黑就离去,她要让自己记住这一天,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她的生活可能会全面改观了,她可能从一个连自行车也舍不得买的普通女孩瞬间变成一个受人仰慕,让人侧目而视的高贵女孩。想到这里,她的心里微微的颤抖了起来,就象是她刚刚偷了别人什么东西一样。
但夜里冷冽的寒风并不卖因子的面子,它们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穿过亭里那些幽黄的光辉俯冲到因子的身上,直弄得她连续打了几个不算文雅的喷嚏,鼻子水都出来了,她只好匆忙的用纸将这些可恶的家伙擦干净,急速的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因子第一次觉得它们是那么的无聊,她整天都在等待着莫科的电话,但莫科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一直都没有来电话。她感到很痛苦,一种炼狱般的痛苦,但她并不愿意跟自己的朋友们说,她只是每天茶饭不香的等着,盼着莫科的出现。
马云几天都在注意着因子,这让她感到很厌恶,她有时甚至想狠狠的瞪他几眼,然后跟他大吵一架以解除自己心里几天下来积蓄的郁闷。但她终究没有敢这么做,她还不想在这个时候破坏她在马云心里那乖女孩的形象,她也不想在莫科没有正式向她表白说要娶她,保护她一生的这个时候去逼急了马云,让他随便的以一个理由把她给辞掉,甚至于将她打下十八层地狱。
因子在马云面前依旧是那么的谦虚,近似于有点低声下气,马云却似乎不再愿意看到她继续这么客气下去,他当着林子的面说:“因子,你以后就不要叫我马老师了,那多不亲切呀!你也学学林子,他不是叫我老马吗?你干脆也叫我老马或是马云算了。”因子不肯就他的范,怕自己若真这样做了马云会误会她真的喜欢他,到那时就真麻烦了,于是她聪明的回绝了。
天气在一阵较长时间的阴冷后终于放晴了,天空的云很是洁白,它的底色也蔚蓝得出奇,这样的景色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是很难看到的。因子播完六点钟的广播,匆匆忙忙的想赶回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配对,下了楼,令她惊讶的是,先走的马云在楼梯口等她,“因子,这么急,有什么事吗?”
“没有!”因子有点不大高兴。
“那就好!”马云高兴的对自己说。
“那就好?马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因子警惕的问。
“没、没有!”马云顿了顿,接着喏喏的说:“我只是想等你一起走而已!”
“那就不必了,马老师,您是个大忙人,您哪有时间来等我呀!再说了,我也没有自行车,让您推着车陪我走我实在过意不去。所以马老师,您还是不要等我了,我还得到那边店里去买点东西呢!”因子有点不大客气的想拒绝跟他同行,并试图往路旁的一个蛋糕店走。
“我有时间的!因子,我难道跟你走走都不行吗?你不是每天都能跟林子一块走吗?难道我比不上林子?”马云有点失控,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他的威严在顷刻就全数化为了污水,他立即想去挽回,于是补充说:“因子,不好意思!我失态了。刚才那样的话我是不该说的,你能原谅我吗?”
因子仍被他的那些话语震惊着,她猜想,马云一定是误会她和林子了,她和林子在一起上课,因此每天放学后自然是一起来到广播室的,这些马云都看在了眼里,日子长了他就产生怀疑并醋意突发了。因子并不想对他解释这些,她清楚,若她向他解释跟林子没有什么,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向他发出一个信息:她和他要有什么。再者,现在马云以为林子是自己喜欢的人,一定也不敢更进一步对自己怎样的。想到这些,她就故做没有什么事似的微笑着说:“没有什么,马老师。我谢谢你这么看重我,真的。但我现在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我很喜欢他,我想他一定也是喜欢我的。马老师,你的条件这么好,要找一个比我强的那是很容易的,你就不要太关心于我了。”
马云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来。为了不再这么尴尬的呆下去,他垂着头,推着那辆显得有的过时的自行车慢慢的走了。
因子目送着这个单瘦的身影消失在喧嚷的人群里,心情很是复杂。
元月十六日,这一天对因子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
当因子上完课,走到教学楼外面时,一大群人围在了楼前的岔路口,不知道在干什么。因子在广播站工作,是个校记者,因而对这样的事情有种职业的敏感性,于是她也就撮了过去。但由于看热闹的人太多,她挤不进去,就只好在边缘徘徊。
“因子,我爱你!啊!好浪漫呦!”一个女生夸张的叫着。
因子并没有听清楚,她只是隐约听到了有人在叫她,就答应着,“我在这里。“就这么一句,拦在前面的人象受了刺激一样迅速的往两边散开,因子并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因此也跟随着大家往外退。因子有些在里面了解了情况的同学忙跑了出来拉住了她,“因子,你看,用玫瑰摆成的心!好漂亮呦!我们真羡慕死你了!”
因子不敢相信的重复着那句话,“玫瑰摆成的心?为我?这,这是怎么回事?这可能吗?“但她很快就确定了这些都是真的,在散开的人群围成的圈里,地上铺着一张五六平方米的红地毯,有人刻意的在上面用红玫瑰围了颗大大的心,在心的中央站着一个穿着崭新西装的青年男人,他的手里也握着一束火艳的玫瑰,一张写着大大的“因子,我爱你!“的牌子悬在他的另一只手里。看到因子出现,他忙将轻快的笑容挂到了脸上,慢慢的走了出来,想将手上的花和示爱牌献给因子。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因子很久才反映过来,令她不能相信的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而是一向沉稳古板的马云,她的领导,同学们的团支书。她不知所措的站在那里,身边的同学挤推着她,她却象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马云走到她身边,大声的向所有人宣布“因子,我爱你!“围观的人们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加以鼓励。
因子冲了出去,她相当的愤怒,她不能容忍马云以这种方式来向她示爱,以她看来,马云的行为是在逼迫她,她因子不是那种怕逼的人,她从来就没有因为谁逼她而乖乖的就范,她也从来就不会因为这样而宽容别人的冒失,进而去理解别人,去服从于别人的所为,相反,她会因此而更加努力的去讨厌这个人,甚至鄙视,打心眼里鄙视这个人,而这个人要在她的心上再有任何的分量,那是再也不可能的事了。
在谁都不能预料的情况下,马云脸上无端多了五支血红的手指印,这些手指印很是纤细,纤细得特别的刺眼,不论看没有看到这个场景的人都会立刻的意识到,这个男人被女人抛了,而且抛得极不光彩,他的脸上一定被女人吐满了唾沫,他的头发一定是被女人搓上了一把灰,他的灵魂也一定是被女人擦上了灰。
总而言之,他已经是个倒过一次霉的人了,是一个世界上,最少可以说是爱情世界所遗弃的垃圾了。马云并没有立即反映过来,他的笑容还是那么轻巧的印在脸上,嘴角的话语还在试图着疯狂的往外面的世界跳。但他确实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了,他什么也不能说出口了,也没有人再去听他的了,因为假如他在此时再去对大众说出些什么,不管这些是好的、是坏的、是不好不坏的,总之这些都是无用的,都是虚伪的招人怀疑的,让人觉得他是在为自己圆场,在为自己进行无奈的辩解,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也不过是好让自己退场,或是求得观众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