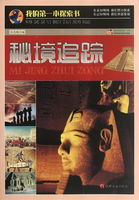木箱的重量十分沉重,入手的感觉和分量,绝对是材质上好的实木。我费力地掀开箱盖,顿时灰尘飞扬,只见箱内装的都是一些泛黄陈旧的古书,绝大多数都是旧书市场见过的那种线装书,一本一本码放得整整齐齐。
我家并非什么书香门第,全家上下算上户口本,大概也找不出来十本书,而这时突然发现,家中埋藏多年的秘密,居然是这一箱子比厕纸强不了多少的破书,不禁有些大失所望。我又打开其他几口箱子,无一例外的都是装满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一个装了许多褐色的、封面印着日文的笔记本,我无意间翻开一看,原来这些都是我太爷爷留下的日记本。
虽然我家里几代人,肚子里都不曾有几滴墨水,但是听我爷爷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家中族人无论男女老幼,那皆是饱读诗书之人,尤其是我太爷爷,据说他曾经远赴日本求学,是当时有名的外科大夫。日军侵华期间,他曾在南京的保护区内建立临时医务室,救治过许多被日军摧残蹂躏的无辜百姓,是名副其实的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拿出几本随便翻着看了看,我太爷爷名叫胡广凌,日记中记述的都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经历,以及回国后的一些生活琐事,但是书中的内容却令人难以自拔,其中的一段经历更是离奇古怪、跌宕起伏,简直比小说还要精彩。
因为原文都是一些文绉绉的言辞,而且是日记体,读起来未免过于繁琐,所以我在下面会对文章略作简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给大家。
事情发生在1925年的秋天,当时,三十岁的胡广凌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日租界”开办了一家西医诊所。那时候上海的正式称谓还叫“上海国际公共租界”,主要控制权都在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手里,而所谓的“日租界”,不过是老百姓对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的习惯称呼。
那年头,日本人在上海滩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甭管你是做什么生意的,都要和日本人搞所谓的“合作”,哪怕是一个道场的小小武夫,也要“无本三分利”,你若得罪了他们,就连那巡捕房中的公差衙役都不会放过你,更别提那些打着商人幌子的日本军官了。不过,胡广凌当时完全不需要考虑日本人的威胁,因为他与当时负责“日租界”安全防务的平谷一郎,是日本留学时的同窗校友,所以没有几个日本人敢去找他的麻烦。
可是你不闯祸,却也架不住“飞来横祸”,这件事情,险些让胡广凌葬送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
话说一天傍晚,胡广凌最后一次查完房,正准备从诊所离开,他的住所离此地还有一段距离,便想搭乘一辆黄包车,可是他四下张望,只见街道上显得秋风萧瑟,异常凄凉,连一个黄包车夫的影子也未瞧见。听说白天,一位日本领事在“日租界”遇刺身亡,巡捕房的爪牙们立刻实施了宵禁,贫家百姓害怕惹祸上身,纷纷闭门不出,哪里还敢随处乱走。
无奈之下,胡广凌只得一人徒步走回家中,借着那冷月辉星的微弱光芒,步伐急促得好似脚底生风,走着走着,他忽然发觉自己身边有些异样的声音。
这胡广凌本就是心思细密之人,再加上生逢乱世,平常出门行走,更加是小心谨慎。这时,他隐隐约约听见,在这条空无一人的街边小路上,竟然出现了一阵凌乱细碎的脚步声,他猜测这必是身后有人在跟踪自己,此时万万不可回头望去,不然跟踪者狗急跳墙,自己就更加难以脱身。
他下意识地低头,只见地上影影绰绰、树影婆娑,看不清身后是否有人尾随跟踪。胡广凌走到前方路口处停住脚步,发现附近左右无人,便一个闪身,迅速躲进旁边一个幽深的小巷。
他微微侧目向外张望,忽见一只浑身黑色、身形轻盈的瘦猫,直愣愣地站在了路口,绿莹莹的猫眼四下打量,接着又向别处窜去。
胡广凌吁了一口气,原来是一只黑色的野猫跟着自己,难怪看不见它的身影,他一边想一边走出小巷。就在这时,突然一只手从身后捂住胡广凌的嘴巴,将他又拽进巷子里,同时在他耳边轻声道:“别动,我是中国人,不会害你。”
这时候,巷子外面有四个巡捕房的巡捕,正好巡逻路过此地,胡广凌本可以向他们大声呼救,但他听见此人与自己一样是中国人时,便没有这么做,那几个巡捕拎着酒瓶子,很快就离开了。
胡广凌从对方手中挣脱,回头一看,眼前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高高瘦瘦,面色惨白,一身灰白的粗布衣服,右肩处一片殷红色,明显是受了重伤。那女子的身材也比一般女人要高挑得多,一身男儿装的打扮,一边搀扶着那个受伤的男人,一边急切地说道:“我们刚才也是迫不得已,请胡大夫不要见怪。”
胡广凌看那女子说起话来细声细语,也不似恶人,便问她:“你们是什么人?这位先生看来怕是受伤了吧?”
女子答道:“他受的是枪伤,还望胡大夫救他一命!”
胡广凌小心翼翼地把两个人带回自己的诊所,替受伤的男子取出了弹头,缝合了伤口,又打了针,这才问道他们是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却不料此二人口风甚紧,无论怎样盘问,愣是不说自己的身份底细,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夫妻二人在上海滩惹了仇家,希望胡大夫看在同为中国人的份上,连夜把他们送出城去。
当年的上海,除了外国人横行霸道以外,还有各路帮派林立,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利益纠葛,局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要胡广凌突然之间,把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连夜送出城去,他是断然不会答应,谁知道他们是得罪了哪位帮派头目。
那男子万般无奈,只好道出实情。这对男女本是夫妻,男的姓黄,祖祖辈辈居住在北平,是个名门富户,只因家道中落,不得已才来上海投奔亲戚,可惜世态炎凉,那一家人全然不顾同族情分,硬是将他们二人扫地出门。
夫妻俩来到上海多日,身上的盘缠早已用尽,眼看就要露宿街头,只好将家中祖传的一幅名画拿来变卖,换几个吃饭的小钱,可有道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这世道荒乱,还有几人有闲情逸致去花钱买张破字画呢?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二人走投无路之际,有一个识货的英国商人出了高价,要他们跟他去取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夫妻俩心智淳朴,便也没多想就跟人家走了,岂知那英国商人把他们骗到了“英租界”,进了英国领事汤普森的公馆,拿了他们的字画,又不给他们钱,还将他们二人强留在公馆,当了打杂的下人。
这黄姓男子也是个血气方刚之人,气不过对方仗势欺人,硬是趁着月色朦胧的夜晚,溜进公馆的储物间,取走了自家的字画,趁乱带着妻子逃了出来。不料刚刚跑出大门,身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洋人卫兵,就在自己背后打了黑枪,下了杀手,饶是他二人命不该绝,一排子弹过去,竟然没有一枪打中要害。
他们夫妻二人听闻,在“日租界”有个连日本人都不敢招惹的中国医生,所以是特地来寻求胡广凌的搭救,说完,黄姓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卷画轴,递给胡广凌。
胡广凌接过画卷,看见好端端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少爷,此时竟混得这般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像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一时间心头百感交集,他说:“你二人大可放心,这英国人与日本人向来是心存芥蒂,只要是躲在我的医馆里,他们绝不会找到你们,明日一早,我便托熟人将你们带出上海。”
这夫妻二人听到此处,立刻跳了起来,说自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再留下去恐怕夜长梦多,而且事情万一牵连到胡广凌的身上,岂不是旁生枝节?
胡广凌觉得他们说的有几分道理,而且白天“日租界”发生了日本人遇刺事件,这地方的确是不宜久留,万一让日本特务知道了,有一个受了枪伤的人躲在自己的诊所,到那时,平谷一郎怕也保不住自己了。
可话虽如此,这深更半夜的,如何把两个大活人送出城去呢?
正思索间,忽听门外响起一连串急促的叫门声。胡广凌急忙把这夫妻二人藏进手术室,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出声,自己则像平时一样,慢悠悠地走去开门。
门一打开,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胡广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校友——平谷一郎。他身后还跟着十几名穿着黑色制服、面色铁青的日本人。
【未完稿】
烧红的月亮
1
很久以前,在网上认识一个学习美术的男孩。他时常在博客里,展出一些精美绝伦的油画作品。有人物,也有景物。画风唯美、细腻,栩栩如生。配图文字具有古典诗词般的浪漫气息。这种文艺格调浓重的圈子,总能吸引很多年轻人的目光。点击率飞速增长。
但是,他和一般的画家有所不同。每当他挂出一幅新作品时,他都要在色彩艳丽的油画下面,贴上一幅名为“时间之眼”的素描本。内容和之前的油画遥相呼应。若前者是苍翠欲滴、生机盎然的莽莽林海,后者则是枯枝败叶、死气沉沉的阴暗荒原。若前者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的繁华都市,后者则是万籁俱寂、渺无人烟的贫瘠小镇。若前者是风华绝代、艳冠群芳的绝世佳人,后者则是衣衫褴褛、满目凄凉的老迈妇人。
每每看到此处,我都会感到窒息般的压抑与难过。那种用铅笔勾勒出的潦草图案,充斥着空虚、无助、灰暗、绝望、阴郁和死亡的气息。仿佛使人类褪去一切华而不实的骄傲伪装,直面镜子里的自己是如何的丑陋与凄惨,令人对未来心生庞大而森然的恐惧感。无法逃避,更无法退缩。
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那样大煞风景,总要破坏人们心中的美好景致。
他说,美丽的事物总是短暂而匆忙,它们没有永恒的根基。
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
我们从来不问对方的身份和姓名。他叫我伯爵。我叫他佛朗。
佛朗经常说,人们总是习惯相信眼前的美好,而忘了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有从辉煌走向衰败的那一天。花开自有花落,相聚还有别离。时间就像一只目不转睛的眼睛,它看清了虚假,看清了残缺,也看清了岁月的残酷。
这就是为什么“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总会在时间的注视下,露出马脚。
我说,这就是你的人生哲学吗。
他说,不!是惨痛教训。
2
佛朗曾经画过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油画。画面中,暗黑色的油墨将天空晕染的深邃而富有神秘感。一个形销骨立的男人,蹲坐在一块布满青苔的石板上,神色漠然地眺望着远方繁星密布的无垠夜空。一双充满希冀的眼睛,仿佛流淌出清冷的银色光芒,澄澈明亮,让人不忍注视。
佛朗异常偏爱这幅油画。把它挂在博客最显眼的首页,让每一个浏览者进来都能看见它。
我问他,这个眼睛漂亮的男子是谁。
他说,是一个傻子。
他的回答,曾经让我一度以为,画中的男子就是佛朗自己。只不过他不承认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那幅画不止一幅,而是一套有主题的系列作品。名为“月殇”。每幅油画,都是以那名男子为主角进行创作的。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画中的男子变换着各种姿势、角度,但无一不是仰望星空的姿态。仿佛那是他不可违背的一项使命。
佛朗给男子的眼睛绘出了迷人的光影效果,使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盏盛满月光的透明玻璃杯。
大概是我看得太仔细吧。我有一天忽然发现,这几幅油画虽然都以辽阔无垠的星空为背景,但是,却没有一幅画出现过真正的月亮。连月亮的影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