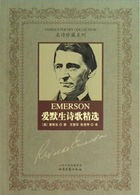可怜的焦有两三天惊恐不安。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去拉塞尔广场老宅,而瑞蓓卡小姐也不再提起他的名字。瑞蓓卡在塞德立太太面前必恭必敬,感恩不尽,那位慈爱的太太带她逛商场,上戏园子,看得她眼花瞭乱,喜不自禁。一天,爱米莉亚头疼,不能去参加两人都受到邀请的一个娱乐聚会,瑞蓓卡害怕独自前往。
“亏你想得出!我是无父无母,全托你的福,这辈子有幸体会到欢乐,温暖的味道。我怎么能丢开你,自己去玩?决不!”说着,她眼睛看向上方,两泪汪汪;于是塞德立太太肯定,她女儿的朋友跟她一样的善良,真讨人喜欢。
老塞德立先生玩笑,令瑞蓓卡总是笑个不停,而且笑得那么真诚,着实令随和的老绅士高兴并且感动。瑞蓓卡小姐不仅赢得这家主子的喜爱,连女管家布伦金索普太太对她也有好感。事情是这样的:布伦金索普太太正在做紫莓果酱,瑞蓓卡对这项手艺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和兴趣,令女管家感动。她还坚持对桑波使用敬称,叫他“桑波先生”,使那名听差受宠若惊。每次吩咐太太的女仆,她都要说给她们添了麻烦表示抱歉。总之,她待人接物是那样柔和有礼,使门厅里的仆佣几乎跟客厅里的东家一样喜欢她。
有一回,在浏览爱米莉亚从学校里寄回家来的一些图画时,瑞蓓卡突然看到一幅画,竟泫然泪下,奔出室外。那天恰恰是焦·塞德立在妹妹回家后第二次到拉塞尔广场老宅来。
爱米莉亚赶紧追出去了解她的朋友为什么一下子如此伤心。这位善良的姑娘是独自回来的,心情也很激动。
“妈妈,您知道,她父亲曾是我们在契绥克的图画老师,我们的作业其实很多是他自己画的。”
“我的宝贝!我明明听到平克顿小姐经常说他根本不碰你们的作业——他仅仅把那些画装裱起来。”
“干这样的活就叫做‘装裱’,妈妈。瑞蓓卡还记得这幅画,也忆起父亲作此画时的情景,现在睹物思人,突然——您知道,她——”
“难得这可怜的孩子如此不忘亲情,”塞德立太太感动了。
“我希望她能跟我们一起再住一个星期!”爱米莉亚道。
“她和我在达姆达姆经常见到的卡特勒小姐极相似,只是头发和肤色浅些。卡特勒小姐现在嫁给了炮兵队的军医蓝斯。告诉你们,女士们,有一次十四团的昆丁跟我打赌——”
“哦,约瑟哥哥,这故事我们听过,”爱米莉亚笑着说。“你就打住吧,怪费力的,还是劝劝妈妈给一位姓克劳利的什么爵士写信替可怜可爱的瑞蓓卡请个假吧。瞧,她来了,她的眼睛都哭肿了。”
“现在我好多了,”那姑娘说着,灿烂地笑着接过塞德立太太伸出的手,恭恭敬敬吻了一下。“你们对我都这么好!每个人都是,”她哧哧地笑着又加一句,“就您除外,约瑟先生。”
“就我除外?!”约瑟说时已在考虑立刻逃走。“我的主啊!仁慈的上帝啊!瑞蓓卡小姐!”
“是的;您的心肠也太狠了,首次见到您,在饭桌上您就骗我吃了辣得流泪的咖喱饭。您可不像亲爱的爱米莉亚那么可爱。”
“他还不知道你那么怕辣,”爱米莉亚为他辩解。
“亲爱的,谁对你不好,我帮你跟他算帐,不管他是谁,”塞德立太太说。
“那天的咖喱饭确实棒极了,没可挑剔,”焦十分认真地说。“可能里边香橼汁少了点儿;对,没错。”
“那么淇漓怎么解释呢?”
“天哪,一只淇漓把您辣得哭天喊命!”焦不禁记起那滑稽的一幕,开怀大笑,而这阵笑声照例又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
“下次对于您为我挑的东西我得多加注意,”瑞蓓卡说;这时又该下楼去吃饭了。“我们这些女孩子怪可怜的,又不招惹是非,原先我以为男人们不会捉弄我们,开我们玩笑的。”
“我起誓,瑞蓓卡小姐。我绝对不想伤害您。”
“当然,”她说,“我知道您无意伤害我。”她在约瑟手上轻轻摁了一下,马上慌张地缩了回来,先是看了他一眼,然后低头目视压地毯的金属棍条。要说那单纯的姑娘这腼腆温柔、有意无意的一摁打动焦心扉,我可不敢担保。
这是她的一次主动出击,某些恪守礼教、绝不逾矩的女士也许会斥之为有失体统;可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事可怜可爱的瑞蓓卡都得依靠自己。一位公子哥儿若是寒酸至无力承担佣人费用,那么,无论他原本多么养尊处优,必须自己动手打扫房间。一个好姑娘如果没有妈妈为她寻觅金龟婿,也只得亲自出马。庆幸天见可怜,这些女子没有更多地施展她们的魅力!否则我们绝对无法抵挡!她们只消表示那么一点儿好感,男人们立即会跪下来,即便老或丑。我说的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女人若是自身条件还可以,除非十足的驼背,可以嫁给她喜欢的任何人。感谢上帝,这些妙人儿好像旷野里的猛兽,并不知道她们自己的威力之大。要是她们知道的话,我们可就永不见天日了。
“怎么回事!”约瑟进入饭厅时心想,“我真的开始产生在达姆达姆跟卡特勒小姐交往时那种感觉了。”
吃饭的时候,瑞蓓卡小姐屡屡主动与他交谈,多半是关于菜肴,言辞不多,却柔媚动人,半似撒娇半似玩笑。其时她已完全融入这个家庭;至于两位姑娘,她们相亲相爱,如同亲姐妹一般。未出嫁的少女在同一所房子里一起待上十天再正常不过。
仿佛下决心要全力促成瑞蓓卡的计划似的,爱米莉亚提醒哥哥,上次他们全家一起过复活节那阵子(“当时我还上小学,”她笑着说),约瑟向妹妹许过一个愿——承诺要带她去沃克斯霍尔。“现在瑞蓓卡也在这里,”她说,“正好同行。”
“哦,真开心!”瑞蓓卡说着正欲拍手称庆,但她及时自警,立刻恢复文静,没有失态。
“今晚不成,”焦说。
“好,那就明天。”
“明天你爸和我要出去吃饭,”塞德立太太道。
“难道你以为我会去游乐场,塞德立太太?”她丈夫问。“再说,这年龄和身体根本不适合这样潮湿的鬼地方生病怎么办?”
“孩子们总得有人陪着才行,”塞德立太太还是担心。
“让焦陪她们去,”做父亲的笑道。“他相当大了。”
听到这句话,连侍立在餐具柜旁的桑波也不小心笑出声来。可怜的胖子焦此刻恨不得把他的亲老子置于死地。
“帮他把紧身马甲脱掉!”狠心的老绅士继续说。“瑞蓓卡小姐,往他脸上洒些凉水,要不干脆扶他上楼去:这可怜虫几乎要晕过去了。真是活受罪!把他带到楼上去吧;反正他身轻如燕!”
“要是再这样拿我开涮,先生,我发誓——!”约瑟怒气冲天。
“桑波,给焦斯少爷备大象!”做父亲的吩咐道。“吩咐人到动物园去,桑波。”但是看到焦气得都快哭出来了,幽默的老绅士才向儿子伸出一只手正经道,“焦斯,在我们交易所里这都司空见惯;桑波,别管大象了,给我和焦斯少爷每人一杯香槟。这样的香槟就连波尼的酒窖都没有,我的孩子!”
一杯香槟入肚,约瑟的心理恢复了平衡,在瓶底儿朝天之前(他有病在身,所以仅喝了大半瓶),他已答应陪两位姑娘去逛沃克斯霍尔。
“每个姑娘必须有一位先生陪着,”老绅士说。“焦斯肯定会冷落爱米,他的心思全用在瑞蓓卡小姐身上都嫌不够呢。还是邀请九十六号的乔治·欧斯本同行。”
笔者浑然不知何故,塞德立太太听后,向她丈夫瞅了一眼就笑了。塞德立先生的眼睛里闪起一种难以形容的调皮神情,他把目光投向爱米莉亚;爱米莉亚则垂头不语,脸上刷地泛起红晕——特有的十七岁的姑娘脸红,而瑞蓓卡·瑞蓓卡小姐此生从不会这样脸红——至少自从她八岁时从食橱里偷果酱让教母当场逮住后,就没再红过。
“爱米莉亚最好写个简帖儿,”她父亲说,“也让乔治·欧斯本欣赏一下咱们的小爱米从平克顿女校带回来一手书法有多漂亮。还记得吗,爱米?你写信邀他共度第十二夜那回,你写的twelfth(第十二)掉了一个f。”
“都过去好几年了,”爱米莉亚说。
“可是好像就在昨天,你说是吗,约翰?”塞德立太太对丈夫说。
当晚在二楼靠前一间屋里曾有过一次谈话。室内的布置仿佛帐篷,周围印花布幔上的印度图案繁复浓艳,想象丰富,还衬有嫩红色的布里子。帐内铺着羽绒被褥的床上有两个枕头,枕上搁着两张气色红润的圆脸,其一戴着镶花边的睡帽,另一个戴着顶上有流苏的普通布睡帽。在这次对话中,塞德立太太责备丈夫不该如此奚落可怜的焦。
“塞德立先生,你也太过分了,”她说,“竟忍心这样折磨那可怜的孩子。”
“我亲爱的,”带流苏的布睡帽辩解。“焦斯实在死要面子,与你一辈子最爱面子的时候相比更甚,这不能小视。当然,大约三十年前,在一七八几年那会儿,你有虚荣心无可厚非,我没有意见。可我实在厌烦焦斯和他那扭扭捏捏的公子哥儿德性。他自认比《圣经》上的约瑟更有魅力,我亲爱的,这孩子整天尽在想他有多么漂亮。很可能,太太,他还会给你我惹不少祸事呢。眼下爱米的小朋友正努力地在钓他这条鱼——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焦斯不被她钓走,也会有别人的。他命中注定是女人的猎物,正像我命中注定每天得上交易所一样。他没给咱们带个黑种儿媳妇回来已经是祖上保佑,我亲爱的。记住我这话:哪个女人最先下手钓焦,焦就是谁的。”
“她明天一定得走,那个鬼丫头,”塞德立太太的口气非常坚决。
“她跟别人没啥区别,塞德立太太?那姑娘至少还不是黑面孔。就我而言,谁嫁给焦并不重要。只要焦喜欢。”
交谈到此为止,或者被鼻子里发出的一阵阵还算轻柔却不浪漫的乐声所代替。除了教堂正点打钟和更夫报时外,位于拉塞尔广场的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约翰·塞德立先生宅内悄然无声。
当早晨来临时,和蔼的塞德立太太已放弃她夜间所说决不挽留瑞蓓卡小姐的扬言,所有感情中母亲的妒忌心更强烈、更寻常和天经地义,然则她毕竟无法想象这个温良谦恭、知恩图报的小家庭教师胆敢觊觎像波格利沃拉的收税官这样的白马王子。另外,为那姑娘请求推迟到职日期的信已经发出,很难借故再突然打发她走。
仿佛一切都商量好了要成全温顺的瑞蓓卡似的,居然天公做美,不过开始她并不领会老天的一片苦心。在约好去逛游乐场的当天傍晚,乔治·欧斯本先生来吃饭,塞德立先生和太太则应邀去了海伯利仓和高级市政官保尔斯共进晚餐,不料骤降大雨,大概只有逛游乐场的夜晚才会如此风狂雨暴,于是年轻人被迫置留家里。欧斯本先生看来丝毫不因此败兴。饭厅里只有他和约瑟·塞德立两人畅饮,喝掉的红葡萄酒不在少数——对酌时塞德立大讲他最得意的印度故事,因为和男人在一起他一贯健谈。后来爱米莉亚·塞德立邀大家到客厅,四个年轻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都说真得感谢这场雷雨使他们放弃逛游乐场。
乔治·欧斯本是约翰·塞德立的教子,二十三年来始终被视为这家的一名成员。他出生才六个星期便收到了约翰·塞德立的礼物——一只银杯;半岁时,礼物是一件带金哨子和小铃铛的珊瑚咬环。从乔治少年起,每年圣诞节老绅士都要给他压岁钱;乔治每次度假结束返校时还有零花钱。他清楚记得,约瑟·塞德立揍过他一顿,那时后者已是个青春洋溢而又笨手笨脚的胖小伙子,而乔治还是个十来岁的莽撞顽童。总之,因为互相关爱,频繁往来,乔治与他们已亲如一家人。
“塞德立,你可记得,我把你一双黑森靴上的流苏剪了下来,你怒发冲冠,多亏塞德立小——”他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改口道,“多亏爱米莉亚跪下来苦苦哀求,我才免挨一顿揍。”
那件特殊的事情焦斯记忆犹新,但他赌咒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临去印度,你坐了双轮马车到绥希泰尔博士的学校来看我,送我半个畿尼,拍拍我的脑袋,还记得吗?我一向以为你身高至少有七英尺,可是当你从印度回来时,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直不可思议。”
“塞德立先生真情感动天,特地到学校里去看您,还要给您钱!”瑞蓓卡以无比欣喜地赞叹。
“是的,他不记我剪掉他靴子上流苏的仇,实属不易。男孩子上学时从不忘记那些零花钱,也不会忘掉是谁给的。”
“我很欣赏黑森靴的款式,”瑞蓓卡赞同。
焦斯·塞德立对自己的两条腿尤其钟爱,总是穿这种花里胡哨的靴子,听到这句话更加不可一世,尽管当时腿缩到椅子底下。
“瑞蓓卡小姐!”乔治·欧斯本道。“您的绘画惟妙惟肖,您一定得把有关这靴子的历史场景汇成一幅雄壮的画卷。画上的塞德立穿鹿皮裤,一手拿着一只流苏被剪坏的靴子,另一只手揪住我衬衫领口的褶边。爱米莉亚跪在他旁边,举着一双小手;那幅画搭配一个壮美的譬喻式标题,就像《正传》和识字课本的插图那样。”
“在这儿恐怕不行了,”瑞蓓卡说。“我会在——我离开以后再把它画出来。”说到这里她语无伦次,显得黯然神伤,以致每一个人都对她深情的表示,真有点儿舍不得与她分手。
“真希望你能再多住些日子,亲爱的瑞蓓卡!”爱米莉亚说。
“何必呢?”瑞蓓卡回答时神情更加悲伤。“这只会让我在离开你们时更加不——更加依依不舍。”说到这里,她扭过头去。
爱米莉亚生来爱哭,笔者已经有所交代,那是这个小傻瓜的一个毛病,现在她自然泪如泉涌。乔治·欧斯本瞧着两位姑娘,既感动又好奇;约瑟·塞德立低头打量他心爱的黑森靴,从他硕大的胸腔里发出一种酷似叹息的声音。
“塞德立小姐——不,爱米莉亚,我们听音乐吧,”乔治说,此刻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动,简直无法抑制,不顾有人在场,只想把爱米莉亚搂在怀里吻她的脸蛋儿。她疑视乔治片刻,如果我说在那一瞬间他俩坠入了爱河,恐怕不很妥贴,因为事实上这一对青年从小就由双方的父母按这一目标加以培育,他们的婚姻在十年前就已被敲定。此时他俩走向小客厅里的钢琴;由于那里比较暗,爱米莉亚小姐坦然让欧斯本先生拉着她的手,因为让乔治在椅凳之间择路肯定能比她看得更清楚。不过因此前客厅桌旁便只留下约瑟·塞德立和瑞蓓卡两个人了,后者忙于用绿色丝线编织一个钱包。
“府上的秘密早已众所周知,”瑞蓓卡小姐说。“他俩的心思显而易见。”
“等他当上了连长,”约瑟说,“我想他们也就会结婚。乔治·欧斯本是个挺棒的小伙子。”
“令妹实在是世上最可爱的人,”瑞蓓卡说。“能捕获她芳心的男人真是好福气!”说着,瑞蓓卡小姐一声长叹。
一对未婚男女在一起议论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们彼此间即已形成某种相当信任和亲密的气氛。此时塞德立先生与那姑娘在谈些什么,并没有必要加以介绍;从上面的例子易出猜出,这次谈话既不会费尽心机,也不会言辞滔滔——人们私下交谈或者在任何其他场合很少如此,除非在华而不实、挖空心思的小说里。由于隔壁有音乐,谈话自然保持低调,不过他们即使高声说话,其实也不会打扰隔壁那一对儿,他们自己的事儿还应接不暇。
约瑟·塞德立跟一位异性说话竟丝毫不害羞或犹豫,几乎前所未有。瑞蓓卡小姐问了他许多有关印度的问题,他趁此机会叙述关于这个国度和他自己的许多趣闻轶事。他描绘了总督府里举行舞会的场面和他们在炎热天气里纳凉的办法,如手拉的布屏风扇、用香草根编结借以隔热和避秽气的湿帘子以及其他各种装置;在谈到倚仗总督明托勋爵的那些苏格兰人时,他的词语非常风趣。接下来他讲了一次猎虎的经历,讲了他的象夫如何被一头发怒的大象从座位上掀下来。总督府的舞会令瑞蓓卡小姐心驰神往;那些个苏格兰侍从武官的德性则令她忍俊不禁,并且称约瑟·塞德立先生是个说话够损的刻薄鬼;而大象摔人的故事又使她花容失色!
“为令堂着想,亲爱的塞德立先生,”她劝说道,“为您的朋友们着想,答应我:以后定要拒绝这种可怕的探险。”
“没关系的,瑞蓓卡小姐,没事儿,”他说着把好几条衬衫领子拉平些;“危险只会增加这项运动的刺激感。”其实,他总共只参加过一次猎虎行动,也就是以上讲述的那回,当时他可以说捡了一条命——倒不是虎口余生,而是几乎吓死。他越说,胆儿越大,居然鼓足勇气问瑞蓓卡小姐:她编织那个绿色丝线钱包是谁的?他为自己的表现那样洒脱不羁而惊讶不止,也欣喜万分。
“谁用得着,钱包就给谁,”瑞蓓卡小姐答道,与此同时向他投递了蕴含着千种风情、无穷魅力的一眼。
塞德立正打算说出一番最最精彩动听的话来,而且已经开了头:“哦,瑞蓓卡小姐,您是多么——”不料隔壁小客厅里的一首歌正好结束,使约瑟十分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于是他突然打住,涨红了脸,紧张失措,便使劲擤鼻涕。
“您有没有领教过令兄的口才?”欧斯本先生悄悄对爱米莉亚说。“您的朋友创造了奇迹。”
“那不是挺好吗?”爱米莉亚说。类似几乎所有够格儿的女人,她骨子里也是个红娘,要是能让约瑟哥哥带个嫂子回印度去,她一定很开心。另外,这些日子她俩朝夕相处,爱米莉亚和瑞蓓卡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情,发现她有数不尽美德和优点,这是她们一起在契绥克时爱米莉亚忽略。要知道,姑娘的好感发展之快犹如童话里杰克的豆茎,一夜之间便长成苍天大树。倒不是责怪她们,不过这种SehnsuchtnachderLiebe在结婚以后便会递减。喜欢夸大其词的伤感派称之为向往理想,无非说明女人通常都贪婪,直到有了丈夫和孩子,她们原先七零八落的感情才有了集中倾注的目标。
爱米莉亚小姐所知曲目寥寥,或者觉得在小客厅里待的时间太长,此刻该请她的朋友来一展歌喉了。
“您要是先听过瑞蓓卡的歌声,”她对欧斯本先生说,“您就彻底不想听我唱了,”不过她知情自己有点儿口是心非。
“不过我要先跟瑞蓓卡小姐知会一声,”欧斯本说,“不管是对是错,在我心中爱米莉亚·塞德立小姐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歌唱家。”
“您听了再下定论,”爱米莉亚说。
约瑟·塞德立大献殷勤,居然亲自把烛台移到钢琴上。欧斯本表示他坐在黑暗中蛮舒服,但塞德立小姐笑道,她可不愿再奉陪了,于是两人也随同约瑟挪位。
瑞蓓卡的唱功比她的朋友要高得多(不过欧斯本或许不敢苟同),而且这次又特别卖力,令爱米莉亚大为惊讶,因为水平超过从前。瑞蓓卡先唱一首法文歌,约瑟一窍不通,乔治则坦称听不懂;接着她又唱了好几首四十年前流行的通俗小曲儿,歌词内容不外乎英国水手、吾王陛下、可怜的苏珊、碧眼的玛丽之类。据行家说,这些曲子造诣平平,但直抒心境,浅显易懂,不像如今流行的唐尼采蒂音乐中一些个lagrime,sospiri和filjcih那样索然无味。
桑波送茶进来以后,和厨娘一起在楼道上倾听小客厅里的歌声,厨娘听得津津有味,连女管家布伦金索普太太也屈尊加入其中。
在歌唱间隙中进行的闲谈也围绕曲旨,带有荡气回肠的性质。众多小曲中有一首尤为出色——它是这场音乐会的压轴——歌词如下:
啊,无际的荒野凄凉肃杀,
啊,狂风似刀,来势汹汹。
小屋顶下坐落人家,
小屋里炉火通红。
一个孤儿自窗前路过,
他看见全家围炉其乐融融,
更觉得午夜列风猛扎心窝,
更枉言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屋里惊觉这孩子走了过去,
见他腿软心慌晃晃摇摇;
好心的人们顿时心生怜恤,
诚意招呼他归来留宿一宵。
到天明旅人告辞继续跋涉,
虽然好客的炉火仍在燃烧;
愿上苍哀悯世间孤苦的漂泊者!
听,凛冽的风在山巅怒号!
这首歌的情调与前面瑞蓓卡所说的“我走了以后再把它画出来——”那句话异曲同工。唱到结尾处,瑞蓓卡小姐“深沉的嗓音幽咽颤悠”。听歌的人都联想到她即将离去以及她这个孤女的悲惨命运。约瑟·塞德立本来就喜欢音乐,心肠慈悲,瑞蓓卡唱这首歌时他如醉如痴,曲终时深受感动。假如他有勇气,倘若乔治和塞德立小姐按前者的主意不靠近,约瑟·塞德立的单身汉生涯会就此结书,而本书也就无尾而终了。然而,瑞蓓卡唱完那支小曲后,便离开钢琴,把手伸给爱米莉亚,两人一起走到昏暗的前客厅里去。就在此时,桑波端着一只托盘进来,内有三明治、果子冻,还有几只亮闪闪的杯子和玻璃壶,这些东西立刻把约瑟·塞德立的诱惑了过去。当塞德立夫妇赴宴归来时,发现这些年轻人谈兴正浓,以至于连马车驶近的声音也没有听见,而约瑟先生恰好在说:“亲爱的瑞蓓卡小姐,您辛苦了,吃一小勺果子冻吧,您的表演太棒了,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妙极了,焦斯!”老绅士进门就说。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里包含的逗趣味儿,焦斯马上回复到紧张拘谨的沉默状态,接着就急急告辞。他并没有彻夜不眠,反复思考自己是否爱上了瑞蓓卡小姐。不,爱的激情从未影响过约瑟·塞德立先生的日常生活。但他倒是想过:假如在印度办公之余能听听这样的歌曲,那该有多惬意;这小妞儿还挺有修养,她的法语讲得比总督夫人更地道;她要是参加加尔各答的舞会,一定一片哗然!
“显然这可怜的鬼丫头对我有意思,”焦斯心想。“与大多数远走印度的姑娘相比,她也不见得穷到哪儿去。甚至我会落个更糟糕的下场,还不如这样呢,没错!”他便在这样的算计中进入梦乡。
瑞蓓卡小姐是否难以入睡,惦念他明天是否会来?此处自不必说。第二天,就像命中注定的一般不可避免。约瑟·塞德立先生午餐前赶到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乔治·欧斯本很奇怪的也已经到了那里,爱米莉亚原是在给契绥克林荫道她的十二位密友写信,这下“全乱了套”;瑞蓓卡照例在做针黹。焦的“巴吉”驶至门前,他跟往常一样先是敲门如打雷,在门口引起一阵骚动;接着,当这位波格利沃拉的前收税官艰难地登上楼梯往客厅里来的时候,欧斯本与塞德立小姐互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他俩带着狡狭的微笑看看瑞蓓卡。瑞蓓卡埋头编织,浅色的鬈发垂向丝线钱包,这一回倒是确定脸红了。约瑟出现在眼前时,她的心呯呯乱跳。约瑟从楼梯上便呼哧呼哧大口喘气;他穿了件新背心,脚登锃亮的靴子咯吱咯吱直响;内衬填料的领巾仍难掩他因体热心慌而涨红的脸。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拘束不已;至于爱米莉亚,我想她甚至比当事者更加紧张。
桑波把客厅门敞开,通报约瑟少爷到,并且傻笑着跟在收税官后面,手捧两束漂亮的鲜花,原来那位行为厅特的公子哥儿居然也懂得向姑娘献殷勤,是特意从科文特花园买来的——如今的女士时兴怀抱卷在锥形镂空纸筒中的花束,几乎大如干草垛子,这两束花虽然没那么大,但是当约瑟极其严肃地鞠上一躬向两位姑娘每人献上一束的时候,她们收到这礼物都很开心。
“做得好,焦斯!”欧斯本在一旁喝彩。
“谢谢你,亲爱的约瑟哥哥,”爱米莉亚说,并且会甘心情愿亲吻她的哥哥,如果后者希望的话。(换了我,如果能得到像爱米莉亚这样娇媚的人儿一个吻,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黎先生所有暖房里的花全部买下来的。)
“哦,此花只应天上有,太漂亮了!”瑞蓓卡小姐惊叹道,还斯文地闻了一下,怀抱鲜花,两眼朝上一翻望着天花板,作心醉神迷状。可能刚才她先往花束中间瞥了一眼,看看里边是不是藏着情书;不过她失望了。
“借花传情的名堂多着呢,塞德立,那些波格利沃拉人知道这个吗?”欧斯本浅笑。
“嗨,别胡说!”多情公子答道。“我在奈森的铺子里买了花;很高兴您能喜欢;另外,我亲爱的爱米莉亚,我还买了一只菠萝,已经交给桑波。咱们把它当小点心吃;炎热的天气里,吃起来一定特别清凉爽口。”
瑞蓓卡说她从没吃过菠萝,太想尝一尝了。
他们热烈地交谈着。我不知道欧斯本借故离开了客厅,也不知道爱米莉亚为何尾随其后——大概是去监督仆人处理菠萝吧,反正只留下焦斯和瑞蓓卡两个人,后者又继续她的女红,飞针走线,令人目不暇接。
“亲爱的瑞蓓卡小姐,昨晚您唱的那支歌太动听了,妙——妙不可言,”收税官说。“我感动得几乎落眼泪;我以人格担保绝无虚言。”
“因为您有一颗宽厚的心,约瑟先生;我认为塞德立一家人都是这样。”
“昨夜我失眠了,脑中都是那优美的旋律。今天上午我在床上还试着哼唱;绝没骗你。郭洛普一我的医生——十一点钟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染病在身,您也知道,每天得麻烦郭洛普来给我看病),天哪!他来的时候我竟唱得尽兴,像——百灵鸟一样动听。”
“哦,您可真有意思!您得唱给我听听。”
“我?不,瑞蓓卡小姐,您唱;我亲爱的瑞蓓卡小姐,还是听您来唱吧。”
“很抱歉,塞德立先生,”瑞蓓卡说着发出一声叹息。“这会儿我的心情烦闷;另外,我必须把这只钱包赶出来。您能帮忙吗,塞德立先生?”
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约瑟·塞德立先生还不知如何帮,已经被指定坐在一位姑娘对面。他看着那姑娘,含情脉脉;他伸出两只胳膊,似在向她恳求,手上撑着一绞绿丝线让姑娘捌起来。
当欧斯本和爱米莉亚进来招呼大家吃小点心的时候,发现这有趣的一对儿竟如此浪漫。一绞丝线已经在纸板上绕好,焦斯先生却还沉默。
“我确定今晚他准会开口,亲爱的,”爱米莉亚握着瑞蓓卡的手对她说。
而塞德立深思熟虑后,暗暗对自己说:
“到了游乐场里我一定要找她问清楚,就这么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