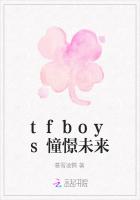离开布莱顿以后,我们的朋友乔治既然是个坐驷马高车旅行的上等时髦人物,当然不能掉了身价,所以命令驭者驱车直接使到凯文迪许广场的一家高级旅馆,那才叫威风。一组豪华荣丽的套房、一张布置得赏心悦目的餐桌以及严然肃立在周围的五六名黑人服侍,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位年轻的绅士和他的新娘。乔治摆出王子一般的派头向焦斯和铎炳尽地主之谊,爱米莉亚十分腼腆而又害羞地生平头一次坐在主妇位子上,用乔治的话说,今番是她做东。
乔治一会儿埋怨酒品太次,一会儿斥责侍者愚蠢,俨然帝王风范;焦斯则大谈其清炖海龟,吃得不亦乐乎;铎炳还给他夹菜。其实汤盆放在女主人面前,理应由爱米莉亚主持分菜,但是她对此道一无所知,认为只要给她哥哥舀汤,却不知道敬上此肴的精华。
筵席之奢侈、客房之富丽导致了铎炳先生的不安,餐后趁着焦斯在大圈椅里熟睡的时候,他对乔治进行劝阻。他认为吃海龟、喝香槟过于浪费,又不是招待大主教,不该如此铺张。但是忠言逆耳。
“我旅行在外,从来不计较花费,”乔治道,“而且,我太太在旅途中也不该显现半点儿小家子气。只要钱包里还有一分钱,她就该应有尽有,”这位阔佬竟敢用偌大口气说话还自以为是。铎炳原本想使他明白爱米莉亚的幸福并不因为清炖海龟,现在也就只得作罢。
饭后不久,爱米莉亚胆怯地表示想去富勒姆看望她妈,乔治嘀咕几句后答应了。她高兴地跑进大卧室,卧室中央放着一张阴森恐怖的大床(“那是联军各国君主来到这里庆祝胜利时哈勒山大皇帝的妹妹睡过的”),高兴又迅速地系好小帽,围上披肩。她回到餐室时,乔治还在那里喝红葡萄酒,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
你不和我一起去吗,最亲爱的?”爱米问他。
“不,最亲爱的今晚有事儿”。他的听差已经给女主人雇一辆街车送她去。雇来的车已经停在旅馆门前,爱米莉亚先是盯着乔治的脸看了一会儿,发现毫无反应,无奈向他行了个屈膝礼,失望地沿着宽阔的楼梯走下去。铎炳跟在她身后,搀扶她进了车厢,然后目送马车向目的地驶去。连乔治的听差不好意思当着旅馆侍役的面告诉马车夫要去的地址,只说等一会再给告诉他方向。
铎炳步行回斯劳特咖啡馆,那是他习惯的落脚点。他肯定在想,此时要是和欧斯本太太一同坐在那辆街车里该有多幸福。乔治的爱好显然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喝够了酒以后,到戏园子花半价看后半场,欣赏基恩扮演的夏洛克。欧斯本上尉是个戏迷,自己曾几次在军营剧社中饰演高登喜剧中的角色。焦斯一直睡到天黑,会很长时间,才被他的听差收拾桌上的酒瓶把剩酒倒空时发出的嗓音所惊醒;当然又得雇一辆街车把这位胖大官人送往其住处,并且扶他上床。
当爱米莉亚乘坐的街车在小小庭院门前停下时,塞德立太太自然急冲冲从屋子里跑出去,迎接啜泣、唠叨的姑奶奶,紧紧搂着女儿,贴在心上,奉献出自己全部炽热的爱。只穿衬衫和背心、没套外衣在整理庭院的克拉普先生,被这情况吓了一跳,赶紧躲开。那名爱尔兰女佣从厨房里飞奔出来,笑嘻嘻道了声“愿老天保佑您!”爱米莉亚费劲的沿着石板路走过去,登上几级台阶跨入小客厅。
任何一位读者只要稍通人情世故,就可以想象这母女俩在屋里没有别人时相拥在一起,肯定哭得死去活来。反正哭哭啼啼是女士们的看家本领。伤心时哭,高兴也哭,不论生活中遇到什么事都要掉眼泪,何况刚刚经历女儿出嫁这样的重大事件,娘儿俩自然要痛痛快快宣泄一下自己的感情,这既能安慰心灵,又可振奋精神。我以前过平时互相痛恨的女人在涉及到婚姻问题时竟然彼此亲吻,抱头哭作一团。所以,倘若她们本来相爱的话,不知要激动到什么地步。慈母在女儿出嫁时会觉得自己又一次做新娘。在此后的系列事情上,谁都知道当妈妈的满怀着无与伦比的母爱。其实,女人在当上妈妈之前,多数不可能真正理解做母亲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要去打扰爱米莉亚和她的妈妈在黑暗的小客厅里说悄悄话、长吁短叹、又哭又笑吧。老塞德立先生便是如此做的。马车在门前停下时,他并不知道到来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跑去迎接,尽管爱米莉亚进屋后他也热情地吻了女儿(他在家时依旧成天整理他的一扎扎文件、账目之类),但和母女俩仅坐了一小会儿,就十分知趣地离开小客厅让她们畅流。
乔治的听差摆出非常高傲的架势,瞧着只穿衬衫和背心在给玫瑰花丛浇水的克拉普先生。不过,他终于给了塞德立先生一点脸面一行了个脱帽礼。老绅士向他打听起女婿的情况、儿子的马车,焦斯的马是不是也去了布莱顿,还问及波拿巴这个卑鄙小人和战争;一直聊到爱尔兰女佣用盘子端着一瓶酒出来。老绅士执意请听差喝一杯,还赏给他一枚面值半畿尼的金币,听差收下时,心里既惊异,又不屑。
“朋友,为你东家夫妇的健康干杯,”塞德立先生说,“这点儿小钱你回去后自己买酒喝,朋友。”
虽然爱米莉亚离开这所小屋和家人刚刚九天,但是她告别此地的那个时候距今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现在她觉得过去的生活已如同前世。她几乎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那样回顾、凝视那个迷恋中的未婚少女,那时她除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外,对什么都置若罔闻,对待父母的慈爱虽非不仁不义,至少也是理所应当地加以接受——她把整个灵魂和全部思想都贯注于实现一个愿望。追忆那些刚刚过去却显得这般遥远的日子,令她感到惭愧;看到慈爱的双亲,她禁不住暗自责骂。既然梦寐以求的大奖已经到手,生活应该富丽如在天堂——可是获奖者为何依然顾虑重重,仍不心满意足?通常,小说家让他们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走出了婚姻这一步,便可闭幕,似乎戏已演完,疑云消散,奋斗完结;似乎一旦进入婚姻的温柔乡,便是一派满目苍翠、百事顺遂的好景色;似乎丈夫和妻子无所事是,只需挎着胳膊一起走向未来,在幸福美满的岁月中走向暮年。但我们的小爱米莉亚刚在她那片新天地登岸,却已经忧心忡忡地回过头去,遥望隔着一江春水从对岸向她挥手告别的亲人们悲凉的身影。
为了庆祝女儿回娘家,做母亲的少不得要作一番准备以添喜气。在成车的话慢慢卸去了一些之后,她暂且向乔治·欧斯本太太告别,跑到底层的厨房兼饭厅里去(那儿往常由克拉普先生和克拉普太太使用,夜里那个爱尔兰女佣弗雷纳根小姐收拾完餐具后,也会摘下头上的卷发纸去坐一会),开始准备一些精美雅致的茶点。人们表达爱心善意的方式不相往庭,塞德立太太则觉得做一些热的松饼,再用车料玻璃碟盛一碟略带苦味的柑橘酱,这样款待第一次来做姑奶奶的爱米莉亚是最好不过的了。
乘这些美味在底层操办的间隙,爱米莉亚离开小客厅上楼,不知不觉来到她出嫁前住的小房间,坐上她时常在那里发呆犯愁的一把椅子。她靠着扶手椅背,就好像扑到老朋友的怀里,静下心来思考过去的一个星期和以前的生活。才作新人便已经在怅然若失地回首往事;老是苦苦追求着什么,一旦得到后,疑虑和悲伤却多于欢乐——可怜这个从不招谁惹别人的小东西,命里却注定要在名利场上苦苦挣扎的茫茫人海中漂泊、落迫。
她坐在那里,满怀柔情地回忆她在闺中那么崇拜的乔治的形象。但她是否认识到,乔治本人与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个白马王子有多大区别?这要在好多好多年以后,并且那人必须确实很坏很坏,一个女人才能克服自尊心和虚荣心的抵抗,承认这一点。在乔治的印象之后,则是瑞蓓卡的一双闪着绿光眼睛心怀不轨地微笑着浮现在她的头脑里,搅得她忐忑不安。她就这样坐了一阵子,沉浸在对自身命运的习惯性惆怅之中,不久前忠厚老实的爱尔兰女佣给她送来乔治旧事重提的求婚信那天,见到她正是这副郁悒寡欢、无精打采的模样。
她望着前此日子以前自己还睡过的白色小床,真想今晚就睡在这里,翌晨醒来能和以前一样看到母亲爬在床前向她微笑。这时她记起了凯文迪许广场豪华旅馆里的那间卧室虽然富丽堂皇,却是大而无当,阴暗深沉,那里等着她的花缎帐篷式大床阴气逼人,使她颤颤发抖。亲爱的白色小床!无数个漫漫长夜她曾在这张床上敧枕暗泣!当初她是多么绝望,只盼着在这张床上老去!如今她的所有梦想不是都成为现实了吗?她为之肝肠寸断的恋人不是永久属于她了吗?以前慈祥的母亲总是十分耐心和关怀备至地守护在这张床畔。爱米莉亚走到在床边跪下。这个受伤的女子胆怯荏弱,却有一颗柔婉的爱心,她在向上苍寻求安慰;应当承认,我们的小爱米过去还几乎没有求告过神明。迄今为止,爱情就是她的信仰;现在,这颗受伤、失望的心在流血,开始感到需要另一种抚慰。
我们没有权利重复或偷听她的祷告。诸位,这是人家的隐私,超出了本书定位的名利场这一范围。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当茶点终于端到小客厅里供姑奶奶享用时,我们这位年轻女士下楼时变得开心多了,她不再心灰意冷,不再埋怨命运,也不像近来习以为常的那样去想乔治的冷漠或瑞蓓卡的眼神。她下楼梯来到小客厅里,亲吻了父母亲,跟老绅士说说笑笑,塞德立先生已经许多日子没这样兴奋了。爱米莉亚坐在铎炳为她买的那架钢琴前,自弹自唱她父亲爱听的那些老歌。她说今天的茶点非常可口,并且赞赏柑橘酱盛在小碟子里显得极有品位。她决心要使别人都开心,自己也从中得到欢乐。回去后,她在阴森森的大帐篷里酣睡,直至乔治从戏园子回到旅馆,她才含笑醒来。
次日,乔治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这可比去看基恩先生演夏洛克更为重要。他刚到伦敦就给他父亲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写过一封信,盛气凌人地表示希望在第二天会见那里的律师。为了付前些日子他在布莱顿旅馆里打台球、玩纸牌输给克劳利上尉的赌账,几乎掏空了这位年轻人的钱包,他在出征前不得不把钱包重新装满,而他没有别的资金来源,除非动用律师受托付给他的那两千英镑。乔治自己心中一直坚信他父亲过不多久便可心回意转。哪一个做老子的能长期不认像他这样才貌双全、十全十美的儿子?如果说他过去的诸般好处、浑身优点不能使他父亲平息愤恕,那么乔治决心在即将打响的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定教老爷子向他屈服。万一还是不让步坭?怕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在牌桌上也许会时来运转,两千镑还够他花一阵子的。
于是他再次打发爱米莉亚坐车去她妈妈那儿,再三嘱咐她们娘儿俩尽可以放心购买乔治·欧斯本太太这等地位的女士即将出国旅行需要的所有东西。这母女二人只有一天工夫购置一切,可想而知她们有多么辛苦。塞德立太太又像从前一样坐上了马车,穿梭于时装店和内衣铺等处所,离开时由点头哈腰的伙计或有礼有节周到的业主送上车,她几乎重又找到了过去的自己,从她家落迫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打心眼里高兴。同样,乔治·欧斯本太太对于逛商店、看橱窗、讨价还价、买漂亮东西也决不是毫无兴致。(倘若真有哪个女人对于这一切一无所谓,恐怕世上任何男人——即便是最有哲学思想的——都不愿花两便士要她。)爱米莉亚固然是按照丈夫的嘱咐行事,同时自己也觉得开心,所以买了许多女士衣着,在选购时充分显示出高雅的品味和非凡的眼力——所有店铺的老板、伙计都这么说。
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欧斯本太太并不十分担心。她相信几乎毫不费力就可以打垮拿破仑。马盖特的邮船天天坐满了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开往布鲁塞尔和根特。人们根本不像开赴战场,倒像是去观光旅游的。报上全都是嘲笑那个天杀的暴发户兼骗子写的文章。这样一个科西嘉混小子居然敢同欧洲各国联军以及不朽的威灵顿这样的军事天才作对!爱米莉亚对波拿巴表示极度的蔑视。不用说,像她这般温柔委婉,自然把周围的人的看法拿来当自己的,因为她那份儿爱国心实在太幼稚,压根儿没法独立思考。总之,她和母亲劳累了一天的采购,这是爱米莉亚以贵妇人的身份第一次在伦敦亮相,她的表现很有风度,可谓成绩卓越。
那天,乔治歪戴着帽子,挺直腰板,大摇大摆,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倍得福路,昂首挺胸走进律师事务所,仿佛那里所有面色苍白的文书、录事都是他的员工。他吩咐向希格斯先生报告,就说欧斯本上尉等着见他,那副凶狠、傲慢的架势意味着:律师不过是区区平民百姓,只有遵命办事的份儿,即使天大的要事也该立刻停下,过来伺候上尉。(其实这名律师拥有的智商是上尉的三倍,财产是他的五十倍,经验是他的一千倍。)乔治没有看见,屋子里所有的人——从首席办事员到练习生,从服装寒碜的抄写员到绷着太窄的衣裤、面色苍白的跑腿小厮——都在暗暗嘲笑他,而乔治坐在那儿,用手杖拍着靴子,独自认为这些人真是一群没出息的可怜虫。没出息的可怜虫们却完全清楚他的底细。夜里,他们还在自己的俱乐部——小酒店——里跟其他的办事员聊天时喝着啤酒讨论他的事儿。天哪,伦敦的律师以及律师手下的办事员们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乔治走进希格斯先生的办公室时,也许希望那位律师受托向他转达他父亲愿意妥协或和解的消息。也许他摆出目空一切、不屑一顾的架势是要别人以为这是勇气和决心的表现;倘若这样,那么律师的反应却冷淡得令人寒心,使乔治的不可一世变成无的放矢。上尉进去时,希格斯先生装作正在撰写一份文件。
“请坐,先生,”律师说,“我过一会就着手解决您那件事儿。坡先生,请准备好办理交割的有关单据,”说完,又埋头继续写他的文件。
坡把单据递了过来,律师把两千镑公债按当天行情结算好以后,问欧斯本上尉是要一张银行支票呢,还是想用这笔钱购买有价证券。
“受托管理欧斯本太太遗产的几位中有一人此时不在伦敦,”他漠然道,“但我的委托人愿意配合您的希望尽快了结此事。”
“就给我支票吧,先生,”上尉双眉紧锁说。“尾数的先令和便士统统省略,先生,”他在律师开支票时又补充了一句,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此大方的一招定教这老东西无地自容。然后,他把支票揣在兜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用不了两年,这小子就会因债务而蹲监狱,”希格斯先生对坡先生说。
“先生,您不认为老欧斯本可能回心转意吗?”
“除非石碑会自己转过身来,”希格斯先生答道。
“他正在疯狂乱花钱,”那名办事员说。“他结婚才一个礼拜,但昨晚我瞧见他和另外几名军官在散戏后把海弗莱尔太太扶上马车。”之后律师叫他把另一宗案卷取出来,随后乔治·欧斯本先生便从这两位可敬的绅士记忆中消失。
支票指定的兑付者乃是伦巴第街我们熟悉的哈尔克和布洛克银公司,乔治便奔赴该处,仍然以为自己的身价并未改变,并从那里取了款。乔治走进银行时,弗雷德里克·布洛克先生恰巧也在,正俯身指点一名显得很拘束的雇员如何记账。他看到上尉后,一张黄脸变得更加灰黄,接着他便心虚地溜到后面客厅里去了。乔治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大数额的一笔钱,所以一下子眼花了,无心注意他妹妹的黄脸未婚夫神情有何变化,也没发现后者是怎样溜走的。
弗雷德·布洛克向老欧斯本汇报了他儿子到银行去的经过和所作所为。
“他厚着脸皮走进来,”弗雷德里克说,“提走了所有的钱,连一个先令也不落下。像他这样阔手阔脚,千儿八百的能坚持多久?”
老欧斯本发出恶狠狠的咒骂,说他才不管这小子什么时候花光这笔钱。如今弗雷德天天上拉塞尔广场吃晚饭。但不管怎样,乔治办完这一天的事儿还觉得挺心满意足。他自己的行装很快就全部准备妥当,爱米莉亚购物的账单他全部开了支票由他的代理人付款,气派之大不输那此达高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