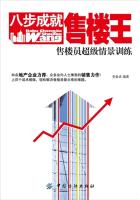我去仙女堡家访的时候正好遇到杀猪。肥滚滚的猪被三四个男人从猪圈里拖出来,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嚎,一点不像没了胆的猪。宽大的杀猪凳摆在院坝里,旁边没有像通常那样放一个盛血的脚盆。烫猪的大黄桶摆在柿子树下。刀儿匠扎着皮围腰,嘴里还叼着纸烟,黑亮的刀子便抹进了猪的颈项。刀儿匠砸了口烟,刀子才开始在猪的颈项里搅。血喷在地上,热气伴随着血腥气。非常新鲜的血,看上去一点不像瘟猪的血。猪的叫声弱下来,四肢乱蹬——大峡谷的人叫打冷拳。有人担了烫猪水从屋里出来。一挑两挑三挑,倒进大木桶。刀儿匠一只手往桶里倒事先准备好的冷水,一只手伸进桶里风快地搅动,测试着水温。几个人搭手帮刀儿匠将猪抬过来丢进黄桶,刀儿匠一手逮猪尾巴一手逮猪前腿上下晃动,一刻也不停息。我站在旁边没看多久,黑猪就变成了白猪。捅了皮,吃了气,在黄桶上搭了木杠,让拔光毛的猪骑在上面。刀儿匠拿了瓢舀水冲了猪身,边冲边刮,顷刻猪变得雪白。雪白的猪骑在木桶上,除了颈项上的刀口,其余都完美无缺。眼睛还睁着,耳朵还立着,尾巴还翘着,像是要奔跑。宰杀这样一头肥猪,主人家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刀儿匠和帮忙搭手的人也应该是很高兴才对,可都是愁眉苦脸的——害怕又是头被人抽了苦胆的猪,连庖汤也吃不上一口。
开膛的时候,来了很多人,睁大眼围着挂在柿子树上的肥猪。主人家的眼睛睁得最大。女人怀里孩子也圆睁着眼忘了咂奶。一刀下去,猪肚子开了,白花花的油翻了出来,接着露出了红艳艳的内脏。刀儿匠没有像往常先取出心、肝、肺,而是直接掏出胆囊摘了下来。刀儿匠用刀尖摘胆囊的动作干净利落,声音轻得像一片干枯的柿子叶掉在地上。
奇迹没有发生,摘下的胆囊干瘪瘪的,皱巴巴的囊壁上有一个明显的针眼;剖开,里面只剩几滴浑浊的胆液。刀儿匠把胆囊拿给主人家看,男主人再拿给从屋里小跑出来的女人看,边看边指着针眼。开了膛的猪挂在柿子树上,再没有人去动它,也再没有人想去动它。主人家、刀儿匠、帮忙搭手的人和看热闹的人都开始吃闷烟。还有人在看挂在柿子树旁边一棵落光叶子的花椒树上的胆囊,指着针眼嘀咕。花椒树下花椒落了一地,高处的枝条上还剩着一串串花椒,显然是猪肉不能吃,花椒便排不上用场。
我是希望奇迹发生的,那样,我也好美美实实吃一顿庖汤。很久没有吃肉了,更别提吃庖汤。吃庖汤吃心,吃肝,吃肺,吃竹笋炒坐登。坐登就是猪屁股上的肉。现在都不吃肺了,觉得是下料。其实猪肺炖起很好吃,加花椒姜片加两三个干辣椒。小时候婆婆把肺和小肠炖一起,加萝卜,我总能吃上好几碗。吃不上庖汤,每个人都显得垂头丧气。主人家一狠心杀了只鸡,说还是要喝几盅。杀鸡自然是款待我这个老师。在他家的神龛上,老师虽然排在末位,但毕竟在天地君亲之列。
刀儿匠没有喝上这顿“狠心”酒,被别的人家请去杀猪了;都晓得十有八九是白杀,但还是不甘心。
主人家一直没有去管挂在柿子树上的猪(我不知道该称它是猪还是猪肉)。在他们眼里,它已经是个废物,是一堆烂肉一堆垃圾。然而,喝酒没喝酒,在我看来它都还是一头猪,一头肥猪。主人家在酒桌上提起养猪,眼泪哗哗就下来了。“老子要是晓得哪个狗日的抽的苦胆,非把他的皮剥下来不可!”主人家还没上四十,常年在大峡谷淘金练就了一身疙瘩肉,要剥一个拿注射器的人的皮轻而易举。“真有那么一些抽猪苦胆的人吗?”我问主人家。“要是没有,那么多猪身上的针眼是从哪里来的?你刚才也看见,那么肥实的猪,胆咋会是瘪的?”主人家说着说着,就骂起镇子上的干部,说他们都是chua球的,事情闹了这么久连个说法都没有。我也觉得气愤。1992年冬天,大峡谷里出了这样的事,两三个月,还真没给个说法。不管是谣传还是真正的事件,都已经像山火蔓延开了,不应该没有人站出来灭火。
我推着自行车往公路上走的时候,已是大半夜了。仙女堡的夜晚很安静,也很美,具体美在哪里又说不出来。或许在仙女两个字吧。主人家要送我,给我打电筒,我说不必,有昏昏月亮。真的有昏昏月亮,看得见大峡谷的轮廓。远处还有渔火。不是渔火,是淘金人牵的电灯。主人家坚持要送,说顺路把死猪背到河里去扔了。我要他别扔,先盐起来熏干,免得将来后悔。300多斤的肥猪,说扔就扔了,折算下来是一个农民大半年的收入。主人家不听,说可惜老子的盐巴和工夫了,一个人从柿子树上放下猪搁在背上。开了膛的猪随着他酒后的步子在夜里移动,白晃晃的像一朵云。
我捡了一块肉回来在水龙头上洗。她下课路过看见,过来叫我扔了。我说我想吃肉了。她说结婚证都办了,吃肉还会等好久吗?我晓得她说的吃肉是办酒席。我想起一句诗: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过来洗手的学生看见我在洗肉,瞳孔都放大了,舌头也从嘴里拖了出来。我认为所有被扔掉的肉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胆汁的猪的肉也没有问题。她见我舍不得扔,就伸手来抢,紧紧拽住不放。水龙头的水还在哗哗淌。她没有抢赢我,一边洗手一边掉眼泪,好象我吃了这肉马上就要死掉。
雪化过后没出几个太阳就一直是阴天。到处都看得见化雪的水,一滩滩的。除了水泥球场,校园、街道和公路都还是湿的。天光黯淡,灰云均匀地密封着峡谷,无论是晃眼看还是下细看,总觉得有灰烬纷纷扬扬在流泻,从灰云一直流泻到山腰,流泻到河谷。山腰以上都没在灰云里。大峡谷没有尽头。不是它的境域,而是一种感觉,一种近似于我们对时间对宇宙的感觉。河谷里的最后一片红叶凋落了,清澈但依旧丰沛的河水或急或缓地流淌着,感觉不到一点人情味。永恒在有限的失却了时间的大峡谷,以流水的姿态,以黯淡的色泽,以虚无的本性呈现出来,像那些从石头里蹦出神来的雕塑。
我把肉煮了。她说要吃你一个人吃。我一个人吃了。还真好吃,姜味辣味花椒味都很大,但最大的还是山猪的肉味。我买了酒,本来是请了几位同事来吃的,都坐上桌了,又被他们的老婆拖了回去。我吃得香,吃的时候倒真的想起了小时候在生产队吃瘟猪儿肉,青辣子炒卷卷肉,一口一个,没有一滴油水抛洒的。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两天,我吃了肉没一点问题。我要继续捡了肉回来吃,捡了肉回来盐了熏腊肉。她发火了,骂我是土贼,是讨口子。她要搬回她的寝室去睡,她不要我碰她。她这样歇斯底里,还是第一回。
有人听说我吃了抽了苦胆的猪肉没有一点事,也捡了回来吃。教化学的丙斗,她教过的学生青云飞,下街子的韩光棍,天生桥桥头的梁哑巴。有人说还有凡大爷,但凡大爷自己不承认,虽然他的嘴唇较先前油亮了许多。但他们都吃病了。丙斗拉了3天肚子,不好意思去医院拿药,结果严重脱水,被送进卫生院补水。青云飞生了满身红颗颗,在街上抠。还头晕呕吐。韩光棍和梁哑巴无大碍,只是消化不良,找到庙坪上的任兴李摸了食就对了。
整整一个礼拜,我都没一点异常反应,她也相信就是有什么毒素也被代谢干净了。她又允许我碰她了。新房基本上刷白,前后窗玻璃上都贴了彩色的玻璃纸。搭了刚打好的新床作婚床,把旧床抬出去扔在了葡萄架底下——它每天晚上都要咯吱咯吱响,使得我们很被动。后窗外面是一条深涧,比起夏天溪流小了许多,但也白了许多。白里带粉带蓝。响声应该也小了许多,但开了窗户听还是轰鸣。溪水从一个叫自治沟的寨子奔流下来,落差很大,每撞击一处山崖一块石头都好比放了一炮。后檐边的几棵苦楝树和香樟树已经长成精了,高出了我们的房檐好几倍,它们的枝条粗得可以做柱头,有几拨伸到了我们房子前檐。树上的鸟听惯了溪水的轰鸣,像是从不失眠,一大早便在树巅唱歌。它们新鲜得真快啊,舌头一点不带夜晚的懵懂。我们却老是睁不开眼睛,在被窝里搂抱着,相互无论怎样鼓励也下不了起床的决心。说我们纯粹是为了留恋年轻的肉体的温腻也不对。我们还没有真干。我们只是睡不醒,下半身睡醒了上半身睡不醒,心睡醒了身体睡不醒。年轻的时候总是瘫软,没有骨头,也许真的像他们说的“吃了鸦片烟一样”。
中午就看见两个人坐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外的烂藤椅子上。两个外地人。中午又出了昏昏太阳,大峡谷的光线有些迷乱。过去出昏昏太阳并不这样。过去只有出朝霞和晚霞,或者落太阳雨的时候才有这种迷乱。当然有时会更迷乱。太阳光从老木花或黄连溪的驼峰射下来,遇到漂泊的新疆棉花一样的云朵,本来干练炽热的太阳光一下子多了色彩和柔润。两个外地人一身白炭泥,一个仰着,一个趴着。我注意到藤椅旁边他们的包袱,像是已经被翻过,拉链也没有拉上,扔在地上的几样东西也没有捡进去。笛子。漱口用的塑料盅。拖鞋。我已经感觉到了,但我不愿意去想。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也害怕,害怕天黑。她答应晚上做我的女人。她说她不哭。我倒是要哭了。一个男人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得到他从13岁就想得到的东西,内心自然是翻江倒海的。14年的渴想,将他想象的坐标已经安装到一个精确的位置。我从镇政府路过,去葫芦溪为她采摘雪莲花。只有葫芦溪才有雪莲花。
在水沟子的磨坊前面听见两个人正在说话:“今晚上天一黑,总有戏看。”我晓得他说的戏。“都走到仙女堡了,是叫人劝回来的,再往前走,筏子头和白梓杨的人不把他们宰了吃了才怪!”“那是肯定的,都好久没吃肉了,肚子里剐得没一颗油珠珠了。”“跑到阔达来莫非就没人敢宰了他们?镇政府现在也管不了这码子事。”“要真是抽猪苦胆的,老子也愿意跑上十里路去砍两刀。”“那你天黑上街去看不看?我看那两个人多半是抽猪苦胆的。”“我看也是,不吃锅巴为啥围着锅边转?”两个人还在说,风一吹,脑壳上的面粉头皮屑一样往下掉。
我在葫芦溪没有找到雪莲花。我想,葫芦溪原本就没有雪莲花。一位砍柴的老人告诉我有,但要等到来年春天。老人爬上很高的悬崖,为我采摘到一棵无花的雪莲。我觉得无花的雪莲要比纯粹的雪莲花好,它青,每片叶子都很显内敛,茎也显内敛。让我高兴的是,她也这样看。她这样看雪莲和雪莲花,我感觉爱了她更多。
傍晚,大峡谷不知不觉露出蓝天。感觉有凛冽的风,不经意抬头看,就看见了黛蓝。像一个海子,从黄连溪到葫芦溪。那黛蓝,随着夜色一笔笔加深。再看,便看见了月亮。下弦月。等夜空呈现,月亮已经非常显眼。我和她都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我的理解还包含了弗洛伊德式的象征:天空在夜晚的展开,与她身体的展开之间存在一种神奇的缘。还有月亮,亏缺与圆满相互转换的月亮,它就是一个女子身体的一世。
我们在镇子外面的田埂上走,在半路的砖瓦窑逗留,看一码子一码子的砖坯因为冰冻而破裂坍塌。她要去庙坪上看那棵老桂花树,我不想去了,我惦记着天黑。她说老桂花树有月亮那么老了,说过就去望月亮。田野的晚风吹起了她的长发,它们的自由让我心颤——过了今夜它们将被我盘起。已经看得见老桂花树了,隐隐约约在一间木楼和两个草垛之间。记得往年桂花开的时候,我还和她去折了几枝回来插在空酒瓶里。老桂花树的花格外香,有点像酱香型的白酒,越老越淳厚。
我们终究没有去看老桂花树,如果从远处望见不算的话。镇子里传来阵阵喧闹声,看见好多人在夜幕里跑。想到她下次看见老桂花树的时候就不再是处女了,我感到多少有些不安;只是这不安隐隐的,埋得很深。一个人两次看到一棵树,不再是同一个人,不再是同一个身体,这里面隐藏的细节既美丽又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