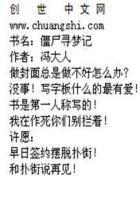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古城合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壮观场面。来自江淮大地各条战线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和“标兵”聚集省城,参加安徽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们滁县地区代表团中午就到达合肥,先在火车站广场集中等候,直到下午三点,才开始出发。代表们排成方队,从胜利路经大东门、小东门、长江路、三孝口,沿着大寨路(现金寨路)南下。
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代表们跳着“忠字舞”、唱着语录歌,载歌载舞,缓缓前行;红色彩旗铺天盖地,红色条幅横跨大道,语录牌两边林立,红“宝书”高高举过头顶,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一路颂歌,一路狂舞,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到达会场。手舞足蹈,加上长时间的奔波,我们年轻代表都感到疲劳,上了年纪的人早已招架不住,到了住地就倒在床上,累得连饭也不想去吃。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来到房间,问道:“请问哪位是朱劳模同志?”靠在床上正在休息的朱某某答道:“我就是。”说着站起身来。
“早就听说您是全国劳模、植棉能手。”
“感谢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
“老人家累不累呀?”
“不累,一点儿也不累。”
“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过您?”
“是呀,接见我三次。”
“啊!您真是太幸福啦!”
“一次在大会堂,两次在中南海。”
“请问您老多大岁数?”
“七十二啦。”
“真是人老心红。也会跳‘忠字舞’?”
“会,不信我给你来一段。”老人家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当着记者的面手舞足蹈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也许是太累了,或许过于激动,他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引得在场代表抿嘴偷笑。他拍拍屁股站起来,冲着大家说道:“我手脚不灵感情真,舞姿不好表忠心。”善于捕捉新闻的记者马上抓住这句话:“老人家说得好啊!”第二天,会刊上就发了头条新闻,标题是:《手脚不灵感情真,舞姿不好表忠心》--一位老代表、老模范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当初,并没有想当什么“标兵”、“代表”,只是一种报恩的思想支配着我、激励着我。公社“党委”、“革委”对我如此照顾,解决了许多我克服不了的困难,离开他们的帮助,我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什么叫“知恩图报”?共产党对我这么好,一定要做点实事,才不会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
于是,我利用自己的舞台经验、文艺特长,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唱革命歌、演“样板戏”、颂“红太阳”。每天早早安置好芸姐母女后,我便带着队伍出发,演遍了整个公社的所有村庄。尽管有时回到家中已是鸡叫头遍,但我克服种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把“宣传队”办得红红火火,在全县汇演中拿了第一名。我多次去蚌埠铁路分局联系,利用铁路抽水站(给水所)的电源,亲自带人拉着板车到县广播站运水泥杆,来回步行一百多公里,在当时农村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办起了全县第一家大队有线“广播站”,及时转播中央电台新闻节目、报纸摘要及文艺节目……说真话,我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受到哪个伟人著作理论的启发,全凭个人感情。但是,待到林彪提倡的学习《毛著》运动一来,整理我的典型事迹时,便人为地把这些生动的事例硬和《毛著》中的某些篇章挂靠在一起,按政治需要,生拉硬扯,掺假兑水,有意拔高,并把我在“毁像事件”中落井下石的表现与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说联系一起。
就这样,我成了对敌斗争的“勇士”,被树为学《毛著》“标兵”;我的“先进事迹”被绘制成图片,到处展览,我在大会、小会以及不同场合介绍学习“心得”。一时间,我红得发紫,紫得发烫。
每当我在热烈的掌声中昂首阔步走上讲台,面对无数双真诚而又崇拜的眼神念发言稿时,虽然总是慷慨激昂,但也不免脸红心跳,觉着自己在欺骗善良的听众。
我的发言稿是由县“政工组”整理的,到了滁县地区再一次修改、拔高,出席省“积代会”时,原来的稿子已被改的面目全非了。参加会议的各地、市代表团都配备了一支“高水平”的“写作班子”,名曰:后勤组。我只能按照经过“加工”的稿子“海吹”,从县里“吹”到地区,从地区“吹”到省里。
后来报告作多了,掌声听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越说胆子越大,越讲越会讲,临场发挥,口若悬河,脸也不红了,心也不跳了。林彪鼓吹: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而我是:死学,活说,在“吹”字上大显本领。我不但自己误入歧途,还误导了他人,由最初的被动变为主动,由开始的想出风头变为后来的追逐名利。这实在是龌龊的表演。
可怕的崇拜,是把偶像当做万能的神;我崇拜“神”的同时,也被当着小偶像被别人崇拜。这不仅是我的自画像,也是那一代狂热者的群像。我成了一个向左旋转的陀螺,不能自控。
公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大会在响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被《东方红》取代。七十五年前的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把“积代会”开幕式放在这天,意义重大,政治色彩更浓。
晚餐时,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陪同其他首长来到餐厅,与代表们共进晚餐。看样子,事先并未作安排。他走到我们的餐桌前,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他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很随意的坐在朱某某身旁:“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代表团领队狄干事抢着回答:“他是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大家都喊他朱老模。”李德生连忙站起来同他握手:“老人家,我向你学习!”同桌的代表们齐说:“向首长学习!”他边吃边聊:“老人家,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毛著》的呀?”朱老汉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狄干事反应快:“几年前他就开始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地区的老典型喽!”李德生同志听了高兴地说:“有了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掌声再一次响起。
他看见中间那盘菜没人动筷子,便介绍说:“这是‘鱼肚’,是一道名菜,你们怎么不吃呀?”接着他又笑着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可不敢怠慢哟!”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我只知道“鱼肚”是中国四大名菜之一,从未见过,还以为是白水煮肉皮哩。经他这一指点,一盘“鱼肚”顷刻而光。散席离开餐厅时,我发现多数餐桌上那盘“鱼肚”没人动,不禁暗自好笑,我们都是一帮“冤大头”!
当晚,突然接到通知:全体代表不准休息,列队迎接毛主席赠送的一件“宝物”。凛冽的寒风中,代表们等啊,盼呀,等到了深夜十二点,还没有消息。有些体弱年老的代表,冻得流鼻涕。人们站在水泥地上双脚不停的跳动,取暖抗寒。为了向“神”献忠心,没有人愿意走开。一种虔诚、敬“神”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每一个人。
凌晨一点,鞭炮声大作,在《东方红》乐曲声中,迎来了“宝物”。
一队军人前面开道,在首长们簇拥下,一位战士双手捧着个透明的玻璃匣子,上面盖了一块红绸布。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
代表们排着长队,按顺序进入会议大厅,瞻仰“宝物”。讲解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毛主席关心“三线”建设,赠给工人们一批冻肉,以示慰劳。他们没舍得吃,把它供奉起来,此消息经媒体一宣扬,各省都去请“宝”。待到安徽去“请”时,早已分光,于是就给了复制品--一块冻猪肉。
这种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儿,也只有在造“神”的年代才会出现!
大会开了二十天,每天上午是代表发言,下午分组讨论。公正地说,介绍先进典型经验的代表中,大多数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干出成绩。有的原来就是全省、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还有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英雄”。事迹真实感人,可是他们像我一样,发言时硬和学《毛著》挂钩,听起来感觉虚假生硬,具有斧凿的痕迹,使人大倒胃口。
“请宝”闹剧虽然荒唐,但是比这更荒唐的事儿还在后面。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位一百一十二岁(年龄上可能有水分)的老太太,她已无法行动。坐在轮椅上,由两位服务员推上讲台。会议主持人介绍说:“旧社会,她讨了一百多年的饭,是毛主席拯救了她。如今国家把她养起来,每天让别人教她学《毛著》。她心存感激,有许多话要说,因口齿不清,我们就请她说两句,大家鼓掌欢迎。”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服务员将话筒拿到老太太嘴边,她有气无力地喊道:“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接着李德生十分幽默地插话道:“学习毛著也能长寿哇!”
作为高寿,她能活到一百多岁,的确是件奇事,宣扬一下也不为过。作为学习《毛著》,实在有点牵强,怪诞不经。她出“风头”后,退出会场。哪里知道,正是因为她的一句口号,使另一位无辜者犯下弥天大罪!
大会闭幕时决定:各代表团要成立巡回报告团,宣讲大会精神,介绍典型事例,要把学习毛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宣讲材料内容由大会统一起草印制,报告时只需照本宣读。(本段拟去掉,用一句话把上下文连接起来就足够了)我因病妻卧床,孩子小需要照顾,没有参加巡回报告团,匆忙赶回家中。
分别不到一个月,芸姐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她头上磕了几个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留下许多疤痕,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开会时那些激昂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眼前景象让我心碎。
我急忙操持家务,忙里忙外,买煤磨面,手脚不停地干起活来。
第三天中午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安徽八一拖拉机厂做报告,宣讲“积代会”大会精神。我问来人:“你们厂不是有一位代表吗?为什么还要我去?”来人笑笑说:“别提了……”
朱师傅是位老实巴交的工人,文化不高,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省城开会归来时,几千名工人列队欢迎,敲锣打鼓放鞭炮,给他披红戴花,在众人簇拥下,登上讲台。
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无论是福是祸,大多是人为所致。一个机遇能得福,一时疏忽可遭灾。这就叫:“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古语说“因祸得福”,可有人偏偏是“因福得祸”。朱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阵阵。他照本宣读十分流畅,当他传达到132岁老太太登台发言时,不知是心情激动,还是思想紧张,一时口误,把老太太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来个颠倒。会场顿时大乱,引起了不小的躁动。几个“政治觉悟高”的人迅速冲上讲台,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朱某!”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全厂数千工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朱师傅吓的面如土色,当时就跪在毛主席像下请罪……下午两点钟,我登上讲台传达大会精神。本来照本宣读是件很容易的事,可当我念到老太太讲话时,心里紧张,突然打了个停顿,台下一下子静得鸦雀无声,气氛严肃极了。待我小心翼翼地说罢“打倒……,保卫……”,台下的工人也都松了一口气,继而哄堂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们肯定也为我捏把汗。事隔多年,再见到那些工人师傅,他们还说:“那天你在台上做报告,我们在下面的人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好在厂“革委会”领导多是熟人,在我的要求下,他们网开一面,带着我走进临时“禁闭室”。朱师傅双膝跪在水泥地上,面对着毛泽东画像请罪,他的妻子也陪他跪在一旁。(据说她是自愿来陪跪的,目的是减轻丈夫的罪过)他看到我来,两行委屈的泪水滚滚而下。我知道,他是一时“口误”,根本就不存在丝毫的“反革命”动机。厂里的人也清楚这一点,也都很同情他,但谁又敢站出来说他是口误?一下子由“大红人”变成了“反革命”。我拍了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悄悄地退了出来。
芸姐的病,日益加重,已到了离不开人照料的地步。开会期间,公社做工作,让生产队派一名社员到我家当临时保姆。来的是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名叫芮秋儿。
不久,我又到省里参加“贫代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接着又出席省第二届“积代会”。从那以后,只要我有事出门,都由她来照顾芸姐。开始是由生产队指派(生产队为她记工分),后来是她主动上门帮忙。
时间一久,问题就来了,她和芸姐越来越默契,有事没事常在一起低声叽咕,似乎有事在背着我。我无暇顾及眼前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可是这一切将注定我的命运再一次大起大落。
我如痴如醉,无力自拔,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一股热血冲上头顶,脑子一片空白,心脏急剧跳动,两腿一软无力倒下,她一口气吹灭了煤油灯……三十六白雪染尘芮秋儿生在秋天,家里人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图吉利就顺口起了个乳名叫“秋儿”。
秋儿,虽然没有城里女孩那白皙的皮肤、娇嫩的脸蛋、秀美的身材以及文化素养,但她却有农村姑娘的朝气、野气,而且淳朴善良,乐于助人。
她上有一位姐姐,下有一个弟弟;由于家庭贫困,家里又重男轻女,所以她从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她整天和姐姐一道打猪草、挖野菜、养鸡、喂鸭,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
秋儿的父亲是个秉性老实、胆小怕事、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也是附近出了名的“妻管严”,是个活得可怜而又窝囊的庄稼汉;而她的母亲是个生性多疑、无事生非、蛮不讲理的母老虎,也是远近闻名的“惹不起”,常常闹得家庭不和,邻里不安。她对待儿女想打就打,对待丈夫说骂就骂;村里人都怕她,见了她都躲着走。有时为了一件小事,她能把丈夫骂得狗血喷头。更为可笑的是,只要看见丈夫同哪位女子在一起,或是说上两句话,她顿时醋意大发,不分长辈、晚辈、平辈,不论老妇、少妇、姑娘,也不管你是亲戚、同宗还是同姓,开口就骂。而且骂起人来无休无止,什么样的脏话、坏话都能说出口;如果有谁敢反驳她,那你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她不管不顾,拎起一口破铁锅,提着一把切菜刀,坐在你家门前,一边敲打一边破口大骂。尤其是她那富有节奏的敲打和夹带着长长的甩腔且有韵味的叫骂声,似哭非哭,似唱非唱,听了让人气得要死,恨的要命,而又哭笑不得,奈何不得。有人若想拉她离开,她就势倒在地上,来个“乌龟大憋气”,口吐白沫,“晕死”过去。村里几百户人家上千口人,没有不怕她的,背地里给她送个外号叫“锅大娘”。
秋儿生性倔强,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觉得摊上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妈,在乡邻面前很难抬头做人。对于母亲的泼妇行为,她尤为反感,母女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于是经常顶撞吵架,闹得很僵。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长大,秋儿从小就逆反心理极强,对母亲从不屈服,闹翻了她能躲到亲戚家几天不归。对她来说,这个家缺少温暖和温情,感到的只有压抑和无奈。她厌恶这个家,想离开这个家,恨不能早点离开,走得愈远愈好。
我们两家为近邻,加之秋儿经常来帮忙,芸姐与她相处得十分要好,两人也很投缘,无话不谈。秋儿受了委屈就来找芸姐倾诉,女人间的事叙述起来总是没个完,有时讲到深夜,她就在我家留宿。
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九年初,我经常到省、地、县去参加各种会议,家务、病人、孩子就靠她来照顾,因此我们全家人对她十分感激。说实话,当初如果没有她的热情帮助、细心照料,操持家务、分忧解难,我真是寸步难行,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多耀眼的“光环”和“桂冠”。
一来二往,日子长了,她和我彼此都产生了好感,可当时谁也没往深处想。
荒诞岁月自多荒诞事,“文革”中荒诞事更是层出不穷。
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有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婆--顾阿桃。她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五十五岁的生产队社员,就是有人为她造假,被树为学习《毛著》标兵,当上了省革委会常委,出席中共“九大”并坐在主席台上。她九次晋京,六次见到毛主席,还兼任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李素文,一位卖菜大嫂,也是因为政治需要,她的先进事迹挂上学《毛著》的列车,成为沈阳市的领导,继而跃为国家领导人,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许多,许多……这一切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我觉得自己并不比她们差,我既有“文化”又有“口才”,既有“贡献”也有“成绩”,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心里感到极不平衡。再看看同我一起参加省“积代会”的其他代表,许多人都突击入党,火箭似的提了干,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名当了领导。随着一顶顶桂冠和各种荣誉的接踵而至,我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大,日益膨胀起来。
我是省两届“积代会”代表、地区“典型”、县里“标兵”,也曾引起过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多次来人考察,准备提拔我。公社领导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的家庭情况。上面领导不大相信,认为地方上有本位主义,想留住人才不放,便要实地看看。当他们亲眼见到芸姐病歪歪的样子,家中实在困难,都无奈而又惋惜地摇摇头走了。望着他们的离去背影,我伤心地流下了失落的眼泪。
芸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觉得,是自己的病拖累了丈夫,影响了丈夫的“锦绣前程”。于是,一个荒谬而怪诞的想法在她心中慢慢酝酿着,想为我选个能替代她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的女人,好让我甩开膀子去拼搏,干出点名堂来。
一天,我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很晚了,可秋儿还在我家里。芸姐轻声对我说:“坐下,跟你说件事。”我顺势坐在床边。
“什么事?说吧!”
“你看我,死不掉活受罪,害得你陪着我受苦。”
“说这些干什么?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
“其实你是心中有苦说不出。”
“快别说这些,等几年孩子大了,日子会好的。”
“我想……”
“想什么?说吧。”
“我想同你离婚。”
“你在瞎说什么?”对她突然冒出的这句话,我深感吃惊。
“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
“说吧。”
“我是这样想的:我呢离婚不离家,等我俩脱离婚姻关系后,你可以再娶一个女人,帮着操持家务,带好孩子,我也有了依靠,这样才能减轻你的负担,无忧无虑地去干好你的‘革命’工作。说不定日后你也能入党,当上个干部,我们全家也就有希望了。”我听后笑着对芸姐说:“你想考验我,还是开玩笑?”说罢,起身欲走。芸姐急忙拦住我说:“别走,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耐着性子对她说:“怎么可以去干那种荒唐事呢?”芸姐说:“你也尽到责任了,我能住进上海大医院,治疗了两年多,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你别想得太多,日子再苦,我们不也是挺过来了吗?”
“还长着呢,真不忍心再拖累这个家,毁了你一生。”
“我当初选择了你,就应当分担这一份痛苦。”
“我别无牵挂,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九泉之下我也能闭上眼了。”她说得那样真切、那样动情,让我意识到她说的都是心里话。有她这份情,我应该知足了。沉思良久,我然后说道:“芸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总得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还有什么好想的,离婚后还不是在一起过日子吗?”
“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谁愿意来承担这个破碎的家?”
“有人愿意,所有条件她都答应了。”
“可能这人神经出了毛病。”
“瞎说!人是我挑选好的,条件是经过协商的。”
“芸姐,别演戏了。”
“我讲的都是真话。”
“真有这样的人?”
“有。”
“谁?”
“秋儿”。说着,她向外屋指了一下。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被弄得措手不及。我心想,怪不得她们俩老是背着我叽叽咕咕的,原来是为这事。我再一次沉默起来,许久没有说话,因为良知告诉我,不能背叛芸姐。她虽有病缠身,但仍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我们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她今晚来,就是等你回话。”
“别忙,这么大的事,还是让我好好想想。”
说真话,长期陪伴一个久病不愈的妻子,抚养两个幼小的女儿,若说没有一点抱怨那是假话;尤其是失去一次次的机遇,错过许多走向仕途的捷径,我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要不是家庭的拖累,我说不定早就被提升到县里、地区,也有可能到省里了。正是她的病“耽误”了我的前程,如今,芸姐主动向我提出离婚不离家的想法,我不免有点心动。要是真的能同秋儿结合,她又愿承担一切家务,岂不是件好事。我可以把芸姐、孩子托付给她,然后努力工作,一定会受到重用和提拔的。
“做官”的美梦冲昏了我的头脑,我顿觉前途一片光明,浑身上下了轻松许多。什么“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什么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全都被抛之脑后。一个人一旦鬼迷心窍,什么伦理道德、传统美德,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来到外屋。这里没有床,只有一张草垫地铺。秋儿坐在被窝里,身子半靠在墙上,她在等我说话。不知道怎么了,心里感觉怪怪的,秋儿那张原本熟悉的脸,为何在今天晚上变得如此陌生?我不想马上表态,这事需要冷静思考后方可做出决定。我低头走出门外,一阵夹带雪花的寒风扑面吹来,头脑清醒了许多。秋儿她为什么会看上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怎能将自己的终身大事托在一个有妇之夫的人身上?要知道,在农村未婚姑娘去做人家的“填房”是需要勇气的。如果做了,不仅要面对家庭及社会的压力,还要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冷嘲热讽。其中原委令人费解。
她是被爱情所惑?还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在沉思,冥想,分析,判断。与此同时,许多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我脑海中闪动,呈现在我的眼前……曾记得,当初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秋儿就第一个报名参加。她爱唱,而且嗓子也不错,谁知“锅大娘”坚决反对,说什么青年男女搅和在一起不会干出好事来,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是件丢人事情……秋儿就是不听,她说在家受压抑,心情烦闷且无聊,如果到宣传队唱唱跳跳,不仅能记工分还可以放松情绪,躲在宣传队里不愿回家。
一个反对,一个坚持,母女俩互不相让。“锅大娘”又哭又闹晕倒在地,使出“乌龟大憋气”的绝招,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死”了过去……这一招特灵,吓得大伙儿一起劝说秋儿回家。
第二天,我去蚌埠购买乐器,来到炉桥火车站正准备买票,突然发现秋儿站在眼前。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家,我呆够了,想到蚌埠舅舅家住些日子,解解闷。”
“你妈知道吗?”
“我谁也没告诉。”
“还是回去吧,不然你妈会着急的。”
“管她呢。”说罢,她拉着我登上将要启动的列车:“蚌埠我常去,路也熟,买东西也好帮你带路。”
珠城蚌埠,是京沪、陇海铁路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贯穿南北,开往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列车川流不息。上午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二马路商业街。这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宽畅的街道人流如潮。买好东西后,我们坐在天桥上小憩,望着下面的车流;我侧过脸看了一下,秋儿正兴高采烈地数着过往的汽车,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好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上湛蓝的天空。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今天出门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又粗又黑的短辫子上扎了两个蝴蝶结儿,绿色的军帽下一双眼睛流溢着光彩,胖呼呼的圆脸总是带着微笑;她身穿一套绿军装,别人见了都把她当成学校里的红卫兵,她也以此为骄傲。同许多女孩一样,她也热爱解放军,崇拜红卫兵,将绿军装视为最时髦的服装。她平时最喜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毛主席诗词《为女民兵题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奇怪的是,大半天过去了,她却只字未提去舅舅家的事。我提醒她:“你快去舅舅家吧!我还要赶回去呢!”她说:“我又不想去舅舅家了,还是跟你一起回去吧。”
“那好,现在我们就去买车票。”
“晚上七点才有车呢,蚌埠我常来,错不了。”说完,秋儿狡黠地一笑。
既是晚上七点的火车,天色尚早,索性逛逛商场。在拥挤的人丛中,她的手时而同我的手相碰、相挨,时而情不自禁地握住我的手,紧紧倚着我,怕把我丢了似的。当我有所察觉,回眸望她时,她又轻轻地松开了。那张绯红的脸蛋儿,紧紧地挨着我的肩头,我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暖流。
晚上六点,我们就到了车站。一打听,去炉桥的火车早已开出,要等到明天上午才有车。不知是记错了,还是她故意的,反正今晚是走不掉了。我有一种潜在的愠怒,但又不便说出口,我们呆呆地站在火车站门前,望着暮色中那如繁星闪烁的高楼大厦,怅然若失地感到,我和她像被抛出人类世界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小巷中一家普通的小旅社。一见面,服务员要我们出示结婚证。我没有好气地说:“我们不是夫妻,分开睡。”服务员说:“那也得出示介绍信或者证明。”我本来打算当天赶回去,压根没想到带证明信。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小旅社。走到巷口,面对着不夜的珠城,心头倍感凄凉,这么大的城市,竟无我俩的栖身之地。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再次走进候车室。候车室里等车的人并不多,我们挑选了一排椅子坐下。上半夜,天气不算太冷,秋儿靠在我身上轻轻睡去。我静静地聆听着她那细细的均匀的呼吸声,看着她那微闭的双目,一股爱怜之情油然而生。自从她来到我们家帮助照看芸姐和孩子,我就从她的行动中感受到了她的淳朴和善良,我打心眼里喜欢她,也为她常遭母亲的无端责骂而难过。她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疼。
到了下半夜,春寒袭人。也许是冷的缘故,她双手紧紧抱着胳膊,头靠在我的胸前,我本想解开上衣把她裹住,以防受寒,可我没有这样做。那年头男女有别,授授不亲,两个年轻人稍有亲近,就会引来无数惊诧的目光。
窗外的世界仍然喧嚣不已,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好像一只只眼睛,在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我俩紧挨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
说实话,在此之前所有的日子里,除了芸姐,我还没有同哪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呆过一刻,更别说一整夜了。可是今天,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一个初识人间悲苦、渴望新生活的少女就蜷缩在我的身旁。两个年轻的心似乎贴得很近,我嘴里感到很焦渴,胸口也鼓涨得如海潮一般,起伏澎湃。
一夜相依很快过去了,可是两性之间触及心灵的暖流却久久地留在我的心头,令我神往、心醉,想入非非……而今她就在眼前,我该如何面对?
对于秋儿,我无法狠下心来舍她而去,因为她已悄悄地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为了确认她对我的态度,我还是决定问一下,于是转身回到屋里。
“这是终身大事,非同儿戏,你要仔细想想。”
“我想好了。既然做出决定,就绝不会后悔。”
“一个病人,两个孩子,你不怕麻烦?”
“不怕。”
“想过没有,你妈反对怎么办?”
“我的事自己做主,谁反对我也不怕!”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我觉得你很有本事,不会在农村呆一辈子,相信你能带我走出这个穷地方,离开我那个令人心烦的家。”
“假如我走不掉呢?”
“不会的,有我照顾这个家,你肯定会当上干部。”
“那可不一定。”
“上面几次来人我都在场,看得出来他们很想提拔你。”
“万一我当不成干部呢?”
“我就跟你一起受苦,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我这边的事好处理,就担心你们家里人反对。”
“不要紧,我的事谁也干涉不了。”
“你妈要是闹起来--”
“我会对付她的。”
“可是,万一--”
“我的话都说绝了,你还不相信我?”
“你总得让我考虑几天吧!”
“你要是还信不过我……”说着,她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盯着我,顿感有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她抓住我的手说:“我们今晚就--”没等她把话说完,我赶忙站了起来。我那时真的没有什么邪念和欲望,血管里流淌的绝对是正统的道德观念,尽管与芸姐多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但从未想过背叛她,而去和另外的一个女人相好。我心想:她毕竟是个未婚的大姑娘,万一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会身败名裂!我想离开,可是无力抬步。许多缠绵的往事涌上心头,尤其是蚌埠火车站候车室相依相偎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抹不去,甩不掉!我仿佛跌入了一个泥潭,无力自拔。漆黑的泥潭包围着我,压迫着我,使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猛然间,一股热血冲上头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脏跳动加剧,两腿一软,猛然倒下;她顺势吹灭了煤油灯……外面的狂风疯狂地扑打着窗棂。
飞雪飘飘,盖住了村庄,盖满大地,盖着了洁白的世界。
白茫茫的大地,播下了一粒污秽的种子!
男女间的私情,不是想停就能停得了的,犹如干柴遇烈火,一旦点燃起来,就不会自行熄灭,除非等到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