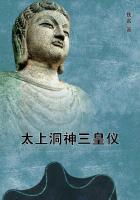“当!当!……”
古寺夜半钟声响起,慧能还没有半点睡意。他两眼死死盯着天花板,尽管那是一页读腻了的书,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
河船汽笛声此起彼伏,与古寺钟声汇成特有的旋律。然而,这些对慧能来讲,一概提不起兴趣。
一轮圆月冷冷地照着大地。慧能感到有些寒意,顺手抓起一条毛毯盖在身上。睡神仍未光顾,他就隔窗望月。记得走出家门时,也是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月亮伴着他,一直伴到天亮,才来到镇上的火车站。然后,他买了票,到了苏州城。再后来死磨硬缠削发做了临时小和尚。整日干打扫寺院的营生,也不知扫落了几钩残月,几多晨星。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一年。想起来有时也觉可笑,不就是为了父母包办的一桩婚姻嘛。爷爷奶奶是包办婚姻,照样生下父亲和两个姑姑;父亲母亲没有爱情,同样有了三男两女。再说,凤月姑娘连见都没见一眼,你敢说不是个漂亮妞。有个漂亮妞陪伴一生,还亏什么。有时扫地扫累了,做佛事做烦了,他就在心里想象着凤月的模样,想着想着,另一个姑娘便把凤月顶替了。她叫文媛,是他高中时的同学。上学时,他就暗恋上了她。两人的眼波你来我往,架起一座爱情之桥。只是不好意思提出,直到毕业分手,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离开了她反而更思念她。他心里说,一辈子非她不娶。介绍人介绍的凤月也是辛庄的,正和文媛一个村。慧能就想,自己当时多傻,为什么不去找文媛打听一下凤月呢?同时也试探一下文媛对自己有没有意思。岂不是一举两得。
命运有时也真能捉弄人。
慧能翻了个身,月亮露出了笑脸,泻下一片温柔的银光。慧能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儿,咕嘟咕嘟地冒着甜泡儿。有一次他正在清扫大雄宝殿时,突然进来一个面熟的女施主,他就偷偷地瞅她,披肩长发,紧身连衣裙。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是文媛。文媛也认出了他,未曾开口却先泪流满面。慧能怕在寺里招惹麻烦,便让她到寺外枫桥边等他。然后,瞅个空子换下袈裟,穿上西装到桥边见面。
文媛一下扑到他怀里:“你怎么忍心抛下我,当了和尚”
慧能答非所问:“你现在过得好吗,”
文媛点头:“还算可以。自从你失踪后,我就到了深圳,给人家当保姆,混来混去,我就感到没知识不行。所以,我挣了些钱后,便考上了大学。就在这个城市。”
“好。”慧能说。然后问,“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文媛说。
“和你一个村的,叫凤月。”慧能说。
文媛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凤月就是我,我的小名叫凤月。”
“我的天!”慧能一把抱住她,“早知你是凤月,我还出家干什么?不过,我已和寺里订了两年合同,期满后,陪你好吗?”
文媛笑笑。两张嘴叠在了一起。
以后,慧能就在希望中打发着日子。
慧能又翻了个身。
月亮已经偏西,月光轻轻地射进窗来。慧能就想,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亮了。天一亮,他就得起床打扫寺院,在寺院开门时,他还要在钟楼前卖票。自从经济大潮冲击神州大地之后,寺院也有了不小的变化,门票由五元长二十元。上钟楼原先是不收费的,现在却一下子每人收五元。慧能、慧智就负责这项工作。开始,慧能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有一次慧智闹病,由他一人值班,有的人耍小心眼,并不要票,悄悄塞给他两元或三元,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上楼了。这一天寺院关门时,他口袋里就有了三张属于自己的老头票。又有一次,他还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和日币。他知道文媛经济来源不足,便接济了她。乐得她用劲在他脸上吻了几口。
明天,慧智告假回家探父母,又只有他一人值班了。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该早睡一会儿。越是这样想越睡不着。他就在心里数着:“一、二……”
此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枫桥上的圆月越变越大,光芒却越来越淡。
慧能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