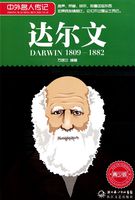杭州,这座因城西的西湖风景绮丽,而成为著名的游览城市,年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但是,自从这里成立了日寇的侵占区和南京政府的管辖区以来,除了日本人像游览他们的京都风光那样,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游人几乎绝迹。
现在,已是万物凋零的冬季,更是寂寞冷落。因为从明天起将实行新旧货币兑换,人们将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杭州上空又笼罩着一片凄凉和悲伤气氛。严寒的自然气候,又面临严峻的政治气候,人们愁肠百结,无怪乎有人书写《苦寒行》里的“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两句古诗张贴在大门口,用以宣泄心中的积郁和悲酸!
“在门上张贴这两句古诗的是什么人?”傅式说听了省财政厅厅长兼货币兑换督查办公室主任张德钦的汇报,先是一阵慌乱,然后用探究的目光,对张德钦、中央储备银行浙江省分行代理行长苏英之、分行储蓄处处长李鸿志和沈尔乔、李仲生等人扫了一眼,最后把眼光停留在来杭州督促货币兑换的周佛海脸上。又情不自禁地瞟了姜晓梅一眼。她是湖南华容人,四天前被抓到南京之后,因为她生得千娇百媚,是丁默邨打埋伏留下的一百二十个女人中的一个。前天她被周佛海看中,成了他名义上的生活秘书,实际上的姨太太。
傅式说从周佛海那冷如岩石的面孔上获得支持,又厉声问道:“把这两句古诗张贴在门上的是什么人?张先生知道吗?”
“报告傅主席,知道。”张德钦两只眼睛像粘了糨糊睁不开似的一眨一眨,“此人名叫刘立人,是永昌绸布庄的老板和大财主。他对新币中储券以五的比率兑换旧法币很不满。昨天下午,他在杭州商会召开的《禁止旧币使用令》的讨论会上,公开说这是政府对老百姓的剥削!”
他毕业于杭州财政专科学校,在省财政厅当了十多年会计才捞到一个科长,两年前他四十岁时,在《中华日报》上发表题为《试论日军占领区之经济振兴》的文章,受到周佛海的垂青,让他当了财政厅长。他对当厅长一个月之后娶上的姨太太王秀秀说:“我的确是‘四十而不惑’哩!”
《禁止旧币使用令》是汪精卫以行政院的名义颁布的,《禁令》决定从十一月八日凌晨一点起,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南京、上海等省市停止使用蒋介石政府发行的法币。与《禁令》同时出笼的《新旧货币兑换办法》规定,一元法币只能兑换五角中储券。照此办理,除了一无所有的要饭叫花子,每个人都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失,越是富有越倒霉,自然会普遍地引起人们的严重不满。
“不管他是什么人,谁反对货币兑换就是反对南京政府!”傅式说的两撇眉毛不耐烦地锁在一起,怒气明显地写在脸上,“等会,请李先生派人把刘立人带到你们特区去,由你们审讯之后再做处理!”他见李仲生连连点头,把脸转向张德钦,“请张先生继续汇报有关动态。”
“动态之二,是李先生手下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副明目张胆反对货币兑换的对联。”张德钦支支吾吾,“内容够反动的,我真说不出口。”
“说吧!无非是臭骂我们一通。”周佛海脸上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心里却怦怦地急跳着,“李先生你说,是怎么回事?”
“报告周副院长和傅主席!”李仲生吞吞吐吐,“对联和横批张贴在吴山南麓的一座小土地庙上,我们的特工人员发现时,贴对联的糨糊未干,可能是今天天亮前贴的。对联和横批给张厅长看过,我把它带来了,请周副院长和傅主席过目。”他从皮料提包里拿出对联和横批,双手捧着递给周佛海。
对联和横批是用黄色蜡光纸写的,字写得东倒西歪,像小学生的笔迹。那对联写的是:
发行伪钞,五角抵一元,卖国贼获暴利;
废除法币,一元值五角,老百姓吃大亏。
横批是:
经济原理“简直是反动透顶!”周佛海拍案而起,暴跳如雷,声音冷冰冰的,像一颗颗弹跳在水泥地面上的圆石子,“请傅主席立即派保安部队和特工人员进行侦破,查出来了先杀他一个压压邪气!”
“遵嘱照办!”傅式说满脸严肃,“请沈先生和李先生退席,马上组织人进行侦破。”
沈尔乔和李仲生起身欲走时,周佛海摇摇手说:“慢!我还有话说。这对联,论对仗,声韵,平仄,都经不起推敲,但撰对联的人肚子里还有点文墨,还会使用‘经济原理’这个词。这就是破案线索。”他手指摆在桌子上的对联和横批,“这黄色蜡光纸,这笔迹,同样是破案线索,你们把它带去。限两天之内破案。你们先预支一万元中储券做活动经费,实报实销。谁能对破案提供可靠线索,奖赏中储券五千元。任务完成了,我重金奖赏二位,每人奖赏二万元中储券!”他面孔一板,“若完不成任务,莫怪我无情!”等沈尔乔将对联和横批塞进皮料提包,周佛海又吩咐说:“让一批保安部队的弟兄换上便衣,打扮成上街买东西的老百姓到市场上去,听听老百姓对货币兑换的反应,发现不满分子盯梢跟踪上去,等他回到家里再抓人。”
“如果商店老板反对货币兑换,是不是马上抓人?”沈尔乔问。
“也不宜过急。”周佛海说,“等天黑以后再动手。”
沈尔乔和李仲生走后,周佛海仿佛听到一阵阵反对货币兑换的口号声,从远至近,像海啸雷鸣似的传来。他的心因此紧张而急剧地膨胀,又急剧地收缩着,仿佛要爆裂,要化掉一样。货币的兑换会引起老百姓的普遍反对,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更有力地对付重庆政府、共产党和一切爱国人士对南京政府的颠覆,他们不得不急剧增加和平军、宪兵、警察和特工人员的编制,这就带来财政赤字的急剧增加。他身为主管财政的行政院副院长,不得不冒风险趁货币兑换的机会,从老百姓身上捞一把。
他终于明白刚才的心情紧张,是因为自己神经过敏而产生的幻觉,也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没有爆裂,没有化掉。周佛海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世界里,但他已经习惯了。
“谩骂,吓不倒我们!”他的两眼像同时按亮的两只手电筒,直射着傅式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在一片谩骂声中进行的,中日和平运动也是在一片谩骂声中开展起来的,政权在我们手里,兵权也在我们手里,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微微一笑,笑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轻松自然,像小河的流水一样随意,“等会我打电话给实行货币兑换的其他省市,告诉他们,老百姓越反对,兑换工作越要抓紧进行。看来,原定一个星期完成兑换任务的时间太长,必须提前四天在三天之内完成,免得夜长梦多!今天是十一月七日,也就是从明天凌晨一点起,到十日晚上十二点止完成兑换任务,逾期不兑换的旧币一律作废!此事,请傅先生打电话通知杭州市和所属各个县。”
杭州城里的居民和郊区的老百姓,看到张贴在墙上的《禁止旧币使用令》和《新旧货币兑换办法》,知道从明天起一元法币只抵中储券五角,仿佛被挖掉一块心头肉似的痛楚,慌忙把自己积攒的钱塞进口袋,来到杭州街上购买东西。可是,人们从东街走到西街,又从南街走到北街,每家店铺大门紧闭,都在门上挂着“今日停止营业”的牌子,连小摊贩也见不到一个人。
残酷的现实,使大家明白了一切。许多人在街上穿来穿去,到了上午十点左右,见商店开门营业无希望了,才唉声叹气,拖着发软的双腿踏上各自回归的道路。性情暴躁的人难免发几句牢骚。于是,这些人的身后就有了个跟踪者。
但是,家里有人病了,等待着买药回去治病,总不能空着手回去。三十多个买药的人,从这家药店走到那家药店,隔着紧闭的大门说了许多求情的话,都没能感动药店老板。大概是想到“慈爱国药局”这个招牌的含义,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这家药局门口,希望老板发慈爱之心。
药局的门被叫开了,但老板却说:“本店的宗旨是救死扶伤,药可以卖,不过法币一元只能算五角。诸位都是明白人,道理用不着我说。”
治病要紧,有几个人忍痛把药买走了。可是,还有二十多个人还在向老板苦苦哀求。他们都是按平日的法币价值带的钱,如果一元钱只算五角,只能买到所需药品的一半;回去再拿钱往返二三十里,势必耽误治病,这就不得不低三下四地恳求老板积善积德。与买药者混进来的十多个保安部队便衣士兵,也都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使老板产生错觉,他默默地数了数,有四十三人。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有这种要求,我可以讲慈爱,但有这么多的朋友有困难,实在是爱莫能助!”老板双手抱拳,“敬请诸位海涵!”
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听老板这么一说,有几个在杭州城里有亲戚朋友的人借钱去了。在城里求借无门的人,骂着:“政府这样做,丧尽天良!”“制定货币兑换办法的人不得好死,绝子灭孙!”一类的话,垂头丧气地离开药店。
善良的人们,自然没有想到这样咒骂的后果。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第一件大事。绝大多数人家积攒的钱,主要是用来购买大米。因此,城中的十多家米店门口,仍然挤满了希望买到大米的顾客。
恒大米行是杭州城最大的米店之一,米店门口聚集着四百多个买米的男男女女。已是上午十点,好话讲尽了,米店仍然不开门,有些人就挥着拳头,使劲在门上捶起来,杂乱而反复地喊着一句话:“开门,开门!我们要买米,我们要买米!”
装着买米的十多个便衣士兵,为了激发人们发泄对货币兑换的不满,也跟着别人捶门,有的边捶边喊:“今天为什么不卖米?请老板出来说明原因!否则,我们把门撞开,把你店里的米背走!”
“是呀!你再不开门,我们就把门撞开!”几百个买米的人呼喊起来。老板宋仁智急了,登上三楼,打开一片窗户,探出半个脑袋,对大家说:“今天不卖米的原因,诸位一定很清楚。如果我今天把米卖出来,一斗米的价值就变成五升,我亏不起啊!”“今晚十二点以前,法币一元还是一元,你没有亏本!”一个便衣士兵说,“不行,不行,你今天非卖米不可!”又一个便衣士兵怂恿着说:“我一家八口等着米下锅,你有米不卖,让我一家人饿肚子,居心何忍!”
“是呀,老板有米不卖,让我们饿肚子,没有良心!”众人很愤怒。
“这不能责怪我没良心!要责怪,你们去责怪政府吧!”宋仁智把窗户关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宋老板也的确亏不起!”一个身穿棉青布面中山服的中年人愤愤地说,“如果杭州还是老蒋的天下,何至如此!”
中年人的话,引起众人的一片哗然,大家吵吵嚷嚷:“一元值五角,伤天害理!”“不怨天,不怨地,只怨政府不体贴老百姓的疾苦!”“坑害老百姓,天理难容!”“干这种缺德事,天诛地灭!”
大家骂骂咧咧走了。几百人咒骂,十多个便衣士兵一时很难瞄准一个目标,只恨自己没能多生几双眼睛。最后,每人只能盯梢一个咒骂时嗓门最高,或反复咒骂一句话的人跟踪上去。
在玉珠米行门口,同样聚集着四百多个买米的人。这时,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等得厌烦了,无可奈何地提着只布袋回家去。她刚走了几步,迎面来了十多个人,虽然都穿着便衣,还是一眼认出了走在前面的那人是她的姐夫,在保安部队任营长的甘昆华。甘昆华也认出了姨妹崔美兰,走过来,关切地问道:“买米吗?美兰。”
“是的,姐夫!”崔美兰忧郁地说,“我帮鞋店纳鞋底,得到七十五元法币,到明天就会变成三十七元五角,想买米,米店老板怕亏本不肯卖。怎么办?姐夫!”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撩起衣襟擦起眼泪来。稍停,她手往等待买米的人群一指,“亲家爷也买米来了。”
她说的“亲家爷”,是甘昆华的父亲甘德祥。
“噢!我父亲也买米来了。”甘昆华悄声说,“你去把他老人家叫来。”
甘德祥挑着一担箩筐走过来,见了儿子,伤心地说:“我背向太阳面朝土,辛辛苦苦种菜,好容易得到一百二十元血汗钱,可是米老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甘昆华陷于沉思。眼见父亲和姨妹在经济上受损失,不管实在不忍心。管吗?若只有父亲和姨妹两个人买米,他可以利用营长的职权,把玉珠米行的大门叫开,让老板佘德隆把米卖给他的两个亲人,因为他与佘老板是熟人,他会买这个账的。讨厌的是买米的人这么多!甘昆华感到很为难。
父亲越哭越伤心,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两只粗糙如树皮的手捧着脸,哭得像个孩子。
甘昆华心如刀割。他不知所措地不时搓搓手,又不时地在原地移着沉重的脚步。
“营长!”连长龙仁舸说,“在法币没有到废除期限之前,哪怕只剩下一分钟,一元还是一元,它仍然具有法律保护价值。我认为,佘老板不卖米是不应该的。”
“走!跟我买米去。”甘昆华感到龙仁舸的话有道理,也给他壮了胆。甘德祥和崔美兰擦擦眼泪,豪迈地挺起腰身跟在甘昆华后面。那些买米的人,一齐伸长脖子望着他们。甘昆华走到米店门口,低声对龙仁舸说:“注意,防止大家跟着我们冲进去,不准开枪,以免暴露我们的身份。”等到龙仁舸带领士兵们围了个半圆圈,把甘德祥父子和崔美兰围在门口,甘昆华大声喊道:“佘老板开门,我是甘昆华,有重要事找你,请开门!”坐在门口的四百多个买米的人看到一线希望,一齐唰地站起来,纷纷把布袋提到手里,把箩筐挑在肩上,都是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