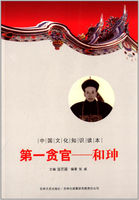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很抱歉,日美会谈上午还结束不了,徐特使阁下。”东山说,“阁下有什么需要我转告丰田先生的吗?”“丰田先生有时间了,请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来。”徐珍心中有股难以释怀的苦闷。在返回下榻处的路上,徐珍见轿车司机不懂汉语,就悄悄对董道宁、影佐说。“要是我能够接受二位的意见,不给济南打电话就好了。”她很懊悔。
“是呀!要是芳子小姐能够在这时候来东京一趟就好了。”董道宁的话里含有责备,但语气十分温和。“贵国有句名言:‘吃一堑长一智。’我们有了这次教训,今后办事想问题会更成熟些。”影佐为了不伤害徐珍的感情,特地在话里用了个“我们”。“是的。”徐珍心急如焚,“那么今后怎么办?影佐先生。”“看来,非主动找近卫首相不可,”影佐沉思着说。“谢谢你,影佐先生,你的意见帮助我增强了信心。”徐珍眼睛一亮,“不管怎样,他现在还是首相。”回到下榻处,徐珍正准备给近卫打电话,一辆轿车驶进来,从车上走下来的竟是芳子及其助手李芳兰和张冰洁。“芳子姐,”徐珍喜出望外地急迎上去,与芳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芳子还是女扮男装,头戴大盖头军官帽,身着军服,佩武装带,脚穿长统黑色皮鞋。“我的好妹妹!”她显得亲热极了。“第三十二师团没有将影佐先生打的电话告诉你?芳子姐!”徐珍又惊又喜。
“告诉我了,翠子妹。”芳子笑着,因为我已经离开了禹城,又想到我们姐妹俩一年多没见面了,很想念你,还是来了。东京也是我的家,有了翠子妹在东京,这个‘家’的概念更深了一层。我真是归心如箭,在济南吃了中饭,顾不得休息就起飞了!她心有疑惑,“你既然派张女士去接我,怎么又临时改变主意不让我来了?”
徐珍见美静子在场,微笑着敷衍说:“想到姐姐重任在肩,担心影响你的工作。”“啊,哦!”芳子不愧为老牌特务,从徐珍的眼神里了解了她内心的诡秘,“原来是这样。”徐珍面向张冰洁和美静子,温和地说:“请二位为芳子司令和李秘书安排住房。”她回头挽着芳子的一只胳膊,“姐,请!先去我的住房里坐一会。”
徐珍来东京的任务和因近卫内阁即将总辞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她请芳子来东京的目的,张冰洁到了禹城就一一告诉了芳子,因此,她来到徐珍的住房,屁股一落座,劈头就说:“上午你要影佐先生打电话到济南,一定是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请直言相告我。”
徐珍将杉山元接见她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满以为一切很顺利,不必麻烦姐姐来东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东条陆军相对我们的支持如此尖酸刻薄。”她又将东条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芳子,接着说,“如果姐姐不来,我们打算去找近卫首相,争取他的支持。现在姐姐来了,一切请姐姐给我做主。”
“应该刻不容缓地找近卫首相,争取今明两天之内解决问题,以免夜长梦多!”芳子当机立断,“在天皇陛下没有正式批准近卫首相的辞呈之前,他仍然拥有首相的权威支持你们的扩军计划!至于是否需要找多田骏表哥,甚至找枢密院平沼议长,等近卫首相接见你们之后再说。”
“感谢谢姐姐的开导!”徐珍感佩地说着,伸手抓起身旁的电话机话筒给近卫打电话。陡然间,一颗心矛盾地怦怦跳动着。他害怕近卫在电话里说出单独接见她的话,又十分渴望这句话能够从电话机里传过来。她害怕,出于她现在身份的某种约束和从良的坚定,她渴望,出于对自己美貌的自豪,并因此能够使她的东京之行能够获得圆满成功。
“是近卫首相吗?阁下好!我是徐珍,是翠子。我是昨天下午来东京的,随来的有董道宁先生,张冰洁女士和影佐祯昭先生。我们来了,阁下还不知道?噢!可能是丰田先生见阁下忙不过来,没有将我们来东京的情况向您报告。”执著的信念和追求支撑着她的精神宫殿,使她的种种顾虑和胆怯一扫而光,对着话筒果断地提出:“首相阁下!我希望您今天晚上八点左右单独接见我。”她获得近卫肯定的回答,舒心地放下了话筒。
“对!翠子妹你应当主动。”芳子会意地微笑着,“一个女人,能够在特殊环境中,以特殊手段获得任何一个男人所无法获得的东西,是人生的骄傲,也是青春的骄傲!”她凄然地叹息一声,“可是,姐姐我老了!”
以色取胜者,色衰而事衰。她今年三十八岁,接近珠黄岁月,深感近年来的特务活动不如过去顺当。两个月前,她受伪满洲国康德皇帝的派遣来东京,想从近卫内阁获得两千万日元的经济援助,但她如同花园里一朵接近凋谢的花朵那样不惹人青睐,尽管她表现得十分主动,但过去与她厮混过的近卫和前外务相松冈洋右、前大藏相河田烈都对她不再感兴趣,结果只得到一千万日元的贷款。
“其实姐姐仍然年轻美貌。”徐珍安慰说,“依妹妹浅见,姐姐穿军装,失去了年轻女性特有的曲线柔和美。因此,建议姐姐还是烫头发,穿旗袍好。”
“我身为满洲国安国军司令长官,烫头发,穿旗袍,不伦不类啊!”芳子持否定态度,“我看透了,也想通了,我不是需要柔美,而是需要军威,这军装我将穿一辈子。”她欢笑着。
世间事物就是这样奇特,凡是竭力争取得来的东西,眼看就要不属于自己所有了,非常难过,可是,一旦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完完全全丧失了,又反而变得轻松起来。
晚饭后,近卫坐在首相办公室,默默地回味二十四小时内思想感情的急剧变化。昨天晚上的这个时候,他正在无限痛苦地考虑他的内阁总辞职,任何年轻美貌的女人也不可能惹动他的情怀,与孤守青灯的老和尚无异。这种痛苦伴随他度过了上午的全体内阁成员会议,又伴随他度过了向裕仁提出的辞呈起草和定稿,直到派人送给裕仁为止。现在,他仿佛从滔滔苦海走向极乐世界,一种与世无争,万事皆休的超脱,使他有闲情逸趣去迷恋女色,急切地等待着徐珍的到来。
徐珍来了。近卫痴情地望着她,一年多不见,她还是那样漂亮,身子变得更加亭亭玉立,长长的腿,细细的腰,高高的胸脯,红润的嘴唇温温柔柔,乌黑的卷发乱中有美,微陷的眼睛黑白分明,浑身洋溢着娴静与成熟。
徐珍望着他,一年多不见,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近切,遥远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不来东京很难想起他,可又近切得像是在昨天,尤其是在东条那里受到意外的冷遇之后,近卫的名字就愈发牵挂着那已遗忘的数次交媾之情,不管这情是勉强还是真情,肉体厮混总是情分。
两人拥抱着,嘴唇吻在一起,此种情和爱是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如此深奥,又如此平淡;如此饥渴,又如此饱和,使得这对老情侣的五脏六腑都要跟着往上翻。
徐珍把身上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又主动帮助近卫脱掉衣服。彼此满足了情欲上的需要,才坐下来谈徐珍访日的要求。
“汪先生计划新建八个陆军师和一个空军旅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来东京的目的无非是需要武器装备的支援,是吗?”近卫的神态是情上加情,热上加热。
“是的,希望你能够像杉山元元帅那样支持我们。”徐珍将杉山元和东条说的话如实告诉近卫。“东条先生是有意从中作梗。”她有点愤愤然。
“我完全同意杉山元先生的意见,支援你们十个陆军师和一个空军大队的武器装备。”近卫马上拍板,“至于东条先生的意见你可以不予理睬,一切由我和杉山元先生做主。”他略一思索,“但是,你们至少得支援我们三千吨铁和八百吨铜,因为这是我们最缺乏的物资。如果你能做主,明天就签订有关协议。要抓紧,越快越好!”徐珍明白近卫“要抓紧”的含义,见他不明说,也就装着不知道他的内阁即将总辞职。忽然,她淫笑一声,柔声问道:“你是怎么搞的,还要这么多的铁和铜?”她与近卫之间不存在特使和首相的尊严,只有情妇与情夫的挑逗,伸出右手食指在他左腮上戳了一下,嫣然笑着说:“你呀!支援我们还不如杉山元先生那样慷慨,真是怪事!无偿支援我们的扩军计划吧,我的首相先生!”
一阵愉快的沉默过去,近卫说:“好吧!无偿支援你们,我的宝贝!”他把她搂在怀里,“你会永远惦记着我吗?”
“会,会,会永远惦记着你,也会永远爱你。”徐珍一阵狂喜,“我爱你一辈子!”第二天上午,由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写好《关于日方无偿支援华方武器装备之决议》,征得裕仁同意,由近卫和杉山元签字生效。
徐珍被近卫留住,又继续在东京待了五天。五天中,丰田几次找徐珍,她都有意回避了。这并不是她事先知道丰田与比利时、土耳其、秘鲁、哥伦比亚四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被美国识破作废,也并没有预料到在十月十八日东条组织新内阁时,裕仁和东条没有让他再当外务相,而是她的访日已圆满成功,没有必要在丰田面前再出卖色相。
十月十五日上午,徐珍一行回南京时,芳子接受徐珍的邀请,同机赴南京访问。十一点二十分,在明孝陵机场,徐珍和芳子等人受到陈璧君、外交部长徐良、军政部长鲍文樾、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外交部次长周隆庠的日本籍姨太太、芳子的同养父养母的妹妹智子,以及日本驻南京政府大使本多熊太郎和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二号人物晴气庆胤等人的欢迎。
当徐珍介绍晴气与芳子见面时,他忧悒地对芳子说:“不幸,土肥原将军夫妇在禹城失踪了!”
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头子,居然与他姨太太一起失踪,刚下飞机的人无不猛然吃惊,惊得心脏差点从腹腔里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