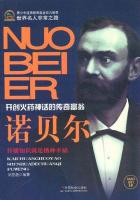赵毓松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五点五十分了。湖北省政府大院内的花园里,不知什么鸟在不住地叫,叫醒了武汉的黎明。
他是五天前的十月二日带着三姨太戴云珍来武汉的,因为何佩瑢为他在大冶修建的公馆才破土动工,征得汪精卫的同意,暂时住在湖北省政府里面,只每天驱车去大冶矿业公司待两个小时。头两天,是安排新上任的中日正副经理埋葬牛场等四人那已发臭的尸体,以后是督促经理们维修被周成哲他们弄成废物的机械设备,争取在两个月内恢复生产。
这样的单调生活,使赵毓松感到乏味;戴云珍更是受不了每天往返近四百华里,把她像铺盖卷一样抛来抛去的汽车颠簸,已经哭过两次了。昨天,她就赌气没有随丈夫去大冶,过了一天独守空房的孤寂生活。
人,一旦娶上年龄与自己悬殊过大,而又美貌非凡的姨太太,就时刻警惕着别人打姨太太的主意,恨不得世界上的男人都死绝。半年前,他赵毓松在武汉间谍训练班见到戴云珍时,不是一见钟情吗?不是从拥抱,接吻,到上床厮混,她都表现得非常驯服和顺从吗?她对他如此,对别人不也是一样?昨天晚上,他总是疑神疑鬼,觉得她那瓷体般的胸腹又被另一个男人爬过。
现在,天大亮了,他翻身坐在床上,望着熟睡未醒的姨太太,见她那嫩白秀美的脸上荡漾着几丝笑意,又被另一个男人在上面吻过的怀疑更强烈了。他怒不可遏,心脏无缘无故急跳起来,血液直往脑袋奔涌。“啪!”他莫名其妙地打了她一记耳光。
脸上的疼痛和清脆的巴掌声,使戴云珍惊醒过来,本能地摸着凸起的五条指印,惊讶地问赵毓松:“你打了我?”
“一只蚁子叮在你脸上,我想把蚊子拍死。”赵毓松若无其事地说。
“是脸,又不是大腿,拍蚊子拍得这么重!”戴云珍反感地说,“拍死的蚊子呢?”她惊疑地在床褥子上寻觅着。
“没拍着,飞了。”赵毓松耸了耸肩膀,下床舒展几下胳膊。
“昨天我没有跟你去大冶,你恨我!”她有高中文化,又受过一年特务训练,还有点分析能力。
“你有权利这样判断。”他望着她那迷人的容貌,后悔刚才那一巴掌打得太重了,俯下身子伸手在五条指印上轻轻抚摩着。“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我可爱的三太太。”他在那五条指印上吻了一下。
“汪委员长不是要你管管武汉的棉纺织业吗?在大冶公馆没有修好之前,你可以一半时间住在武汉,何必每天去大冶呢?”戴云珍在比自己大二十五岁的丈夫脸上吻了一口,表示谅解。
“我何尝不想住在武汉。但是,武汉的棉纺织业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出什么问题,而大冶矿业急需恢复生产,我住在这里,实在有愧于汪委员长对我的器重呢!”赵毓松的心胸里有着一种感恩戴德的激动。
姨太太的话,使赵毓松的思维退回到去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的一次签字仪式。那天,日本政府为了将其法西斯统制经济政策贯彻到中国,进一步掠夺中国沦陷区的棉纺织业,在控制沦陷区的面粉业之后,又由周佛海和日本驻南京大使本多熊太郎签订了《华方产棉区纺织业与日方在华纺织业联营协议书》。身为农矿部长的赵毓松与工商部长梅思平参加签字仪式。根据这个《协议书》,武汉沦陷后落在汪精卫集团手里的武汉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厂和裕华、大华、新兴、华兴、时代等五家私营纺织厂,与日本人开办的泰安纺织厂联营,由该厂经理市川东升任总经理。名为联营,实际上,不仅棉纱、棉布的销售和价格的制订,都是市川东升说了算,而且各联营厂每年还得向泰安纺织厂缴纳百分之五十的纯利润。根据这个《协议书》,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和武汉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棉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棉布被低价运往日本,造成中国的国防用布和老百姓的生活用布奇缺的窘况局面。近一年来,由于何佩瑢派出大批保安部队驻守在这些纺织厂,总算平安无事。
“作为中央的一名部长,我得切实维护中日和平,希望武汉的纺织业不出任何问题。”赵毓松向往着说。
“部长,部长,苦差事都落在你头上。”戴云珍撅着嘴巴说,“我可不愿意每天跟你去大冶受罪。”
“唉!你不懂。”赵毓松甜甜一笑,“昨天下午两点我在大冶时,汪委员长在电话里向我交了底,等大冶矿业公司的一切恢复正常了,我就回南京兼任司法行政部长,前任部长李圣五先生去德国当大使去了,让我身任两个部长,拿双份薪水哩!这是委座在电话里向我讲明了的。”他很兴奋,“所以,不管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我每天得去大冶转一转。你呀,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亲爱的部长大人!”戴云珍欣喜地跳下床去,扑向丈夫的怀抱里,在他脸上一阵狂吻。
女人是清泉,是白云,是金星,是皎月,是朝霞,是绿树红花,是高山大地。因为人类有了女人,天地间才五色纷呈,流光溢彩,男人才有创造的力量,光明的起点,幸福的归宿,人类才永葆青春,灿烂的文化才得以永恒的继承和持久的发扬。
那么,作为女性个体的戴云珍是什么呢?然而,这又能责怪她吗?
赵毓松和戴云珍吃了早餐,夫妇俩正准备带领随身卫士去大冶,一个身着和平军高级将领制服的中年人,带领六个身着和平军士兵制服的青年人闯进门来。
“赵先生好!”中年人主动向赵毓松伸出手来。
“将军阁下是……”赵毓松的两只眼睛,仿佛患夜盲症似的吃力地打量着对方,越打量越惶恐不安,但还是把手伸出去。
“我是和平军新编第五师师长李省吾,与阁下是第一次见面。”中年人把一张名片递给赵毓松。
赵毓松不懂军事,故平日不过问和平军的建制情况,接过名片看了看,不知和平军是否有这么个新编师,也不知是否有李省吾这么个师长,顿时警惕起来,等他向戴云珍和卫士使眼色时,他和卫士的手枪已被人缴走了,门也被关上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赵毓松一种大祸临头之感油然升上心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到顶里面的房间去。”中年人手往里面一指。这是一进三间的房子,分别为赵毓松的临时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
“顶里面的房间是我们的卧室,有话请在这会客室说。”戴云珍究竟受过特务训练,还比较沉着。
“这是白天,不是深夜,是你们的卧室又怎么的!”中年人两眼一瞪,“眼下,你们的行动只能听从我们的指挥!”
赵毓松住在第五栋第三楼,他的卧室与第四栋三楼省政府秘书长贺遐昌的办公室隔着个花圃相望。也许是戴云珍年轻易冲动的缘故吧,她一阵风似的走进卧室,打开北面的窗户大声叫喊:“救命啊!赵秘书长……”她没能再喊出第二声,脖子就被人卡住,两眼翻白了。等她回过气来,嘴里塞进一块破布,两只手腕已戴上了手铐。
“我们要处死你很容易,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看!我们手里的家伙都是无声的。”中年人用手枪口在戴云珍那高高隆起的胸脯上戳了一下,“想到你才十八九岁年纪,没有真正尝到人生的滋味,还是让你继续活下去。但是,你必须放老实点,放明白点!”
在同一个时候,被吓得战战兢兢的卫士也受到了与戴云珍同样的遭遇。
赵毓松已吓得魂飞魄散,不由自主地走进卧室,见姨太太右嘴角有团铜钱大的白泡沫,掏出自己的手帕给她擦了擦。他的手两次接触到塞在她嘴里的那团破布,想把它拔出来,但没有这个胆量,顿觉自己渺小而可怜。贺遐昌听到戴云珍的叫喊声,慌忙带了两个工作人员急跑到这边来。他边敲门边喊:“赵先生,赵夫人,你们出了什么事?”赵毓松的脑袋已被人用手枪口顶住,只能按照中年人的吩咐行事。他说:“没什么,贺秘书长!我们夫妻俩刚才打了一架。清官难断家务事。贺秘书长,谢谢你的关心。”门外的贺遐昌说了句毫无作用,但又不能不说的话:“夫人有什么不对之处,请赵先生多多原谅。”就带着人走了。中年人大模大样地往皮沙发上一坐。“请坐吧,赵先生,”他冷笑一声,“生活真会捉弄人,我倒成了这房间的主人了。”赵毓松啼笑皆非,只好尴尬地坐下。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赵先生!我是驻扎在宜昌、秭归一带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的钱俊卿。职务嘛,五天前是团参谋,现在是集团军司令部专与你们这号人打交道的对敌联络部少将参谋。”钱俊卿已取得了主动权,说话胆大气粗,“老实告诉你,多次把大冶矿业公司的铁和铜运走的是我,把牛场等四个日本人干掉的主谋也是我,把大冶矿业弄成瘫痪局面的主谋还是我!我知道,你一定很痛恨我,是吗?赵先生!”
赵毓松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说:“不敢,不敢!你们,你们要我干什么?钱先生?”他这种心理上的退却,是正义与非正义较量的必然结果。
“请你陪同我去见见泰安纺织厂的经理,也就是你们的所谓武汉纺织业联营总经理市川东升,要他把包括泰安纺织厂在内的九家纺织厂近三个多月来生产的布和纱统统交给我们!”
“这,这,我无能为力,武汉纺织业联营不归我管,我实在不好插手。”赵毓松诚惶诚恐,“不过,钱先生见市川东升,我一定奉陪。”
“赵先生太不诚实了。”钱俊卿教训他一句,“你离开南京来武汉的前两天,汪兆铭先生向你做了交待,要你好好管管武汉的纺织业,你插手是名正言顺的事!”
赵毓松仿佛被人掌握了生死似的惶恐,脸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青,最后变得苍白,手指也微微发抖。他无法否定,也不敢承认,心里忐忑不安,如同坐在针毡上,屁股不自在地在皮沙发上移动了两下。
汪精卫要赵毓松管管武汉纺织业的事,是周佛海在无意中透露给唐生明,唐生明要程克祥用无线电话告诉戴笠的。于是,军统驻武汉秘密联络组及时掌握了赵毓松的行踪,对武汉各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了如指掌。
“由于汪兆铭先生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与日本签订了丧失中国纺织业主权的《协议书》,致使沦陷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棉布、棉纱被日本掠夺走了,致使广大民众衣不蔽体,尤其令人愤慨和痛心的是,一些在前线流血牺牲的抗战部队,因军服用布无法解决,夏天到了没有单军装换,还穿着棉衣上前线,冬天到了没有棉军装穿,还穿着单军装打仗!”钱俊卿横眉立目瞪着赵毓松,“赵先生作为中国人,你难道没有一点恻隐之心?”
“感谢钱先生的教诲。抗战部队穿衣服这么困难,我的确于心不忍。”赵毓松感到为难,“但是,直接统治中国纺织业的是日本政府大藏省,要把武汉纺织业联营各厂现存的棉布、棉纱夺过来,我做不了主,市川东升也做不了主呢。”他顿了顿,“当然,如果钱先生有高招,我一定密切配合,鼎力相助。”
“好,够朋友!”钱俊卿说,“我这里有周佛海先生给市川东升的信。坦坦白白告诉你,这信是仿照周先生的笔迹写的。”他打开手提包拿出信递给赵毓松。以周佛海的名义写的信说:“随着和平军的编制不断扩大,部队军服用布量大大增加,军委开办的几家纺织厂生产的布匹和纱锭已不够开支,经驻日大使褚民谊先生与贵国政府大藏相小仓正恒先生磋商,报请近卫首相批准,兹将包括泰安纺织厂在内的九家联营厂近期生产之三万八千五百匹棉布(每匹一百尺)和五千八百四十吨棉纱交给和平军使用。所需款项缓日由财政部派专人前往武汉结算。现派新编第五师师长李省吾将军前往联络起运棉布、棉纱事宜,敬希接洽支持,即不胜感谢之至。”
“市川是个很狡猾的人,他会相信吗?”赵毓松将信退还给钱俊卿。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怕他狡猾。”钱俊卿胸有成竹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赵毓松讨好地笑着。
钱俊卿留下两个士兵看守戴云珍和那个卫士,带着其余的四个士兵监视着赵毓松走下楼去。在一楼的楼梯口,他们碰到了何佩瑢,赵毓松赶忙介绍说。“这位是新编第五师师长李省吾将军,这位是湖北省主席何佩瑢先生。”
“久仰,久仰,何主席!”钱俊卿满脸景仰表情与何佩瑢握手,“本想马上去拜望阁下,无奈有要事急于与市川东升先生磋商,只好从泰安纺织厂回来后,再去向您老人家求教。”
“李将军与我商量好了,我陪同他去泰安纺织厂办完事之后,再和他一道去见何主席。”赵毓松紧接着说。
何佩瑢知道新编第五师师长是李省吾,但从未见过面,又见他由赵毓松陪同,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忙说:“求教,实在不敢当!好,好,我等待着与师长阁下面叙。噢,二位去泰安纺织厂有车吗?”
“有,有!”钱俊卿手往停在前面地坪里一辆轿车和一辆吉普车一指。那是军统秘密联络组的车辆,但车上的徽记和牌号是和平军的,车头上插着戴有三角黄布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在泰安纺织厂各个车间的日本富田车,美国花旗车,英国卢顿车,玩命似的竞相旋转,到处一派繁忙景象,到处一片嘈杂的声响。市川三十五岁那年建立这个厂子,两天前他在这里庆贺五十寿辰。他在这里熬成两鬓银霜,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他见日本政府因发动侵华战争经济拮据,一连三年,每年向大藏省捐献一亿五千日元。因此,两个月前,他在东京受到裕仁天皇的召见,并被敕封为日本枢密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