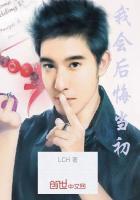这平地里蓦然响彻的一道清清冷冷的嗓音,如一颗漫不经心的石子,猛的投入到一片暗涌的深湖之中,激起一连串的波荡涟漪。
夏侯缪萦原本悬在喉咙口的一颗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把声音,瞬时又是一提,几乎急不可耐的想要跳出腔子,就如同一尾滑腻的鱼,不受控制的蹦落在泥地上,再也难以捡拾。
本能的转头,向着说话之人望去,夏侯缪萦一眼就撞进了那一双讳莫暗郁的寒眸里去了,但见溶溶日光之下,男人点了漆般的墨色瞳仁,却深沉的如一湾不见底的夜海,濯黑的没有一丝亮光,惟若鬼影里面幢幢,反射出泠泠的温度,沁寒似冰凌。
这一刹那,夏侯缪萦只觉心底某处,蓦地掀起无数的惊涛骇浪,层层叠叠的漫延上来,捉不紧,抓不牢,迅速的在她体内的每一根血管里,激荡洋溢,流窜至全身的各个角落,一发不可收拾。
赫连烁亦是心头微惊,箍住女子皓腕的一只大掌,本能的就要一松,却在转瞬之间,陡然反应过来,但见他眸光一厉,竟是将掌心里不盈一握的滑腻肌肤,揉搓的更紧,显然故意挑衅一般,施悠悠的开口道:
“本王还以为是谁鬼鬼祟祟的突然冒出来了呢?原来是三王兄,当真是吓了本王与缪儿一跳呢……你说是不是,三王嫂?”
夏侯缪萦本就还沉浸在男人的蓦然出现,带来的一系列震荡之中,久久不能回过神来,陡的却听到近在咫尺的赫连烁的声音,心头顿时悚然一震,下意识的就朝着说话之人望去。
这四目交投的一个画面,戳进赫连煊的瞳底,似在一记巨大的冰块上,不期然的划破了一道锐利的痕迹,丝丝冷气,从不见底的深渊里透出来,迅速的笼满全身,连周遭的温度,都仿佛骤然降了几分。
夏侯缪萦没来由的打了个冷颤,一把嗓音,近乎低喃,不受控制般的唤道:“赫连煊……”
男人望着她尚带些懵懂的瞳色,冷戾寒眸,似是一敛,沉沉嗓音,没什么喜怒的开了口:
“过来……”
夏侯缪萦触到他这隐忍的几乎一触即发的清冽目光,心头残余的激荡,刹时尽数被逼了走,只余一片莫名的紧张。被定在原地的双腿,不由自主的就要往他的方向挪去,但转念又想起,他这口中吐出的“过来”两个字,嚣张的如在唤他家的阿猫阿狗一般,那命令的语气,理直又气壮,听来当真叫人十分的不爽。
就这样屁颠屁颠的过去他身边,夏侯缪萦表示有些不甘心,但如果继续任由这赫连烁将她箍在他的大掌里,亦更非她的所愿,两害相较取其轻,虽有定论,却仍不免有些踟蹰。
哪知她这须臾的犹豫,落进赫连煊的眼睛里,又是一番搅起的风暴,如狂风卷着落叶,飞旋在半空之中,几乎难以自抑。
赫连烁亦察觉到了她的踌躇,却是心底漾起连绵的暗喜,立马形于色,毫不掩饰的露出几分幸灾乐祸的意味来:
“看来三王嫂似乎并不想过去王兄的身边呢……不如由本王代劳,送三王嫂回府,如何?”
夏侯缪萦纵然再迟钝,也觉出对面的一个男人,因为他这六王弟的一番话,而瞬时笼罩下来的冷冽气息,头皮不由一麻,本能的就要从赫连烁紧握的大掌之下挣脱,但他显然早有准备,只将她箍的更紧,半分都动弹不得。
夏侯缪萦忍不住抬眸,恶狠狠的瞪向他。同时一把青葱似的指甲,毫不留情的掐着他的掌心,只盼他能够吃痛,将她放开来,哪知这人手掌之厚,更甚过脸皮,任她如何用力,他亦是纹丝不动,一张唇红齿白的嘴角,甚至还暧昧的扯出一抹邪肆笑意,瞧来真真如妖似孽。
赫连煊冷冷睨着对面的一男一女,清冽嗓音,却是没什么情绪的开口道:
“越俎代庖这种事,就不必麻烦六王弟了……”
话声未落,男人高大秀拔的身形,却是蓦地一闪,转瞬之间,已移到了夏侯缪萦的面前,她甚至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出的手,但觉腕上一痛,她整个人,便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狠狠拽进了一具坚实的怀抱之中,那强而有力的势道,竟撞得她半边身子都是一麻,不由闷哼出声。
赫连烁的震荡,却远比她更甚。虽说刚才他这三王兄是突然发难,自己没防备,才让他一击得手,但扪心自问,若两个人真的实打实的交手的话,他同样并无必胜的把握。
尤其是看到女子如一枝缱绻的栀子花般,窝在他的怀中,赫连烁更觉刺目,妒忌似缠绕的藤蔓,将他紧紧锁住,烙下一道道深浅不定的印痕。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邪魅一笑,赫连烁目光凉凉,在对面一男一女身上扫过,“三王兄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这么喜欢跟本王抢东西……”
男人语声轻曼,透出股真假难辨的意味来,赫连煊却仿似听到了一件极之有趣的事情般,只将薄唇微勾,漾起抹冷冽的弧度:
“难道不是六王弟你一直想要抢本王的东西吗?”
说这话的男子,濯黑瞳仁里,有着目空一切的傲然与嘲讽,一张清俊冷毅的面容,却是浮着丝丝漫不经心的潇洒,惟有箍在女子纤细腰肢上的如铁长臂,惩罚般的狠狠收紧,似将一切的不爽,都尽数发泄在了这充满占有性的一个动作之上。
夏侯缪萦被他勒的几乎喘不上气来,只觉整个腰身,都快坳断了一般,偏偏男人将她搂的丝毫密不透风,稍微的挣扎,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已被他狠狠掐死在了怀中。
死咬住一口银牙,夏侯缪萦方能堪堪阻止自己想要将他,嚼吧嚼吧吞到肚子里的冲动……尼玛,这俩人是把她当成了可以任由他们争来抢去的一件东西吗?东西你个大头鬼,她才不是东西呢……不对,她的意思是,她才不要当什么东西……面前的这两个男人,他们才是东西,他们全家都是东西……身子动弹不得,夏侯缪萦只能猫在他的怀中,恨不得将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一双死命拧着他腰间软肉的玉手上。
赫连煊朗逸眉眼,微不可察的挑了挑。大掌却是如铁似钳,不动声色的将女子猫爪一般不安分的挠在他腰上的一双小手,狠狠卷进了他温厚的掌心之中,那强势的力度,就像是关住了一只拼命想要逃离的鸟雀,任她扑棱断双翅,却再也飞不出他的股掌。
夏侯缪萦只觉深深的挫败。除了抬眸,狠狠瞪着男人好整以暇的半张侧脸之外,仿佛再无他法。
正自懊恼不已间,却见赫连煊蓦地薄唇轻启,嗓音徐徐,将檀口里的每一个字眼,都咬的如梦似幻:
“况且缪儿根本不是什么东西……她是本王明媒正娶的妻,是本王八抬大轿抬进门的正妃……除了本王,不容任何人的染指……”
男人一把清清冷冷的嗓音,一如既往,却又字字掷地有声,有如珠玉落盘,在深秋微凉的空气里,荡开一圈圈细小的涟漪,撞进夏侯缪萦的鼓膜里,迅速的沿着奔腾的血液,蹿遍全身,似簇了一团火,在所过之处,点起星星点点的火苗,微烫着心底最深处的每一个角落。
落在男人朗俊侧脸上的一双明眸,不自不觉褪尽了恼与恨,漾起蔼蔼浮光,闪烁的似天边最耀眼的两颗寒星,每一丝每一缕的波动,都仿佛只映出瞳底的那一道秀拔身影,除了他,她澄澈的眼中,如再无其他任何的杂质。
夏侯缪萦听到自己,怦然心动的猎猎风响,一下一下,狠狠撞击在她滚烫的骨血里,急促的呼吸中,像是要冲破她的胸膛,迫不及待的从腔子里跳出来一般,连绵而不绝。明知眼前的男人,也许不过是为了刺激另一个男人而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表白,却似有着蛊惑人心的魔力,叫人不受控制的往他挖好的一具巨大陷阱里,心甘情愿的往下跳。
赫连煊很快察觉到,她灼灼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如丝似线,将他一寸一寸裹在里面。被她凝望住的侧脸,有微烫的温度,一点点的漫延开来,似春日里融融的日光,铺洒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像千万只小爪子一样,轻轻挠着她眼眸所及的地方,酥酥的、麻麻的,爬过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叫人心痒难耐。
男人竟仿佛需要微微侧目,才能稍减这不在预料之内,无意闯入的异样之感。
赫连烁却是动也未动,将对面的一男一女,最细微的波澜,都尽数收归眼底。他看到目光晶亮清透的女子,就那样安定的凝视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乌黑的瞳仁,似水洗过一般,缭绕开热烈而缠绵的温度,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却是毫无阻隔的投射向他,世间的一切光影,都似在她眸底,幻化成那个男人的身姿。
妒忌如遇水疯长的野草一般,堵满赫连烁的心口,冷笑一声,便听他洌声开口道:
“三王兄这番话说的好不动听,只可惜没一句做的准吧?你若敢当着本王的面,告诉三王嫂,你为何千方百计的娶她进门的原因,那本王才真正的佩服你……”
夏侯缪萦只觉埋在胸膛里的一颗心,重重一跳。下意识的望向面前近在咫尺的男人的一双明眸,不自禁的漫出层层的紧张与不安,几乎要将她淹没。
赫连煊却只是凉凉一笑,一张刀削斧砍般的俊颜上,容色寡淡而清冽,不氲丝毫的情绪。
“六王弟的佩服,还是自己留着吧……本王与自己爱妃之间的恩怨,想必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指手画脚……六王弟与其有功夫在这里挑拨离间,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处理,你那侧妃常氏留下的烂摊子才是……话说六王弟如此的流年不利,接二连三的出了这许多事情,若不好好补救,只怕跟唐国公主的婚事,还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去吧?”
男人凉薄的嗓音,悠悠响彻在秋意峥嵘的林间山路上,卷着凛冽清风,荡开丝丝嘲讽的温度。从夏侯缪萦的角度望去,只能看到他朗逸俊美的半张侧脸,棱角分明,一如雕刻的大理石般,冷硬,不带半分的温度,犹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神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间,便将人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
一腔绮思,尽数化为乌有。心底炽烈燃烧,熄灭成灰,只余冰冷余烬。
夏侯缪萦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好笑。不过因为他三言两语的好话,她就几乎忘记了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吗?夏侯缪萦,你还可以更愚蠢一些吗?
夏侯缪萦懊恼的想死,却又莫名的心灰意冷。
沉默的对峙,在两个男人之间,一触即发。
而她夏侯缪萦,却自始至终,不过是他俩之间斗争的一道布景墙吧?需要的时候,扯出来展览一番,谁又在乎她是喜是怒,是悲是哀呢?
秋风凛冽,吹得人衣袂猎猎作响,九月沁凉的温度,穿透凉薄衣衫,像锐利的刀锋一般,剐在人的肌肤之上,漫开层层的颤栗,经久不息。
男人的怀抱,坚硬厚实,炙热如铁,夏侯缪萦却只觉得冷。
“你们两兄弟说完了吗?”
咬牙,狠狠将唇齿间逸出的凉气逼尽,夏侯缪萦没什么情绪的开了口:
“说完的话,可以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各归各家了吗?”
两个男人,同时望向她。夏侯缪萦自觉问心无愧,只目不斜视,似连多看他们一眼,都怕脏了自己的眸子。
“冷吗?”
却听身畔的男子,嗓音低魅,犹如爱侣间不为外人道也般,幽幽开口问道。
夏侯缪萦但觉心口之处,像是被什么东西裹着,在炽烈燃烧的火堆上,滚过一遭般,似烫似痛的感觉,刹时传遍全身,说不出来的滋味。
还未等她反应过来,身上却是不由一暖。玄青色的披风,不知何时,被男人从自己身上解了开来,然后不容分说的将她牢牢裹住。
属于他特有的清新气息,瞬间丝丝萦绕在夏侯缪萦的鼻端,无孔不入的钻进她体内的每一个毛孔里,荡开连绵的热度,似苦似甜,似喜似悲,说不清,道不明,激荡而蛊惑。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男人清清冷冷的嗓音,尚响彻在耳畔,划破满心的涟漪,夏侯缪萦却仿似刚刚自噩梦中惊醒,下意识的拒绝道:
“不用……我不冷……”
她的急于摆脱,落进赫连煊的眼瞳里,有极冷冽的精光,陡然闪过。
“乖……”
轻巧的一个字,从男人凉薄唇瓣间,徐徐倾吐而出,似淬了数不尽的缠绵与情愫,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牢牢将夏侯缪萦笼在里面,如同被罩住的一只鸟兽,再也难逃。
想要去解身上披风的手势,就这样消弭在男人的强势之中,任由他温凉的指尖,亲昵而自然的将她包裹的更紧了些。
赫连烁冷冷的瞧着对面的一男一女,该刹那,他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般,被隔绝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从未有过的灼烈恨意,与茫茫妒忌,紧紧交缠在一起,如同喷涌而上的潮水一般,在坚硬如石的心底,缓缓漫延出来,划下一道道裂痕。
“这样的温柔体贴、耐心周旋……”
邪肆一笑,赫连烁有如记起了一件极之有趣的事情般,施施然的开口道:
“别说三王兄的其他几位侧妃,都无福消受……只怕……”
语声到此,悠悠停顿,赫连烁似漫不经心的瞥了一眼那窝在男人怀中的女子,薄唇轻勾,便即开口……夏侯缪萦心中陡然一跳,直觉他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定与她有关,甚或就是她一直想要知道的那部分原因,一颗心,瞬时不由紧张起来。
却听身畔的男人,偏在这个时候,语声曼曼,打断了赫连烁未完的一切恩怨,说的是:
“只怕六王弟今日一番言辞,落进不明就里的人耳朵里,还以为是六王弟你对本王的爱妃起了非分之想,觊觎自己的三王嫂,所作的妒忌之举呢……”
夏侯缪萦只觉,悬在半空中的一颗心,又是重重一跳,但旋即,却一点一点的往下坠去。身旁的这个男人,永远都知道,在什么时间,说什么样的话,会将人一切的希望,都毫不留情的狠狠堵死。好整以暇,不慌不忙,优雅而残酷。
果然,先前还迫不及待的想要揭穿他的赫连烁,此刻却不由堪堪闭了嘴,似在斟酌着他一时意气,想要吐出的这个秘密,到底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利弊?值不值得?
赫连煊却显然不打算给他这样的机会,疏离一笑,提醒道:
“天色也不早了,六王弟不是急于进宫请安吗?想必洛妃娘娘一定有许多话跟六王弟商谈的吧?本王与缪儿,就不打扰六王弟进宫了,自便……”
转首,赫连煊薄唇潋滟,荡开邪魅笑意,冷冽寒眸,映着瞳底那一道纤细的身影,浮光蔼蔼,明灭莫测:
“缪儿,我们回府……”
语声泠泠吹散在微凉的空气里,夏侯缪萦只觉手上一股灼热的力量传来,男人微带薄茧的掌心,就这样覆住她,大掌牵着她的小手,一步一步向着不远之处的马车走去,两人的脚下,踩着茫茫枯黄的落叶,发出窸窣而柔软的声响,久久回荡不息。
赫连烁望着那一男一女,两道身影,旁若无人般的掠过他的身畔,并肩而行,如同最亲密的爱侣一般,走向共同的目的地,一双料峭桃花眼,似淬了初冬郁结的冰凌,散发出无尽幽幽的寒气,薄削唇瓣,却是斜斜轻挑,勾起抹高深笑意,邪魅异常。
山野静谧,惟有轰鸣的马车,踏破一路颠簸,驶向不知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