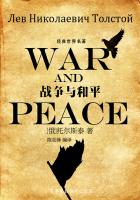王双花闻讯从娘家赶了回来。闻讯从娘家赶回的王双花和周天一大吵了一架,吵得天昏地暗。
对劝架这件事,周天一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周天一这种人,居然一个死心眼犟到底,王双花觉得自己没法跟周天一这种人过下去了。
王双花两口子吵翻了天,孙大壮和曹爱梅两口子没赶过来劝架,庄子里也没一人赶来劝架。
王双花突然觉得和周天一的日子一点滋味也没了。
孙大壮和曹爱梅两口子不再吵架了,两人恩恩爱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两口子记恨上周天一,再也未登过周天一的家门。
村里人觉得周天一劝架的事很好笑,就有了两句口头禅:周天一劝架——劝离不劝和;周天一劝架——适得其反。村里的孩子一见周天一就唱这两句口头禅。
王双花觉得这日子一下子断根了,见天和周天一吵着。村里却没一个人过来劝架。
后来,周天一和王双花吵得没了心气,心平气和地离了婚。
王双花很快嫁人了,是村里人帮张罗的,嫁给了光棍汉苏大龙。两口子十分恩爱,曹爱梅两口子和他们又有来有往。
村里人谁也不爱搭理周天一,除了那些唱口头禅的孩子。
不久,周天一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去广东打工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村里人还常常有人对着孩子念叨起周天一:长大了可别跟周天一一样缺心眼,连个架也不会劝。
签字笔
谢丰荣
超级歌星经过不久,大街上空空的,只剩下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哭,她没有得到歌星的签名。
我想我可以帮帮她。
女孩听见日记本哗哗翻动,诧异地回头,这样她就看到我了。
“天啦,一支笔,在翻我的日记本!”她嚷道。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翻过上千人的日记本!是刚才那位歌星派我回来,满足你的愿望。你看,名已经签好了,货真价实是他的笔迹!”我说。
女孩对歌星签名很熟悉,她在很多人的本子上看过。
“是真的!”她惊喜万分。
突然,一只手把我抓住。女孩取下假头发,变成了面目狰狞的男子。
“这次,你跑不了了!”他大笑。
我上当了!他的绰号叫缠丝兔,为了抓我,已经想尽了办法,我对小女孩怀有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在劫难逃。缠丝兔把我装进一个笔盒,笔盒上有锁,他带着我到了一个阴暗的地窖里,然后把我放出来。
我怒视着他。
他洋洋得意,抱出一尺多高的各种材料。他拿出几份扬了扬,贪婪地说:“看看吧,我三年前就伪造了这些字据,这儿大概有一千张吧。现在只等你签字了,签了字,这些证据就都生效了,我就可以去各个国家打官司、收钱了!”
我问:“你这些都是什么证据?”
缠丝兔说:“全是别人欠我钱的借据,有法国的,有西班牙的,有大银行的,有世界首富的,还有总统的……”
“他们都欠你钱?”我觉得不可思议。
缠丝兔说:“没有!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我。但你帮我签上他们的字,他们就欠我钱了!哈哈!”缠丝兔手舞足蹈。
我镇定地说:“我又不是他们本人,我的签字算不得数。”
“我早知道你的底细了,就别装了吧!你的真名叫签字笔,对吧?你不是一支普通的笔,你的特异之处是,逼真模仿任何人的笔迹,即使本人看了也只好承认,对吧?你是由中国一位科学家研制成功的,对吧?你闯荡天下三年,干了很多行侠仗义的事情,对吧?”
四个“对吧”问得我着急起来。这家伙在我身上花了多少精力呀!
是的,这一路上,我常帮助那些单相思的人写情书,成全了许多美事。有时候,我见一些不法分子伪造证据,将无辜者告上法庭,就悄悄篡改了状纸,还签上不法分子的名字,这样全成了他们自讨没趣。
我的真名就叫签字笔,我才是造假的祖宗!研制我的科学家叫郑直。
缠丝兔等不及了,他把借据全摊开在我面前,强迫我按指令签名。
我一阵晕眩,突然呕吐不止。
缠丝兔骂道:“妈的,你今天就是累死,也得把这一千份借据签完!”
可是我笑道:“险恶的先生,我身体不适,呕吐得这么厉害。你看看,我肚子里的墨水全吐光了,一点也没有,怎么签字呢?还是招待我美美地吃一顿,然后再签不迟。记住!我只吃黑墨水。”
“好的,好的!”缠丝兔欢喜地端出一瓶黑墨水来。
我郑重地走上桌子,做出开心就餐的样子,然后,我将墨水吸了个饱。
……
郑直是在荒郊野外捡起我的。那时候,我已昏迷了三天三夜。
郑直一滴泪将我淋清醒过来。
我问这三天三夜的事情,科学家告诉我:缠丝兔拿着借据去找法国总统,说要求他归还十年前的借款共计一百万元。经法庭辨认,那所谓的总统签名是伪造的。缠丝兔正在狱中呢,听说他疯得厉害,每天将“签字笔”连说一千遍。
我感到奇怪,问:“我并没有给他签一个字就倒下了呀,他怎么会……”
科学家说:“是他见你死了,就自己握住你,用你这支笔签上总统姓名,他以为只要是你签的,就不会有假。”
我说:“真是财迷心窍!”
科学家问我:“我在研制你时,就设定平常墨水是你的烈性毒药。我是害怕有人控制着你干坏事,但这对你,就太残忍了!你不会怪我吧?”
我使劲地摇了摇头。
科学家叹了口气,最后说:“好样的!宁死不屈!现在,你的五脏六腑已经烂完,我也无力回天,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不过,你在世间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那东西比生命更加重要!”
我听着,微笑着闭上眼睛……
失恋的长发
金晓磊
卡付卡无精打采地走出K城火车站,就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直往耳朵里钻。他抬起头朝不远处望了望,一个奇怪的名字立刻跳进了他的眼睛里:情感慢递工作室。只听说过“快递公司”,还从来没见过“慢递工作室”,而且是“情感”的,于是,卡付卡决定去看个究竟。
宽敞明亮的大厅,此刻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人手一张宣传单,两三成群,指指点点,说说笑笑的。卡付卡从服务小姐那里也领了一张宣传单,找了个人少的地方,仔细阅读起来。等阅读完上面的内容以后,卡付卡突然觉得这个“情感慢递工作室”的老板真是太神通太友善了,他好像全程观看了自己在S城所遭遇到的感情问题,然后为自己量身订制了这么一个工作室,来欢迎自己的到来。
人群逐渐散去,大厅里冷清下来以后,卡付卡对一个服务小姐说:我想和你们的老板面谈一下。
很快,卡付卡就见到了那个年轻的老板莫哈。莫哈二十来岁的样子,满脸的忠厚老实。卡付卡悬着的心就掉了下来。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那个大皮箱,从里面掏出一个纸盒来,说:我想把这些东西慢递一下。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您是我们工作室开业后的第一个客户,所以一切费用全免。莫哈伸出手来,握住卡付卡说,不知道您想慢递哪一类情感?
爱情,可惜是有关失恋的。卡付卡边说,边打开了那个纸盒。
莫哈看了看,是一些丝巾、耳环、信件之类的物件,估计是那个女孩子退回来的。的确很遗憾,莫哈拍拍卡付卡的肩膀继续说,初恋是美好的,爱情也是美好的,继续努力啊。
卡付卡的眼睛有些发潮了。
莫哈连忙叫来工作人员,清点登记卡付卡的物件,然后,请专业的人员估算了这些物件的价值,最后双方签订了合同。
一切手续结束以后,莫哈领着卡付卡去了“失恋厅”,亲自将卡付卡的物件放进了玻璃罩显眼的位置中。
送卡付卡出大门的时候,莫哈再一次握住卡付卡的手,说: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欢迎您随时来“失恋厅”,看看您自己的宝贝!
卡付卡仰头看了看“情感慢递工作室”,头一扭,拉着大皮箱,在K城的大街上笨拙地奔跑起来。K城大街上的时间,就跟着卡付卡奔跑起来了。
那些不知疲倦的时间,跑啊跑,像风一样地跑过了三十年,跑皱了卡付卡的眼角,跑白了卡付卡的双鬓,跑弱了卡付卡的身子。
此刻,卡付卡坐在卡黛集团68楼董事长办公室的老板椅上,感觉无边的疲倦包裹了自己。
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是“情感慢递工作室”的老板莫哈打来的。莫哈说:老伙计,你好啊!你的物品,我们按照当年合同上的时间——2046年8月17日——准时送到了S城的黛比那里。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为你捎带来了黛比的亲属让我们转交的物件。现在,我已经派人给你送去了。
卡付卡淡淡地说:谢谢了,老朋友!
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黛比的消息。卡付卡不是没这个能力,和秘书说一声,派个人去调查一下就行了,但他一直没这样做。他一次次迫使自己不能这样做。他需要等。等一个重要的日子:2046年的8月17日。他想知道黛比在三十年以后,收到当年很绝情地退回来的恋爱物件以后会怎么样。
敲门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工作人员送进来的是一个纸盒。
纸盒里是一束长长的头发和一封发黄的信。
信的第一句是这样说的:亲爱的阿卡,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卡付卡捏着信件的手,控制不住地抖动起来。上面的那些字,像一只只蚂蚁爬动起来。卡付卡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往下看:原谅我的绝情,骂你是个穷光蛋,还让你早点滚蛋。事实上,那时候,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当你连同信件一并收到当年你曾经抚摸过的那些头发时,我想你也猜到了我的病。白血病。好想见证你的承诺:替我梳一辈子的头发。可惜,我没有那样的福分……永远爱你的黛比!2016年5月27日。
卡付卡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一滴,一滴,掉进发黄的信纸中。那纸,像一只枯黄的蝴蝶飞了出去。
卡付卡找来一把梳子,轻轻地梳理起那束长长的秀发来。梳啊梳,把白天都梳成了黑夜。
黑暗里,一朵火苗跳了出来。那些长发,在火苗上,欢快地扭动起来,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味来。
卡付卡狠狠地翕张着鼻子,想把所有的味道都吸进自己的身子里……
风不知道云知道
非鱼
一场车祸把一切都改变了。
池江月想到了死。无数次,她绝食,喝大量安眠药,甚至放开轮椅的手刹,朝江边冲过去。她痛恨苟且活着的生命。
每一次,都是父亲把她拉了回来。
一夜白了双鬓的池原提前办了退休,专门在家照顾她。为她做饭、洗衣服、擦洗身体。在那场车祸之前,池原从来没有做过这些。
池江月经常会大喊大叫,发疯一样摇自己的头,拍打麻木的双腿,直到把长长的头发摇成乱糟糟的一堆。池原不说话,重新帮她仔细地梳好,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这是他唯一会梳的发型了。
池江月说:爸,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让我死。
池原看看她,不说话。转身不停地擦拭妻子的照片。
同学聚会那天,池江月说死也不去。
是池原告诉她同学聚会的消息的,说他们以前的班长打电话到家里,要她无论如何要参加,两年了,同学们都很想她。池江月说:不,不去。
池原坐在她身边,拍着她露在被子外边的胳膊:去吧,同学们都等着你。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池原把电话递过去,池江月就是不接。池原接了,告诉他们江月马上就到,再稍等会儿。
最终,池江月和池原一起参加了同学会。她偷偷准备好了一个很大的苹果,藏在毯子下,如果谁敢提她的腿半个字,她就会把苹果扔过去,砸烂他的脸。但没有,大家像过去一样开心地说话,放肆地笑,好像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遭遇过车祸的人。
回到家,池江月把那只暖得温热的苹果递给池原:爸,我想吃苹果。
第二天,池原刚出去买菜,池江月就听到手机有短信提示音。她打开一看,一个陌生的号码,就六个字:池江月,我爱你。
车祸以来,第一次看到爱这个字眼,池江月的脸一下红了,拿手机的手有些发抖,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匆忙又删除了,然后把手机扔在床上,拨动轮椅,离开手机很远很远。
恶作剧。为什么要拿我来开涮。仔细想想,池江月又开始生气。
第二天,同样的短信又来了。这次既没有兴奋,也没有生气,池江月只看了一眼就删了。爱,距离她太遥远了。她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爱和被爱。车祸把一切都粉碎了。
一连很多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内容,在池江月的手机上出现。
她有些忍耐不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人,会是谁?池江月第一次回复了短信:你是谁?没有回复。整整一天,手机沉默得像个顽固的罪犯。但是,以后的每天,那条短信,依然准时到来。
池江月特别想跟池原说说,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真的是个恶作剧呢。她只有独自沉默地想,反复地想,想到头绪越来越乱。
池原似乎并没有发现池江月的变化,依然按时买菜,做饭,推她去散步,给她讲市井街坊里的新鲜事和笑话,池江月偶尔会答应一声,或者笑笑。
又一次的信息到来时,池江月鼓起勇气回拨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通了,无人接听。再拨,依然无人接听。太奇怪了,究竟是谁?同学吗?聚会时有好多人要了她的手机号码,而她只顾着手里的苹果会扔向谁,并没有留他们的号码。
一个又一个男同学从池江月的心里翻过,曾经朦胧美好的细节又被想起。躲开池原,池江月偷偷地把以前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揣摩着那个号码后面的面孔。细密绵长的情绪在池江月的心里慢慢生长,长成一片绿茵茵的青草地。
突然有一天,池原的身后跟进来一个人,和池原有说有笑。池原说:这是小田。
小田来了一次又一次,帮池原干活,和池江月聊天。他说:很早就认识你的。
偶尔,池原在忙,会让小田推池江月出去散步。
小田说:我们去个新地方。他们走很远很远的路,到达一块菜地,小田说:就是这里。
池江月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不停地喊小田:看啊,茄子;看啊,黄瓜,看啊,辣椒……小田答应着,摘一些放在她腿上,池江月两只手拢过来,把那些蔬菜都拢在怀里,像拢着可爱的孩子一样。
夏天过去的时候,池江月发现小田来的次数越来越多,而她对他的等待也越来越强烈了。她甚至不记得,那条持续了几个月的短信,什么时候已经自动消失了。
但也许池原会记得。
这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