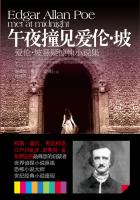罗斯愤怒至极,环境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可周围全是荒草和乱石,没有污染,没有噪声。他沿着断崖向北徒步走了十几公里,终于,他发现了秘密所在:那个地方正是鸟儿的栖息地,却在旁边建起了许多加工厂,工厂内的声音隆隆着,噪声十分吓人,周围的鸟儿成群结队地寻找着良方,它们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却无能为力,只好选择了死亡。
罗斯闯到工厂内部,坐到了领导的办公室里,他将自杀的鸟儿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请领导给予解释。那位领导正襟危坐着只是狞笑,然后将一记耳光送给了试图失控的罗斯。
罗斯又找到当地政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政府官员笑着说道:让鸟儿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它们不能够阻碍经济发展。
这句话提醒了罗斯,罗斯回去后,准备了一大张毯子,将毯子铺到断崖的岩石上,结果起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许多鸟儿一次撞击不成功后,选择了退缩,时间久后,自杀的鸟儿明显减少了许多。
罗斯喜出望外,他这样想着,既然是噪音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如果说我给它们带来节奏感温柔的音乐,也许,它们会安静下来。
罗斯每天给鸟儿吹箫,音乐悠扬耐听,许多鸟儿停顿下来,落在周围的草地上,还有些大胆的鸟儿试图落到罗斯的肩膀上,罗斯选择了接纳,他和鸟儿成了好朋友。
两年时间,罗斯改变了这里的生态规律,自杀的鸟儿几乎为零,罗斯想着自己可以写一本书,来讲述关于鸟儿自杀的故事。
时间来到了2008年,一位看破红尘的姑娘来到了断崖边,她心爱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想选择死亡,到天国去寻找她的最爱。
罗斯看到了她,不说话,现场寂静且柔软。
他只是不停地吹箫,还将一杯杯香茶放在姑娘面前,姑娘回头时,看到了无数只鸟儿,它们伴随着彩云在天上飞,好美的场景呀。
姑娘一直倾听着,他们对峙了好长时间后,她将手递了过来,罗斯牵了她的手。
2009年春天,一个叫罗斯的小伙子和他的爱人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如果一只鸟儿选择了轻生》,他们在书中讲述了自杀鸟的故事,并且讲述了他们美丽的相遇和爱情故事,在文章的最后,他们这样写道:
如果一只鸟儿选择了轻生,我们的双手虽然无力,却可以为它铺上柔软的草坪;
如果一个可爱的人儿选择了轻生,我们的爱虽然脆弱不堪,也可以为他打开心扉,奏响一曲喜乐直通黎明。
今天真好,没有人自杀。
父亲举重
杨汉光
国庆节快到了,单位准备搞两项活动,用周局长的话说叫一文一武,文的是出墙报,武的是体育比赛。
周局长也来了稿,我就找几个人帮忙出墙报。父亲的稿也来了,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更让我吃惊的是,父亲是用毛笔写的,每个字都是标准的楷体。我把父亲的稿直接贴到墙上去,大家啧啧称奇。
出了墙报,我就给所有稿件分等级,这是很微妙的事。按照单位的老传统,局长、书记的稿是一等,副局长、副书记的稿是二等,一路分下来,父亲的稿应该垫底,是最差那个等级。可父亲的稿分明是最好的,我破例把父亲的稿提到倒数第二等。
分好等级,我就给周局长过目。周局长接过名单,从上往下看,看到父亲的名字时,眉头略皱一下:“小杨啊,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可单位不是家呀。”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局长批评得对,我父亲应该是最后一等的。”
周局长用红笔将父亲的名字圈起来,“唰”一个箭头指到最后一名,因为用力太猛,笔尖在纸上划出了一道裂痕。我隐隐感到,这道裂痕里,夹有周局长的一点私怨。
周局长和我父亲确实有点旧怨。那时候周局长还是科长,和我父亲共同督建单位的围墙,围墙修好后,工头给了我父亲一千块钱,父亲惶恐不安,就把钱交给纪检部门。没想到纪检部门顺藤摸瓜,查出周科长收了工头两千元,给了他一个老大不小的处分,从此他就不跟我父亲来往了。虽然过了许多年,周局长还余怨未消。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刚好碰见父亲。父亲知道自己是最后一等的最后一名时,什么也没说,回到家才一头钻进房里去举重。父亲的房里有一副杠铃,母亲说,父亲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就举重,已经举了二十多年。
一会儿,我听到父亲的房里“咣当”一声响,接着是母亲的惊叫:“阿光,快来,你爸闪着腰了!”
我冲进父亲的房间,看见他已经坐在沙发上,母亲正在给他揉腰,杠铃滚到了墙根下。我问父亲要不要去医院,父亲站起来,扭一扭腰:“没那么严重,明天我还要参加举重比赛呢。”我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参加比赛了,或者改打乒乓球什么的,父亲说:“举重才是我的专长。”
第二天,单位搞的体育比赛开始了。我特意请母亲到单位来陪父亲比赛,万一发生意外好逼他放弃。参加举重比赛的只有七个人,周局长也是其中一个,他身材矮壮,挺适合做举重,据说读大学的时候还进过举重队。这是单位搞活动,很随便的,大家推举周局长当裁判,周局长象征性地推辞一下,就接受了,这样他就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周局长首先上阵,一下子举起90公斤。他这一举就像做报告定了调一样,后面一连五个人都没能超过他,身体最壮那个小伙子也只要了80公斤,大家都称赞周局长厉害。
父亲最后一个出场,他脱掉外衣,里面穿的竟然是紧身的运动服,腰间赫然扎着一根宽宽的皮带,好像参加的是正规的国际大赛。
父亲要了100公斤,我走过去小声劝阻:“别人都不敢超过周局长,你不要举这么重。”父亲说:“我想得一回第一。”
父亲在单位里做什么事都力争做得最好,名字却次次排在最后,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心再劝阻他,只是提醒说:“你只要举起91公斤就稳获第一了,用不着举100公斤,小心你的腰伤。”父亲低声说:“举起100公斤,我还怕比不过人家的90公斤呢。”
父亲说得不错,他的墙报稿不是写得最好,结果变成最差吗?父亲执意要举100公斤,我心里酸酸的。
我退到场边,暗暗替父亲鼓劲。父亲真是好样的,做了个深呼吸,俯身抓杠,奋力把100公斤举过头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却忽然发现裁判不见了。父亲举着杠铃,叫我快去找周局长。我说:“大家都看见你举起100公斤了,你放下来吧,一会儿跟局长说一声就行了。”父亲喘着粗气说:“你们怎么做得了主?”母亲也着急地说:“快去找周局长啊,没有领导点头,你爸是不会放下铁杠的。”
我只好去找周局长,听说他进办公室了,我就直奔办公室。周局长果然在办公室里,他正在接电话,跟对方没完没了地说笑。我好几次想打断他的话,又不敢。从办公室的窗口能看见举重的赛场,父亲依然举着杠铃,脚步踉跄一下,又踉跄一下。
我心疼极了,赶紧跑回赛场,对父亲说:“周局长在办公室接电话,一时半会还来不了。爸,你先放下,等局长来了再举。”
父亲喘得更厉害了,断断续续地说:“一……放下,我……我就举……举不起了。”我有点恼火地说:“那就不要举了。”
父亲不听我的,依旧踉踉跄跄地举着沉重的杠铃。我只好请母亲快逼父亲退出比赛,母亲却说:“你爸在单位委屈了一辈子,他举起的是一口气啊!孩子,你就成全他一回,快把领导叫来吧。”
母亲的话像刀子割我的心,我赶紧跑向办公室。这回我没有进去,在门外狠狠地把电话线扯断了,周局长的笑声戛然而止。
周局长终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可是,父亲已经放下杠铃,一只手使劲按住腰,估计是腰伤加重了。周局长回到裁判席上,父亲喘着气说他举起了100公斤。周局长望着父亲说:“老同学,你我知根知底,从读中学时候起,你的力气就比我小,我都举不起100公斤,你能举起来?”
这是什么话?连我母亲都生气了:“那铁杠铁饼不是还没拆散吗?叫人拿秤来,称一称就知道是多少斤两了。”
周局长说:“这杠铃我一看就知道是100公斤,问题是杨永福举没举起来。”
“大家刚才都看见我父亲举起来了。”我请同事们给父亲作证,可那些人都知道父亲跟周局长有过节,一个个支支吾吾不肯作证。
父亲火了,霍一下站起来:“不用别人作证,我再举一次!”他紧了紧腰带,又一次抓住杠铃。
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奔过去,想按住杠铃不让父亲再举。父亲大吼一声:“走开!”声落手起,沉重的杠铃再次被父亲举起来。
父亲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突,身子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但双手紧紧抓住杠铃,高高举过头顶。我和母亲站在父亲左右,双手向上,随时准备接住掉落的杠铃。那杠铃随着父亲摇晃,却始终不落!我蹲着身子,抬头仰望,看见杠铃上面是蓝天白云,一只孤独的鸟贴着白云飞来飞去。
裁判席上的周局长终于说:“杨永福,举起100公斤,第一名。”
父亲放下杠铃,软瘫在我的怀里。我和母亲都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肯作证的同事一个个低下脑袋,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
程刚
铭心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那时候她两岁半。为了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她的父母辗转千里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把她丢在公园里。好心人把她送进了儿童福利院。后来一位姓丁的女教师收养了她。丁老师的丈夫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唯一的儿子留学美国而后定居在异邦。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她从福利院领养了她。
丁老师对铭心比亲生女儿还娇惯,铭心在新的家庭里快乐幸福地成长,转眼就上了高中。那时丁老师刚从一所高中退休,因为是省级优秀教师,很多学校出高薪返聘她任教,她都回绝了。她只有一个愿望:专心培养铭心,不但要安排好她的生活,还要辅导好她的功课,希望她将来考上理想的大学!铭心很懂事,在学习上非常用功,希望将来能回报养母的恩德。
铭心读的是重点高中,成绩一直很优秀,是名牌大学的苗子。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铭心感觉总是困倦,开始以为是熬夜所致,后来身上一些部位出现了浮肿,去医院一检查,结果竟是尿毒症!这对于豆蔻年华的她无异于晴天霹雳。养母丁老师更是伤心欲绝,相依为命十几年,那份感情胜似亲母女,已非血缘可以阻断。丁老师打算倾其所有给铭心治病。这种病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换肾,在找到肾源之前,需要每周透析两次。丁老师愿意向铭心捐肾,医生不同意,说她年龄偏大了。有一天丁老师拿着一张《成都晚报》兴冲冲地来到医院,让医生看上面登出的一则新闻。报上说南充市的苟兴富大爷69岁了,毅然把自己一个鲜活的肾脏捐给了患尿毒症的女儿。医生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她的请求,不过要先进行血液配型,配型成功才能手术。遗憾的是,她的血型与铭心的血型不符,配型失败。透析的花销很大,当初丁老师夫妇供儿子在国外读书,没有攒下几个钱,很快资金上就捉襟见肘了。铭心的学校师生捐了款,市慈善总会给了一笔救助款,儿子从国外汇来一万美元,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肾源,为此丁老师四处奔波,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媒体记者来采访了,新闻一播,报纸一登,丁老师的真情大爱感动了全社会,铭心的病情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有一天,电视台打来电话,说有位女士愿意为铭心捐肾。母女俩很高兴,希望与这位女士见一面,当面表达感激之情。但电视台说人家不愿透露姓名,还不知配型能否成功,希望尽快去医院配型。在记者的陪同下,神秘女士去医院进行了血液配型,结果令所有的人感到欣慰:配型成功了!捐肾要进行信息登记,好心的女士恳请院方不要向媒体和外界透露她的真实身份,院方答应了她的请求。丁老师过意不去,再三恳求见神秘女士一面,在记者的说服下,她答应了。这是一位很和善的中年妇女,不过面容中透着一丝忧郁。她自称姓梁,四十六七岁的样子,外地口音,面相与铭心还有几分相似!丁老师千恩万谢,说一定给梁女士补偿,梁女士淡然一笑,说为了补偿我又何必隐瞒自己的身份?
见面之后丁老师反复思忖,觉得梁女士与铭心似有渊源,从长相与年龄上看与铭心的生母有些相符,莫非……丁老师内心一惊:铭心的生母找来了!此时社会上对梁女士也有种种猜测,结论与丁老师的想法大体一致。大家认为,梁女士当年抛弃了铭心,内心必定愧疚,怕遭社会指责,所以不愿亮明身份。如今铭心有难,出于骨肉情深,她才现身相助。如果真是这样,丁老师觉得当前也不便把事情挑明,以免大家陷入尴尬,毕竟先救铭心最要紧。对于社会上的传闻,梁女士始终缄口不言,这反而更坚定了丁老师的判断——梁女士就是铭心的生身母亲!丁老师喜忧交加,陷入矛盾之中。喜的是铭心终于有救了,直系亲属可是肾移植的最佳选择。忧的是梁女士若是提出认领铭心,那可如何是好?毕竟铭心寄托了她生活的全部希冀。
手术很成功。术后铭心与梁女士都恢复得很好。此间丁老师几次想探知梁女士的真实身份,都欲言又止。这件事她一直瞒着铭心,手术期间可不能过于激动。梁女士向铭心捐肾成功后,如释重负,不久就要出院了。丁老师沉不住气了,终于把心底的疑虑向梁女士和盘托出。梁女士听后淡然一笑,说我本来想临走给你留一封信,来说明我的真实情况,既然你这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也不再隐瞒了,毕竟一切都要结束了。
丁大姐,你是好人,铭心是个好孩子,你们永远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我不是铭心的生身母亲,也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打算捐肾是为了赎罪。我曾经是一位母亲,如果我的女儿活着,应该和铭心一般大。因为生的是女孩,丈夫很不待见我,女儿也不受宠。孩子六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我抱到小区诊所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当时丈夫在酒店接待客户,接了我的电话后,只是慢吞吞地说他很快就回来,不过一整夜也没见他的人影——他对孩子一直漠不关心,好像孩子不是他的似的。我又给婆婆家打电话,他们说小孩子感冒发烧,在诊所打打点滴就好,没啥大不了,结果一个人都没来。后来我和一位好心的邻居抱着孩子去了医院,一检查,孩子感染了急性肺炎,呼吸急促,咳嗽不止,脸憋得通红。我简直要急疯了!后来孩子出现抽搐症状,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挽留住她幼小的生命。婆家人拖延治疗,就是想要一个男孩。他们不惜牺牲我的女儿来达到目的,是何其歹毒!
我心里种下了仇恨,对丈夫的仇恨,对婆家人的仇恨!是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我得替女儿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