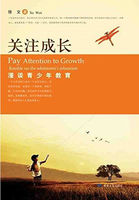那几个人一听,拽着姑娘就往深处跑。这下情况就很明了,遇见歹事了!
田蛤蟆一骗腿儿下了车,抬脚就追。
一边追一边喊,下意识要掏兜拿手机,结果头前俩人停下,直接把他扑倒在地,手机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只觉得脖子一热,拿手一摸,热乎乎的。
他躺在地上喘气儿,那俩大概是以为他死了,于是离开田蛤蟆,又开始跑。过了一分钟的时间,田蛤蟆挣扎着站起来,嗓子突突地往里灌凉气。他用手摸索着,觉得自己能把手指塞进去。
疼!但他仍然大声喊。
四下毫无人烟景象,田蛤蟆也不知道自己这叫声能不能被人听见,但他不敢停,他怕一停,姑娘就真没人救了。田蛤蟆头一次感谢爹妈给他生了一副好嗓子。
他模模糊糊瞧着前面的黑影,开始喊。
声传百里,音震四海。
直到他倒下。
事件的结局,是听田蛤蟆的邻居说的。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逢人便讲:“这儿,知道么,开了一大口子,跟风箱似的。现在给缝上了,但是精气神儿泄了,再也没声啦!”
“田蛤蟆!这份儿的!”可这邻居老拿手捂着脖子,到了我也不知道田蛤蟆到底是哪份儿的。姑娘被救了,因为听到田蛤蟆喊声赶来的,竟然有数十人,要这么算,那嗓子简直赶得上移动电台了。
据亲临者后来回忆,田蛤蟆倒在地上还一直在喊。
喊得不是救命,是救人。
还有人说这辈子没听过这么豪壮的声儿,像项羽力拔山兮,像张翼德喝断当阳桥。
说这话的人大概当过捧哏。
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都是从旁人口中得知的,只有田蛤蟆什么都没说。他也开不了口了。
或许开不了口,对他也是一种解脱。人们经常能见他托着收音机,四处溜达,但性子还和原来一样古怪,走到人前,突然把音量扭大,咧开嘴,无声笑笑,又走了。
我想,田蛤蟆的嗓门,大概也是老天赐下的才能,他拥有这嗓子,就是为了等待救人的机会,等救完以后,老天爷又把它收回去了。
我想,在那个夜里,在那片荒地里,一定满满都是嚷着救人的蛤蟆。
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视机又传来了声音。
还是一如既往的武打戏,刀剑碰撞,乒乒乓乓。
我问老板:田蛤蟆的故事,你信吗?
老板指指电视,笑着说,侠客不止在那里。
他走到柜台前,拿着笔在本子上开始写起来。我没有告别,安静走出了书店。
或许不久以后,还会有另一个人来这家书店,与他交换故事,讲一讲现实里的侠客,论一论故事里的英雄。
天才与凡人
要搬家了。
我帮着整理运输,把硬纸板箱子铺开在地板上,从箱柜倾斜出所有的旧物。
二十多年,搬了两次家。
离开小时候生活的纺机厂,搬到父亲工作的广播电台。之后又告别学生时代的电台大院儿,搬到现在居住的小区。每次迁徙,都像是做淘汰的减法选择。衣物、书籍、杂件儿、破铜烂铁,废布头短线绳,都要丢弃在原地,带走的都是舍不得的,新鲜的,或者至少对于现在来说有价值的东西。
从书柜的摆设里,找到了那把木刻的手枪。这是为数不多,从童年时代一直保留至今的东西。朽木头,从手枪柄的底部看,还能瞧见水渍浸透的烂渣印记。只不过用黑色的油漆刷了一次,于是显得不那么陈旧。
没有如今高仿作品的精细,更不是工厂流水化生产的产品。只有简单的手枪轮廓,用小凿子磨出的扳机,用锯齿慢慢掏空的枪管。我现在拿在手里,枪已经显得很小了。
当年拿在手中,正好合适。
制作这把枪的人,叫做赵小雷。
1988年出生。
制作这把枪的时候,他只有九岁。
赵小雷是我的童年玩伴,也生活在纺机厂的家属院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并不是买房的高峰,更多是依照单位安排,分房。所以邻里复杂,虽然亲热,但各行各业都有,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劳动人民。
赵小雷是小摊贩的孩子。
他爸是街头卖羊肉串的,起早贪黑,拖着碳筐烤箱,和赵小雷的母亲一起在外奔波。没人照料,赵小雷就成了野孩子。他瘦小,皮肤黝黑,眼睛却大,有神。没有爹妈照看的孩子,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是被其他小孩儿欺负得哭爹喊娘,要么是自己奋斗称王称霸。赵小雷却另辟蹊径,用发明创造改变了自己,并改变了其他孩子的童年生活。
他能用纤细的手指,折出各种样式的人物。
怪兽恐龙以及电视机里的奥特曼头像。
那些纸张,都是赵小雷父母裁下,做羊肉串铁盘子垫纸用的。
他能用小吸管和肥皂水,吹出各种各样的泡泡。
他能用泥捏小人儿,用我们提供的扑克牌搭起不倒塌的建筑。
那把手枪,也是他的作品之一。实际上,他制作赠送了许多手工制品木雕玩具,送给身边的小伙伴,有时候,连大人看了也啧啧称奇。
我一直认为,赵小雷是个天才。
他动手能力极强,家里的闹钟拆了再装根本不是问题。
我们小时候还有一门课,叫劳技课,大多是教一些折纸、绘画、雕塑、拼接的东西。一大本厚书,有些类似童年版的动手工具指南。那上面的赵小雷全都会,任何一项,他都能变成现实,对于我这种动手白痴来说,他简直是一个活在同龄人中的发明家。
这小子学习也很好。听人说,他甚至把许多高年级的理科书籍都借了来,读懂读通之后,才又还回去。
搬家之后,我们渐渐没有交集了,我只在上初中的时候,远远见过他一面。他戴着眼镜,低着头,在公交车上看书,厚厚的一本,写着变化的方程与符号,我瞅一眼就头昏脑涨,他却津津有味。
我一直觉得,他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看电视的时候,火箭发射,建筑建造,科研发明,任何一个高科技水准的东西,总能让我想起赵小雷。
啊,他以后,会成为这么厉害的人吧。
这是我从不怀疑的。
他的天分,早在幼时就已显露,听说到了高中,参加了几次竞赛,还有老师推荐他保送之类的事情。
不过,所谓的天分,或者天资,是需要机会和舞台的。赵小雷的天才,或许是没有机会施展了。
他的父母出摊,因为天黑路滑,被一辆车迎面撞上,夫妻双双重伤。这是一个俗套,而听起来又很悲伤的故事。
再后来,都是从旁人口中听来的了。
“那孩子啊,挺可怜的,可惜那么聪明,也不能去上学了,自己出去赚钱养家。”
“能干什么?好像是做了学徒,后来又出摊卖水果之类的……”
“哎,可惜可惜……”
之后,便连这样的惋惜之声都少了,赵小雷就渐渐泯灭在茫然大众芸芸众生之中了。
那把手枪,我一直摆在家里。看见的时候,总会想起赵小雷。
这个世界上如同他一样的人,还有许多。天才的展露,或许除了天资之外,更重要的,却还是滚滚红尘能够为他让出一条道路来。
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也曾遇到过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
冬天,北大的三教暖气很足,自习的学生常去那里。我也是其中一个,因为备考,所以起得很早,然而我却发现,教室里常常已经有人了。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穿一套蓝灰色工装,头发梳得倍儿干净,戴眼镜,眼镜底子厚成酒瓶。他趴在桌子上,身前身后,左手右脚,全堆着报纸本子纸张算式薄,几乎把整个人都埋住了。不管是上课下课,还是人来人往,他都不带抬头睁眼瞧的。右手持笔,不停在纸上写写画画。
偶尔瞧一眼报纸上的数字,沉吟良久,再度开始计算。
我一开始见到这人,以为是某个数学老师因为没有地方,偶尔来此做研究的。后来发现不对,他几乎把一天的时间,全都耗在写写算算上了,除了吃饭和偶尔上厕所,几乎不挪窝儿。
后来,趁着他去厕所的时机,我偷偷跑到他桌前瞄了两眼。发现报纸只有一种,刊登彩票中奖信息的“彩报”。
有相识的北大同学见我去他桌前观摩,于是问我,是不是觉得这人挺“神”的?
我点头称是。
同学说道,这人呐,是一“数痴”。嘿,我一听这名头,顿时好奇心起,赶紧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解释道:“这个人,其实还挺厉害的,我在高数课上遇到过他,他专门等在教室门口,下课以后,来问老师数学题。他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生,就是一高中生,但自学成才,对数字很敏感。”
“不光是计算上很敏感,直观感觉上也非常出色。”
“有学生跟他聊过,攥一把零钱,搁手里,他只要瞅一眼,立刻就能报上总数来,分分角角,一点儿不差。”
“记车牌号,瞬时记忆,也行。”
“只是这人呐,他做算术,不是为了搞研究,是为了挣钱。”
“怎么挣?全靠彩票。”
我这一听,立刻觉得不靠谱了。
同学觉察出我的神色,微微一笑,说道:“这人,已经有点儿疯癫了。你瞧着他干干净净,把自己拾捯得不错,其实脑子里的线已经断了,整个人都扎进数字里出不来了。”
我问,这是怎么弄的啊?
同学说,要真论起来,这事儿还有得一说。
在三教里研究数字儿的这人,名字叫付大平。
河北保定人,年纪差不多有快四十岁了,高中毕业,进京闯荡,因为他好动脑子,数学功底也好,所以一开始是在超市工作。后来头脑灵活,干活又认真负责,等积攒了些钱,就自己开了个小商铺。
这人一旦有了钱,就开始想着花了。
付大平的老乡中,有不少人爱好“卖彩儿”,也不贵,一次花几十块钱。
一开始,付大平不沾这个,可到后来,他也渐渐开始买彩票。
不知道是付大平真的对数字天生敏感,还是邪性,反正他买的彩票,经常中,虽然不是大奖,但几百几千的都是家常便饭。
这一下,他算是彻底来了兴致。除了开店,一天到晚拿着笔算数字模型。大约有半年的光景,终于被他琢磨出一组数字来,当天就买。一买即中。
一开奖,好么,一百万!
这一下,可要了亲命了。老付和他老婆欣喜若狂,本想着把中奖的事儿保密,却没曾想走漏了风声。
亲戚朋友蜂拥而至,纷纷借钱。招架不住之下,只得应允。就连他老婆,也动了心思。结果其实一目了然,借钱的一个人都没还,老婆则带着钱投奔相好了。
至于付大平,谁在乎他死活呢?
这人一旦逼到绝境,神经就绷住了,可人毕竟不是钢丝线,断了,就疯了。
老付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再中一次奖。中了以后,媳妇儿就会回来,亲戚也不再躲着了。
于是乎才有了这个守在北大三教,一天到晚研究彩票数字的“数痴”。
听完这故事,我感慨万千。
付大平对数字的天分,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要真说起来,确实是被这人世里的利欲熏心裹住了脚步。假如他能够认认真真地搞搞数学研究,是不是又有一番不一样的光景?
我不愿意去猜想,因为一旦做了设想,再和现在的他对比,就显得太凄惨了。
不要去做天才,天才脱不开俗世,会比凡人更悲惨。
年底的时候,我回了原来居住的那片老区。相熟的哥们儿,请我吃饭。
去了一家串儿店。不大,有二三十平方米,收拾得很干净。黑色的漆,红色的字,看着有种莫名的工业美感。
进里屋以后,发现桌子很有特色。所有的桌子都带接口,能几张拼在一起,而且不像普通的拼桌儿,不稳当,这里的桌子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严丝合缝。饮料杯子也不一样,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粘住的,杯子底部都带一个垫子,无论是泼是洒,都不会弄脏桌子。
我这瞧着稀奇。
哥们儿解释说,这店有意思吧,我老觉得这不像一串儿店,倒像是一个人的设计展览会。你要是有兴致,可以瞧瞧门口烤串儿的东西,瞧着跟高科技电影里的似的。
我听了这话,扭脸儿去看。
一般串店烤串儿都是碳烤炉子,拿一个大电风扇在旁呼呼地吹风。
可这家的烤串儿店不一样,像是装了个大棚似的,烟气从烤炉冒出来,又顺着管子通到底部接着吹进了炭炉里。
“不明白吧,我一开始也不懂。”哥们儿说。
“等后来问了老板,才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资源的收集与循环利用,副标题——论煤炭的充分燃烧。”
“我琢磨,这家烤串儿店老板,得是一高材生。”
我细细去瞧那正在烤串儿的店主人。他背对着我,但依旧能看出轮廓。皮肤黝黑,身体虽然瘦小,却看着精神。
门口有相熟的顾客,大声吆喝。
“赵小雷,给我烤好了,送楼上去啊!”
嘿!
一个烤串儿的天才,一个混迹尘世的凡人。
造不出火箭,咱们就玩儿火炭。
一样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