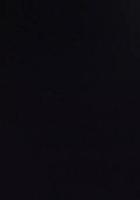就是那个睡了嫂子的小叔子。
具体的消息是我跟着我爸去吃场子的时候得知的。当时是去吃涮锅,席上有个刑侦支队的叔叔,是我爸的朋友。正吃着肉呢,他突然提到了前段时间发生在铁路大院的案子。
“那人是借着送烤串的机会进到家里去的,进屋的时候周卫国还在看电视,刚泡好茶,没喝几口。”
“你们都想不出周卫国是怎么死的,嘿,像是跌了一跤。”
“那脑袋砸在地板上,面朝着地,背朝着天,噗……”
“就像这一样。”他拿筷子指着红油锅和里面沸腾的肉。
尼玛,刑侦的叔叔就是口味重,我顿时觉得自己吃不下去了。
我爸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话。
周围人都没听清楚,但是我听清楚了,是一句拳谚:
侧起腿苏秦背剑,打英雄面落黄沙。
胡子刘是不是英雄,我不知道。
但是周卫国肯定不是。
胡子刘也死了,遗体出现在铁轨上。
从北京发往西安的列车把他碾成了两截,不过据说血流的很少,身上还是干干净净的。从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遗书,上面坦白了自己杀人的事实,另外还提到了怎么处置自己的遗产。
所有的所有,都给了打他闷棍的小子。
再一次和我爸对饮,我们很罕见地没有聊国家大事,而是把注意力扯到了胡子刘的身上。
我问我爸,你说他这么做值不值?
我爸说不知道。
我说,他杀人犯法,是个混蛋。
我爸说,世界上明知有法却无法维护的事儿太多,这是无奈。
我说,他到底喜欢那个女的么?
我爸说,喜不喜欢,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听说那个女的帮了老刘很多,最初老刘开店的钱,大部分都是向她借的。或许是喜欢,或许是报恩。
或许就是单纯地打抱不平。
我和我爸聊了许多,如果胡子刘没有学过武,不是一个普通乘务员,会不会对他邻居的帮助更大。但是这很明显是个悖论,如果他生活的层次更高,那么也不会遇到那个邻居,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侠以武犯禁,这句老话确实有道理。
胡子刘其实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莽撞地闯进我的生活里,带着百年千年前的刀光剑影,然后身死。
他不是好人,但是我很羡慕他。
聊着聊着,我和我爸都喝多了。
到最后,都不再说话。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独行万里为曾经一诺的男人。雄鹰只能飞翔在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里,振翅也飞不出小小屏幕。豪侠仅能活在雪夜醉酒后的呓语中,酒醒后壮志不复。利剑唯有悬于无人问津的博物馆里,即使你拥有了它,又能刺穿什么?
我爸帮着他的老同学办了葬礼。
我去了。
胡子刘教的那个小子也去了。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腰上扎着功夫带,咬着牙,眼睛红红的。
这小子仰着头,像是怕什么东西从眼角掉出来。他低低地吼着一段秦腔,声音像极了胡子刘。
好儿郎起五更习就武艺,离爷娘求功名光耀门楣,出门去只怕我宝剑不利,不封侯我不归桑梓之地。
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雪,雪落在那小子的衣服上,像是开满了花。
骆驼祥子
2014年,春和景明。
和酒肉朋友相聚增光路巫山烤鱼,食鲶鱼一斤,饮国人称之马尿西洋称之啤酒的玩意儿八瓶,飘飘然不知身处何世。
酒兴虽好,但我酒量不佳,饮时如长鲸吸百川,吐时如莱辛巴赫瀑布大决战。被兄弟扶出饭店时,恰有夫妇二人携孩子路过,见我面前砖地一片惨状,戚戚然不忍直视。男女使出左右开弓手法遮住孩子双眼,犹如八点档家庭连续剧突然蹦出了不良镜头。
兄弟要为我招手拦车,但司机们瞧见我的模样,全都脚踩油门儿迅速驶离,只留下我且吐且珍惜。就在我呼哧带喘交代后事,让兄弟们明天记得帮我把一到付的快递费给交了的时候,终于有一聪明的朋友,拿出二十元大钞利诱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这二十算小费,车钱咱们另付。您将就将就,捎带手拉他一程。”
兄弟低首垂腰,两肩抬起,双手将钱奉上,另有几人将我抬起,仓促间要把我塞进车里。
司机师傅摇下车窗,只见这人身材健硕,宽肩,短发,鼻梁高耸,眉眼深邃,如同日本影星高仓健先生。他并二指将钱轻轻拈起,置于上衣口袋内,然后沉声吐气道:“不忙。”
司机师傅打开车门,轻轻挥手,如同电视里到访我国的国际友人下飞机时的样子。朋友们慑于其气势,如潮退散。
他缓步走到我面前,左腿前曲半蹲,伸右手,用拇指按住我手掌虎口处,狠狠按下。我连声呼痛,他却沉默不语,周围人因不知深浅,只得按兵不动,直到两三分钟后,他才把手松开。
我摇摇晃晃站起身,伸胳膊蹬腿儿,发现自己胃不酸嗓不痛,好像一口气再吹瓶都不会费劲儿了,于是赶紧对着司机师傅千恩万谢。
司机师傅神色淡然,轻声说,年轻人喝酒要注意身体,这次学着点儿,那地方有个穴位,醉酒以后按了能止吐。
有哥们儿竖大拇指,笑着问道,师傅,敢情您还是业余老中医?
司机师傅掏兜拿烟,我赶紧狗腿子似的拿火机给他点上。这位深吸一口,然后闭眼缓吐烟圈,像是几千年前尘往事全都混在这一口里了。
站立良久,他才用标准播音腔说道:“这世上司机本不会按摩,在车上吐得人多了,自然就有了绝活儿。”
北京的哥大多都藏有一手绝活儿。
晚报原来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述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故事。里面提到一位董师傅,他等活儿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出租车练倒立,双臂撑着车门,两腿笔直悬空,能坚持一分多钟,不管风霜雨雪,天天都练。五十多岁的人了,一身腱子肉,参加健美比赛还得了第二名。
媒体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偌大的北京城,多少藏龙卧虎之辈,全猫在东风雪铁龙里了。光是我亲眼见识的,就有那么几位。
有一回,我从北外门口拦车,一钻进去,就被车内的布置吓住了。
车前厢的位置摆了密密麻麻的一大摞照片,全是司机师傅和外国友人的合照,黑红白黄,老中青妇幼,应有尽有。
“去哪儿啊?”司机头也不抬地问道,我仔细一瞧,人家手里拿着英语词典背单词呢!
路上聊了会儿,的哥跟我说,他的业余爱好就是英语,从高中课本一直学到大学英语,自己还拿网上的考试卷子做过一遍四级考试题。
我问他怎么想着学英语的?
司机师傅说,咱北京好歹也是国际大都市啊,不会点儿洋文能行吗?另外这也是提高自身附加价值的方法。打一比方吧,你要是去了美国,你是拦一个说hello的车,还是拦一辆说你好的车?我呀,这是给老外们创造一种回家的感觉,让他们觉得温馨,下回还坐我的车。
聊到尽兴处,司机师傅还现场为我背诵了几段英文原着,怎么说呢,那口语和gala乐队唱的“桑嘚死扛硬爱旺那拽卖卡”有的一拼。
“我要上了大学,这至少是个六级水平。”他说。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没错。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司机有一千种绝活儿。
但说到底,所谓的绝活儿也都是日常技能的变种,和普通人比起来,没什么太多了不起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北京的哥,还真有两种其他人不会的技能。
这两种绝活儿,其他人哭都哭不会。
首先要提的,就是“听声辨位”。这听声,指的是乘客口音,这辨位,则指的是乘客打哪儿来。
北京的人流量这么大,到底哪些客人司机喜欢拉,哪些客人司机懒得拉,这上了车兜不兜圈子,黑不黑点儿钱,都有学问,关键就在这“听声辨位”上。就拿西客站来说吧,京津冀地区的客人,其实是司机们最不喜欢的,挨得近跑不远地方熟,想蒙你都蒙不成。越是往南,司机越是喜欢。外地客,不知道路,从西站出发,绕着丰台跑一圈再回海淀,估计乘客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平舌翘舌不分,好,这是一外地客,能拉。儿化音用得标准,就算不是本地人,至少也待挺多年了,赶紧滚蛋,别耽误我挣钱。虽说是小小口音,可钻进司机师傅的耳朵眼儿里,就能听出不一样的价格来。尤其是把“刘奶奶喝牛奶”说成“刘lailai喝流lai”的同志,这声音听着,简直是哗啦啦的钞票响。
早年间,北京出租车很不规范,不打表打假表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载客抢载客也都不稀奇。虽说整顿了这么多年,可老毛病一时半会儿还是改不了。北京的各大长途车站,都有一大批“听声辨位”的高人,等着拉冤大头的活儿呢。
平头,制服,半开着窗户,把耳朵凑出来,遮遮掩掩听着。“哎哟,这是一天津人,算了算了,这活儿不拉。”
这样的明显是刚入行的新人,顶多判断下乘客大概的地方,成不得气候。
戴墨镜,神色不屑,半倚着车门,拿腔拿调喊着走嘛您,等人真走近了,又闭上嘴巴,半侧着身子,专用耳朵对着。
“嗯,湖北的,武汉的,能行。”
这号的,算是步子踏进修行的门槛了,将来定有大作为!
至于真的高人,那都不显山不露水的藏着呢。一大群司机,围着他一人,这是司机当中的带头大哥。上了年纪,肚腩突出,皮带卡在胸口,戴一蛤蟆镜,意气风发,到处瞎侃,讲自己走南闯北,西方哪个国家没有去过?
等乘客走近,突然挥手,万籁俱寂。
耳随声动,如幡随风动。
脚步渐近,先伸一指。
“四川!”
周围散坐的后进司机,有的轻声吐气,为自己猜中答案暗暗叫好,有的垂头丧气,表明还有待学习。
司机大哥却不为所动,闭眼,屏气,凝神,静听。
每个字儿的韵尾,每个音的抖颤,都在掌握之中。
再伸一指。
“成都!”
这一次猜中的人更少了,余下的人惶惶不安,眼神偷瞅着司机大哥,又倏忽飘至乘客处,显示出内心极大的不自信。
还有最后的考验。
司机大哥摩挲着手上保温杯的盖子,动作轻柔舒缓,但此时此刻他的全部精神却紧绷着,像走在钢索上的人,底下就是万丈悬崖!不断地有司机跌坐在地上,满脑门子的汗,听不出来!真的听不出来!这最后一步,再也听不出来!
司机大哥的额角开始沁出汗珠,一滴滴向下坠落,跌成八瓣,晶莹剔透。
这是一场较量,乘客与司机间的较量。
咳嗽声,呼吸声,甚至那未从喉咙里发出的微小之音,全都聚在司机大哥的耳朵里。
突然,他笑了,咧开嘴,喜悦,发自心底的喜悦。
“这个活儿我拉了!”他低声说,再伸出第三指,顾盼左右,除了司机大哥之外,早已无人能猜出最后的答案。
“金牛区的!”
常听人们说,要做好北京的司机,功夫不在开车上,而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耳朵上,指的就是“听声辨位”。
另一个,则在嘴巴上,那就是说话的艺术了。
北京司机能侃,这事儿连奥巴马都知道。可要是把的哥的嘴上本事真当作他们有学问,这就确实有些夸大了。乘客多,见识多,哪儿的消息都能打听一点儿,自然说话的面儿就宽了。今儿拉了一小姐,抱怨哪儿哪儿又严打了,嗯,下回司机就能侃北京治安治理问题,还能给单身男乘客,提供点儿信息补助。明儿又拉一公务员,讲谁谁又被查处了,嗯,这下又能和其他人说说中国的政治问题,贪污腐败问题。
枯坐车中,再加上北京老堵的路况,没人挑头儿说话,确实难堪。
所以司机师傅们往往起了个活跃气氛的作用,一来是缓解压力,二来是调解情绪,打好关系,多收个一块钱,乘客也不计较。这其实是司机的本分,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本事。
但能把本事变成艺术的,这就少了,打了这么多年车,我就碰到过一个。
这个司机姓谢,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活儿,我拦他的车去大悦城,上车没多会儿就聊开了,谈天说地,风趣幽默。我常坐谢师傅的车。我发现他很会和人聊天,就像是三孔插头正好插在三孔插座里。
他简直把普通司机的侃大山变成了一种比央视煽情节目还要艺术的活动。
在我无数次香烟的贿赂下,他终于吐露了如何与人交谈的诀窍。
“你要明白,你对话的那个人,究竟属于什么?”谢师傅低声说道,他的嗓音华丽,如同童自荣老师配音的佐罗。
“就像是你要卖梳子,绝对不会卖给一个秃子。”
“女乘客,一定要先观察,如果是闺蜜之间或者男女朋友,不要插嘴,他们自己会制造话题。你要做的,就是变成空气,隐藏自己。假如是单身女乘客,一旦她掏出手机来,你就要立刻闭嘴,因为她的动作表明在抗拒对话,不要强求。”
“至于男性,那就好办多了。”谢师傅笑了,像是西点师把一个巨大的蛋糕摆在食客的面前,带着职业般的自豪。
“政治和经济,这是男人的核心。”
“抛开这两个话题,还可以有针对性地说说。”
“白领、IT男上了车,那就狂骂公司老总,说他们没人性,不知道体谅员工。再拐弯抹角地夸夸老罗,说只有有情怀的公司,才值得人们奉献。”
谢师傅声音一顿,把头扭向我,对我说道:“至于你们年轻人嘛,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天生的听众。骂领导、骂制度、骂学校、骂企业,什么都骂,你们呐,都是真朋克!”
服!真服!
一张嘴,上下俩嘴皮,磕巴一下就能出音儿,这谁都会的,偏偏只有谢师傅把说话的本事真正琢磨透了。
但说到底本事都是拿日子磨出来的,从早年间的黄面包再到夏利,又从夏利折腾到雪铁龙,谢师傅已经四十有八,两边头发都白了。他说自己在这座城市里见过很多人,好的坏的都有,什么心思的都体验过,有上车就骂的,有上车就哭的,有求谢师傅往河边拉想自杀的。
都是活着呐!
谢师傅感叹道。
有一次他和我讲起他自己的日子,每天起大早,等活儿拉人,中午就在司机之家吃饭。那是一个专门针对的哥的饭店,虽然没什么好东西,但是十二块钱连菜带饭管饱。
司机容易得病,谢师傅说,这么多年,不知道得了多少毛病。
“后来连那地方都不行了,硬不起来。医生说和长期久坐有关系,另外杂七杂八毛病综合的结果。”他笑着说,“我老婆找了个男人,我和她离了,儿子归我,我挣钱供他上学。我儿子比我有出息!”
那一天他没多说话,但我总觉得他那时说的每个字比之前他讲过的所有语言都珍重。
像是金子一样,亮闪闪地发光。
当然,也不是每个司机都把技能点加在了聊天上。
原来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个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七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
这师傅姓廖,名一平,三十七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
当然,从面相上看,也是不善交际的那种。
驾驶座的左侧,摆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小女孩。但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
“来啦?”他冲我点头。
“嗯!”
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是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
后来,我们有了一次对话。
那天是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十一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寥天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
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么,能不能接一下我。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廖师傅问我在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
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拿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是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