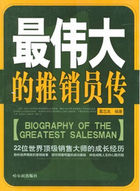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从此,钱学森在帕沙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安了家。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许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
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许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许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懑。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而跟台湾的“中华民国”关系密切的人物,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特工细细“研究”钱学森的行李
钱学森原本是“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然而由于“程咬金”金贝尔的横加干涉,事情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成了不准钱学森离开!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査扣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就已经注意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监控之中。早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査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査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査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査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査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于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而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査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二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美国联邦调査局毕竟还是有收获的。他们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甚至还发现一本“密电码”!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査局向媒体“放话”,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马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査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说,那些盖着“机密”、“保密”图章的文件,其实早已过了保密期。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原来,大约是美国联邦调査局探员的数学太差,没有见过对数表,以至把对数表当成了“密电码”!
不过,联邦调査局的最大收获,据说是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一张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JohnM.Decker)”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成为证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物证。但是,表上并没有钱学森的签名,而且也不能证明钱学森提交了这份申请表,在法律上又不足为证据……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号下午,美国移民归化局官员来到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所。移民归化局总稽査朱尔和稽査凯沙摁响了门铃。铃声响过,钱学森夫人开门,他们提出要见钱学森先生。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钱学森一眼就看出,这位移民归化局总稽査朱尔,就是半个多月前当他从华盛顿返回洛杉矶时,在机场向他出示“禁止离境”公文的那个官员。今天又来了,难道还怕我钱学森跑了不成?钱学森还真没猜错。原来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家中,一连7天待在家中没有出门。这让在钱学森住所周围监视钱学森行踪的移民归化局的探员们不放心了:钱学森该不是偷偷“跑”了不成?要是这样,上峰怪罪下来,谁也承担不起!偏偏这时又听到传言:有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看到了钱学森的汽车从美国越过边境向墨西哥驶去——钱学森“跑”了!这下使这伙监视钱学森行踪的探员们吃惊不小。尽管后来证实此消息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让移民归化局心存疑虑:这次没“跑”下一次呢!因此要采取切实行动,确保他不能“跑”所谓“切实行动”就是把他拘留起来,这样就保险了。
“钱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移民归化局官员对钱学森说。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政府的官员面前,钱学森明显处于弱势,辩白、抗议无济于事。
钱学森什么也没说,看了一眼身旁抱着永真的夫人,什么也没拿,跟着移民归化局官员走了。
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圣佩德罗湾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移民归化局的拘留所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移民归化局看中,扩建为拘留所。
特米诺岛拘留所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拘留所,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岛拘留所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押在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拘留所。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移民归化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
杜布里奇作为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前往拘留所看望特米诺岛上的移民局,钱学森曾经在此受审钱学森。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把他关在圣佩德罗的一个拘留所,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他有一个小隔间,一个完全舒适的房间。那不是监狱——但那是一个拘留所。他有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盏灯,一张床等等。但那样的拘留对他——对他的自负和自尊——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充分地效力于这个国家(他的确如此),却得到了这种对待……这最终使他变得非常愤恨。克拉克·密立根(Clark Milli kan)和我常常去探望他,并与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人作了交谈。
丹·金见尔深感震惊。他说:“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拘留,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拘留他是没有理由的。”移民归化局的行动让丹·金贝尔恼火——我觉得金贝尔是非常恼火,对移民归化局将他随口说说的评论如此当真,以及没有用其他方式劝钱(学森)不要走。也许丹·金贝尔认为我应该劝说钱(学森)不要走——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件。我去那里探访过钱(学森)几次,只是与他交谈,了解他的想法。他们后来让他假释回到了帕萨迪纳,但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洛杉矶郡。他的假释由克拉克·密立根监督,后者需要起誓一旦钱(学森)离开该郡就汇报。这是很受羞辱的经历。
杜布里奇的回忆表明,就连丹·金贝尔都对移民局拘留钱学森表示不满,而且丹·金贝尔明确地说,钱学森“并不是共产党人”。
夫人蒋英只是在释放前一天获准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钱学森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监控的眼睛紧紧盯着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笼罩。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移民归化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已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移民归化局收买,就会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移民归化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予以退还。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