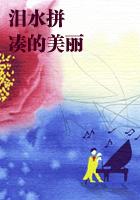李苑再见到谢敬之,已经是两周之后了,他穿了一身休闲西服,和与一家年迈的画廊老板商谈转卖的各项事宜。
他们在金玉楼的包厢门口碰到,还是谢敬之先打的招呼:“远远看着像你,没想到能在这碰到。”
李苑和他客气地寒暄,仔细打量他的神色和模样,依然是那一幅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的模样,不见一丝一毫地疲惫,他的头发又修剪过一次,酒店暖色系的灯光和富丽堂皇的装潢全都给他做了布景,一瞬间有种身处宫殿的错觉。
说了两句话之后,他忽然问道:“锦时还好吗?”
语调没有任何晦涩和低沉,好像在问候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
李苑点点头:“很好。”
谢敬之也点点头:“那就好。”
李苑忽然丧失了和他继续交谈的欲望,敷衍了两句便打算告辞,“再见”已经说出来,他却踟蹰,犹豫了一下,才问道:“她……我是说顾锦时……她有提到过我吗?”
李苑停住脚步,偏着头打量他,慢吞吞地反问:“你是希望提到过,还是希望没提到过?”
谢敬之没有回答。
李苑慢吞吞地笑了笑:“你手里还有她的手机吧,自己问问不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
谢敬之温雅的微笑:“对,不必麻烦。”语毕又向她点头:“我还约了人,有空再聊?”
李苑点点头,转身进了包厢。
晚上她给顾锦时打电话:“谢敬之最近联系过你没?”
顾锦时正抱着电脑看《汉武大帝》,闻言不由莫名其妙:“没有啊,好端端的他联系我干嘛?”
李苑心里咯噔了一声,又害怕自己语气不对被她察觉,急忙掩饰地笑了笑:“没有,就是有点遗憾,你说这好好一前途无限的青年画家,就这么被你放跑了,多可惜,你说是吧。”
顾锦时哼哼唧唧地笑了笑,半真半假道:“西服还在我这放着呢,要不要好歹给个准信啊,不要我就拿回去给我爸了!”
李苑默了默:“你这样对你爸真的好么……”
顾锦时咂咂嘴:“好歹一万四呢,扔了多可惜。”
李苑犹豫了一会:“其实……我今天碰见他了……”
顾锦时只觉得心脏咣当一跳:“他怎么样?”
“在金玉楼碰到的,好像是在谈什么生意,”李苑道:“看起来还不错,挺精神的,还问我……你有没有提到过他……”
顾锦时好一会没说话。
李苑又道:“我暗示他可以打电话给你,所以问问你他打了没有。”
顾锦时很镇定地笑了笑:“没有,”笑完又用咏叹调补充了一句:“陈宝国演的汉武帝真帅啊,和道明叔是一个火力级别的。”
李苑:“……你继续看吧,我挂了,再见。”
顾锦时笑着挂掉电话,手指在屏幕上婆娑了一会,调出微信界面,打了一条信息,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直接锁屏,把手机藏在枕头底下,继续看电视剧。
电脑屏幕上青春不再的卫子夫伸手抚摸心爱儿子的侧脸,说着绝望的台词,顾锦时眼睛盯在屏幕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手仿佛不受控制,摸出枕头下的手机,把先前删掉的字又重新打了一遍,犹豫很久,闭着眼睛点了发送:“你的西服还在这。”
谢敬之秒回:“明天要去一趟四川,正在收拾行李。”
顾锦时下意识的问:“去四川干嘛?”
谢敬之答道:“为一间道观画三清像。”
顾锦时发了个笑脸:“忘了你信道教了。”
谢敬之收到这条信息,愣了愣,手指摁在那个小表情上,发了好久的呆。隔了一会,顾锦时又发了一条:“什么时候回来?”
“要等画完吧,”他想了想,问道:“想要什么礼物吗?”
顾锦时很矜持地回复:“你看着带吧。”
谢敬之调出表情栏,也发了个笑脸过去:“对了,西服你记得送去干洗一下,我回来有一个仪式要出席。”
他说话的习惯,打字的速度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时代,是个完完整整现代人的模样了,让人一不留神就会忘掉他原本的来历,顾锦时赤着脚跑下床,打开柜子看了看他留下的四件西服,一周前她干洗自己的大衣时顺便洗了这些西服,此刻正套在塑料衣里,完全崭新的模样。
顾锦时拿手机拍了张照片发过去:“上周刚洗过。”
谢敬之看着照片,却被西服旁边不小心拍进去的半件大衣摄住了目光,他放大了那张图,仔细看那半个袖子和小片衣摆,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下,提笔画出了那件大衣在他想象中的模样,也拍了张照片给顾锦时发过去:“从没见你穿过大衣,是这样的吗?”
顾锦时把衣服拿出来,直接套在睡衣上,站穿衣镜前自拍了一张:“差不多,很有想象力嘛。”
谢敬之又提起笔,在那件大衣上补上一个女人眉目温婉的模样,盯着画纸看了很久,唇角浮上一丝单薄笑意,伸手将画纸折了起来,放进了打开的行李箱。
顾锦时那晚收到的最后一条信息是:“我睡了,明早要赶飞机,你赶快休息,记得吃早餐。”
“晚安。”
请谢敬之画三清像的道观坐落在青城山的密林深处,一开始还有石质阶梯,到后来纯粹就是山间小路了,一个很年轻的道士在前面带路,穿过树林越过小溪,走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
道观没有名字,只有简简单单飘逸出尘的“道门”二字做了扁,挂在外貌古朴的大殿外,说是大殿,其实也不是很大,标准的汉代建筑风格,青瓦灰墙,庄严肃穆之外,又透露着一丝闲适的气息,犹如隐居世外的老神仙,随意造的一处容身仙所。
“谢先生,就是这儿了,”道士笑嘻嘻地站在殿外,指了指殿里的莲台:“之前曾经供着三清像,不过年代久了颜色就剥落了,再涂又麻烦,干脆撤掉,换成巨幅画像好了。”
谢敬之立在殿前,向莲台行郑重古礼,又对那道士问道:“请教道长仙号?”
年轻道士很随意:“在下……啊不是,贫道姓季,上玄下贤。”
谢敬之只觉得额头上挂下三道黑线,陈郡谢氏笃信天师道,他自幼见过无数道长,无一不是仙风道骨,偏偏到此地之后,见的道士们一个比一个……不像道士……
偏偏又是有些道行的,半分怠慢不得,谢敬之微微欠了欠身,又问道:“先前曾经遇到过另一位道长,仙号玄殷,不知两位……”
“玄殷啊,同门同门,”季玄贤嘿嘿一笑:“就是他介绍你过来帮忙画画的,其实你来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你的档案,滨海画坛风头正劲的新锐画家么,哈哈,那个……本门比较穷……”
谢敬之闻弦歌而知雅意,很无奈地笑了一下:“道长多虑了,在下就是道家的追随者,能为道门画祖师像,是在下的福分。”
季玄贤顿时又把他领到一间干净的厢房:“委屈先生在这儿住两天,我们这吧和外界交流不是很紧密,你要是回去画,我们取画就不是太方便。”
谢敬之把行李箱倚着墙放好,向季玄贤颔首致意:“这儿就很好,容易静心。”
季玄贤喜滋滋地在他肩上很自来熟地拍了拍:“我就喜欢你这么上道儿的孩子,那你先画着,我先撤?”
谢敬之哭笑不得地把这位嘻哈道士送走,返身打量了一下这间厢房,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意料之中的……没信号。
他对着房间拍了几张照片,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卧榻,一张低矮的茶案,床边还有一张宽阔的木桌,应该是专门给他用来作画的画案,这些家具全部复古,使得整个房间充满了古朴的意味,谢敬之矮身坐在卧榻上,一瞬间仿佛自己依然身在谢府,这段时间的奇遇,不过是一个春秋大梦。
谢敬之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四个月,才完成那幅三清画像,他来时还在夏末,转眼已经快要入冬,道门在深山密林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就像住进了世外仙源一样,清晨早起,偶尔能遇到几个打太极拳的道家子弟,有时与他们坐而论道,总能受益匪浅。
他在宣纸上用端正雍容的隶书写,倘若你在……
季玄贤来取画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仿佛在品鉴这四个字所用的书法一样,表情一点一点凝重起来,斟酌着问道:“贫道冒昧问一句,这个‘你’,指的是……”
谢敬之和他一同看着这四个字,轻轻摇头,答道:“我也不知道。”
季玄贤叹了口气:“不知道谢先生是否还记得我那位同门,玄殷师兄?”
谢敬之疑惑地点点头。
“那么他应当告诉过你,假如你还能遇到我,说明你的命盘有所偏差,你过得并不是十分如意”季玄贤犹豫了一下,道:“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谢敬之反映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饶有兴致地追问:“不知道长会如何助我?”
季玄贤没有回答,却问道:“你对你现在的生活,可还满意?”
谢敬之莫名其妙地点头:“还算满意。”
季玄贤皱起眉,自言自语道:“不应该啊……”
谢敬之继续莫名其妙的看他,季玄贤在厢房里来回踱步,踱几步就扭头看谢敬之一眼,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还时不时在手指上点几下,不知是在卜卦,还是做什么。
“玄贤道长,您这是……”
“既然我们能相遇,那么我便履行我的职责好了,真正的选择权还是在你手上。”季玄贤又站回他面前,做了个深呼吸:“谢先生,如果你现在能回到你的时代,你愿意回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