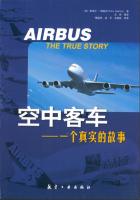谢敬之不高兴她总拿过去当由头,若有若无的呲他,当下一个倾身过去,捏住她的肩膀将她顺势摁到在地板上,两人鼻尖相错,呼吸缠绵。
顾锦时被谢敬之如此狂野的行为镇住,饱受惊吓地瞪大眼睛,连挣扎都忘了,谢敬之看进她的眼睛里,低头贴着她的耳朵低声道:“你不是总提醒我,要遵守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么?还是我那样问让你不好意思回答,所以试图插科打诨地蒙混过去?”
他半长不长的头发从背上滑下来,落在她面颊脖颈上,低低的吐音带着温热的气息,喷在她耳后,像带了颜色一样,很快染红了那一片细腻的肌肤。
谢敬之只是想逗她一下,没指望她能忽然醍醐灌顶地想通什么,见她一言不发,又笑了一声,才慢悠悠地撑起身子,打算从她身上撤走。还没付诸行动,就听顾锦时大喝一声:“别动!”
谢敬之被吓住,立刻停住动作,伏在顾锦时身上,提心吊胆地沉默一阵:“怎么了?”
顾锦时躺在地上,表情严肃地看着他:“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有亲密接触恐惧症?”
谢敬之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啊?”
顾锦时道:“我不能接受别人和我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不然就会全身不舒服,起鸡皮疙瘩。”
谢敬之“哦”了一声:“所以呢?”说完忽然觉得不对劲,低头一看自己正趴在人家身上,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面皮,手臂一用力,眨眼间就已经站起来,端端立在顾锦时身边五步远的地方,特别羞赧地一低头:“抱歉……我并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毛病……”
顾锦时慢悠悠的爬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其实刚刚谢敬之将她摁在地上的时候,她特意留心了一下自己身体上的反应,却发现……果然没有任何抗拒的意思,甚至连别扭的感觉都没有。
当年还和人渣谈恋爱的时候,人渣逮着机会就对她动手动脚,那段时间她忍得简直生不如死,最后人渣还特别不满意地说她,“你是不是性冷淡啊”。
老子哪里是性冷淡,分明是你不对老子胃口。
谢敬之见她没说话,以为姑娘正在气头上,于是更加愧疚:“是我冒犯你了,任打任罚,全随你意,你不要生气了。”
顾锦时咳了一声:“我并没有觉得……你冒犯我。”
谢敬之猛的抬头,看了她半晌,发出一个茫然地单音节:“啊?”
顾锦时心里天人交战了好大一会,终于抬起头,对着他嫣然一笑:“不如……我们来试一下?”
谢敬之继续茫然:“什么?”
顾锦时作为一个几年没谈过恋爱的文艺女青年,本质上还是一个脸皮薄容易害羞的姑娘,现在能厚着脸皮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实属不易,结果听这话的人居然还没有听懂!这简直太考验人的脸皮了,而顾锦时在这一方面的脸皮又属于经不起考验的那一种,当下又咳了一声,站起身,左顾右盼道:“没什么,这个碗是你刷还是我刷?你刷我就去睡了。”
谢敬之直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皱了皱眉,又问了一遍:“到底是什么?”
顾锦时觉得自己脸上快要烧着了,强装镇定,柳眉倒竖道:“都说了没什么,问什么问,你画画去吧,我去刷碗。”说完一躬身,直接端着碗进厨房了。
谢敬之看着顾锦时的脸慢慢变红,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满头雾水地执起笔,一边思考一边无意识地下笔,等回过神来的时候,纸上已经又几个字跃然于上,“不如我们来试一下”。
试一下,试什么?
这边顾锦时已经默默把剩下的面条处理掉,洗洗手准备睡了。
路过谢敬之身边的时候,她扭头看了一下正在盯着宣纸的谢敬之,然后直接看到那句话。
我们来试一下,后面还跟着一个墨水点。
好不容易降温的面颊又开始蹭蹭的发烧,顾锦时站在谢敬之身边,觉得她似乎应该说点什么,于是做了一组深呼吸:“那个……”
谢敬之从愣神中被惊醒,猛的打了个哆嗦:“怎么了?”
顾锦时被他如此大的反应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倒退一步:“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吓死我了。”
谢敬之伸手将宣纸盖上,又镇定下来,轻轻一低头:“抱歉,你准备睡了吗?”
顾锦时摆摆手,没回答他,反而问道:“你干嘛呢这是。”
谢敬之很促狭地笑了一下:“参悟天机。”
顾锦时牙一咬心一横:“……你不用参悟了,来我直接告诉你,这是一句省略句,具体省主语还是省定语我也不太清楚,把它照原样扩充起来,就是……”
“什么?”
“不如我们来试一下,你来当我现男友怎么样?”
谢敬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没答话,只慢慢挑起唇角,笑容越来越大,眼睛随即闪闪发亮:“现男友?”
顾锦时用强大的心理素质忍着满腔羞涩点头:“现男友。”
谢敬之抿着笑意,又问了一句:“不是丈夫?”
顾锦时终于掌不住低头笑起来:“你想的美。”
谢敬之抬起手,轻轻放在顾锦时肩上,顿了一下,又绕过她的脖颈,抬脚向前走了一步,微微俯下身,动作轻柔地拥抱她:“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拥抱你?”他从她耳侧移到面前,与她额头相抵:“还是,亲吻你?”语毕不等她回答,直接封住了她正欲开口的唇舌。
灯光仿佛蓦然温柔,落地窗外万家灯火流动成斑斓的银河,顾锦时闭上眼睛,睫毛如同颤抖的蝶翼,谢敬之没有阖眼,这么近的距离之下,她每一根睫毛,甚至眼皮上一些细小的血管都清晰可见。
他忽然觉得安心,于是也随之闭上眼睛,视野一片漆黑,别的感官功能却被发挥到极致,他听见下水管中细小的水流声、冰箱压缩机嗡嗡的运转声,甚至窗外小区的绿化带中,不知名的小虫为盛夏唱出的愉悦叹歌。
仿佛身上分散开无数的触觉,铺天盖地弥漫了这个空间每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感知所有平时被忽略掉的细微变动,带回来的每一个信息,却都刻着顾锦时的名字。他无意识的用舌尖描绘她樱唇的形状,描绘她丁香小舌的形状,眼前的黑暗越来越浓,就像品尝了五石散,有种瓦解所有斗志的迷醉之力。久而久之,黑暗之中又仿佛蓦然撕开了一角崭新的布景,他看见建康城外那一处常与知己好友曲水流觞的桃林,蓦然盛开一树夭夭桃花,刹那间三月芳菲胜放,充斥了整个瞳孔。
何彼濃矣,华若桃李,他想起那天在博古今中为李苑和章亭画的那副仕女图,题在画上的那句诗,忽然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羞愧。没有饮过玉液,便觉得天下酒都是琼浆,没有见过美景,便以为任意山水都可作画。
因为亲密接触恐惧症,顾锦时在接吻这一方面技术基本为零,她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不一会便觉得大脑缺氧,手指下意识揪住随手能揪住的衣角,紧紧攒在手心里,渐渐又觉得,因为缺氧,连这一点力气都使不上了。
谢敬之在她因缺氧而死的前一秒结束了这个漫长又快速的亲吻,他又抵住她的额头,薄薄的唇微微张开,颜色鲜艳湿润,颜色浓到极致,仿佛开到极盛的盛世牡丹。顾锦时盯着这一小小的美景,忽然开始微笑:“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薄唇的男人最无情。”
谢敬之很浅地微笑,又把头俯到她颈窝里,语调温柔:“建康城南郊有一片桃林,是一位道长栽下的,先前他还在建康时,我经常去草庐寻他,听他讲道,后来他云游离开,我也常常独自过去,或与一些交好的世家子同游。”
顾锦时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呢?”
谢敬之低低地笑:“方才我忽然觉得特别遗憾,倘若我们是在一千五百年前遇到,我就可以带你去看那片桃林,道长走时埋了一坛桃花酿,说是送给我的一份大礼,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在七年之后才能打开……”他说着,忽然猛的站直身子,表情无比震惊:“七年……原来是这个七年。”
顾锦时又被他吓了一跳,条件反射性的就要往后跳,谢敬之却揽住她的腰,表情似悲似喜,眸中神色复杂,低头看了她一会,终于畅快地仰头笑出声来。
顾锦时心里顿时很紧张,而且这会才想起来她是在和一个艺术家谈恋爱,而且还是画画的艺术家,据说画画的艺术家精神都不是太正常,而且癫狂程度和成就高度成正比,梵高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谢敬之笑完,又低下头来看她,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满脸抑制不住的笑意:“你愿意陪我喝两杯吗?”
家里还有半瓶李苑据说是从波尔多酒庄带回来的上好红酒,是她二十六岁的生日礼物,顾锦时将红酒找出来,又洗了两只高脚杯摆在茶几上,小心斟上两杯,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谢敬之一直靠在餐桌边,微笑着注视她来来回回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