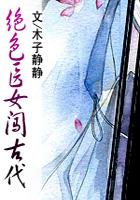可是哥哥还活着这件事,我不能告诉师父,也不能告诉二哥,因为这是欺君之罪。
本道姑生平,最恨这种藏着掖着憋屈的感觉,手心手背都是肉。
第三十七次叹息,我对师父道,“师父,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师父一把夺过我的酒壶,然后仰首便灌了个干干净净,白色宽袖拂动,酒壶再被塞回我手中时,已是空的。素日里,师父一向走知书达理温文尔雅路线,委实未曾像此刻这般豪饮,我纳闷道,“师父,难不成你也有心事?”
师父眨了眨凤眸,妖孽一笑,“是人,便皆会有心事。”顿了顿,他抬起头,目光遥遥看向天边的一弯上弦月,“阿鸢,越美丽的东西,往往越不能轻信。”
我善意提醒道,“师父,你也知道我文化不高,别说这么诗意的东西,假如你用金子比喻,我大抵更容易明白。”
师父,“……师门不幸。”
我,“……”
师父,“比金子,更美好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了想,片刻后道,“很多金子?”
师父的扇子已经敲到了我的头上,叹息,“蠢货不可教也。”
我,“……”
我深深觉得我和师父已经有了代沟,但听师父又叹息道,“傻徒儿,这世间最美的东西,自然是人心。”
“?”
“人心有多好,人心便可以有多坏。纯良的人心,比金子更易腐朽,更不能轻易相信。”
师父此话的意思,到底是让我信,还是不信?
丢下这样一句话,师父施施然离去,我对着一空壶,发起了呆。
皇后说,不对,是娘亲说……怎么就变成娘亲了呢?我一阵烦闷,抓了抓发丝,仔细回想着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那是三十四年前,正值西禹、吴国以及陈国三国联手灭掉南隋,国破当日,南隋皇后诞下小公主,那个小公主便是我的娘亲。那时,因为陈国上一任国主对南隋皇后有情,便以黑衣人身份救走了娘亲,并将其养在陈国将军府里。彼时,将军夫人已有一女。那女子便是当今太后。两个女孩年岁相仿,她们五岁那年,将军夫人病逝,先皇怜爱,将其双双接入了宫中抚养,未料阴差阳错,一个成了皇后一个成了太后。
娘亲并非自愿嫁给皇上,她早与青梅竹马互定终生,而这青梅竹马,便是我的父亲。嫁给皇上不久后,她便有了我,我的出生注定是不容于世上,娘亲让父亲带着我远走,对外宣布我难产而死。皇上暗地里下了圣旨杀无赦,表面上却过继了一个少年给娘亲,以示安慰,那个少年便是哥哥。
说起来,哥哥同样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娘亲要当今圣上的命,是为我为我父亲为我族人报仇,我无力阻止,可是娘亲需要我帮哥哥重见天日,而哥哥,却是害了二哥娘亲的凶手……娘亲想让我在大婚之日,在来参加婚宴的部分人酒中下药,普通的蒙汗药,这样,她便能争取到时间,与哥哥一起离开陈国,如若我肯出手相助,她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离开,而如若不,她们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后半夜,我趴在石桌上睡着了,迷糊中,似乎有人帮我披了件衣衫,总是梦见二月雪这件事,我已经见怪不怪。鉴于此,我发现,如果想要一个人很难将你忘掉,要么你插那人一刀,要么让那人插你一刀。
他坐在我对面,衣衫清冷,轮廓几乎能与月色重合,我哼了一声,“不是说了两清吗?你为何老是要跑到我的梦里来?”
“我来,是因为你需要我。”许久不见,他瘦削了许多,唇角勾起的弧度,是李九霄独有的邪魅。
他不是第二重人格的二月雪。
他是李九霄。
他步步紧逼,“阿鸢,你心底明明那般渴望亲情,为什么不肯正视,非要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才刚问出口,他笑的似是而非,然后那笑容渐渐变成了一个漩涡,很大很大的漩涡,我一头扎了进去,黑色几乎将我包围,良久良久,我睁开眼,这才发现自己竟站在了冷宫之前。
朱红的大门已褪色褪得发白,墙角到处挂的都是蜘蛛网,推开门,举目望去,到处是断壁残垣,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一切都透着腐朽的气息。院子里,草已有半人深,草丛深处,传来一女子喃喃的声音,我不由自主走了过去,那女子的背影好生熟悉,此刻,她正在拼命的往嘴里塞草。
我走近了,才听到她说的是,“好饿,好饿。”
可是那些草根本不能吃,我想上前阻止她,可是她竟抓住了一只青蛙,作势要朝嘴里塞,然而塞到一半,她忽然停了下来,然后傻笑起来,“咦,肉,是肉,要留给乖儿子和乖女儿吃。”
然后,她便抱着那青蛙,拨开草丛,疯疯癫癫朝宫殿内跑去。
“娘亲!”那声音,是皇后无疑,我捂住唇,不让自己哭出声音,“娘亲,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
皇后为什么会被打入冷宫?
我追进了宫殿内,灰尘呛得我几乎无法睁开眼睛,我捂着喉咙剧烈咳嗽了一阵,这才看清,地上竟躺着一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尸体上爬满了白色的蛆,娘亲跪在尸体旁,声音很轻柔,像是对待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辰儿,起来吃东西啦,你一定饿了很久吧,你看娘亲找到了什么?”
她像献宝似得,捧起那只青蛙,青蛙呱呱叫了两声,然后猛地一跳,从她布满各种伤痕的手里蹿出去,她立刻爬着去追,我哭着抓住她的手臂,不让她走,她奋力要将我甩开,我转到她的面前,哭喊道,“娘亲,是女儿啊!”
“女儿?”她咬着手指头,很用力地想,面目一瞬狰狞了起来,她忽然掐住了我的脖子,“你明明举手之劳,便可助我母子二人离去,为什么,为什么不肯?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咳咳!娘亲!”
有那么一瞬,我已不愿再反抗!是啊!我明明举手之劳,只不过迷晕几个二哥手下守城的关键将领罢了!
我原已闭上了双眼,可是忽然间,窒息的感觉消失了,勒住我脖子的双手不知何时松了开,我缓缓睁开了眼,娘亲向来温婉的容颜已变得几乎无法认出,可是那双眸子,却依旧温柔,她抚过我的脸颊,“娘亲不怪你,娘亲本就不该打扰你的生活,拿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去困扰你。阿鸢,娘亲从来都不后悔遇见你父亲,生下了你。”
“娘亲,我错了。”我扑到娘亲的怀里,哭了出来。
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从生下来便没有娘亲和父亲的感觉,孤孤单单,没人疼,没人爱,仿佛是凭空出现在这个世上最多余的人一般。逢年过节,别的小孩有父母买的新衣服,有父母做的好吃的,有父母陪着放烟花,而我自从八岁之后,只有飞鸾宫一个人坐在床头抱着膝看着窗外,幻想着父母何时会出现,帮我撑腰,抚平我的不安与难过。
许是梦里的太过悲伤,醒来时我的手都在抖。
诚然,若我不相信娘亲,不愿帮娘亲,我后半生都会在不安中度过。
人心有多好,人心便可以有多坏。这句话,不正是说我自己的。
翌日大清晨,我便拿着娘亲给我的令牌,寻到了长乐宫。
晨曦微薰,侍候皇后的许嬷嬷只道皇后昨夜一夜未眠,方才入睡,但她并未拦住我入殿内。熏香冉冉,烟雾弥漫,我莫名想起了昨夜梦中的灰尘,手指扯了帐子的一角顿时又放了开,眼泪差点落下,我多么害怕掀开帐子噩梦会成真。
庆幸的是,当我掀开帐子,那个我称之为娘亲的人,正安然躺着。
她睡得并不好,眉头蹙起,我轻手轻脚走过去,跪在床边。昨日,我还不愿喊她一声娘亲,可是一场噩梦过后,我却是生怕再没有机会喊她一声娘亲。
所谓亲情,大抵永远都是失去后方知珍贵。
“娘亲。”这两个字从口中吐出,很是生涩,但那些积聚了许多年的情感,仿佛终于找到了出口,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娘亲你醒醒。”
睁开眼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她眼底先是露出惊讶的情绪,然后是感动与喜悦。
“阿鸢,你终于肯唤本宫一声娘亲了。”
如若那时,我便知道,这一声娘亲的代价会是那般沉重,我一定宁愿自己有一颗天底下最坏的心,可惜世上永远没有后悔药。
二哥因公出差回来的时候,正是二月十二花朝节,家家都在祭花神,我在东宫里,闲着没事,便跟着那些老嬷嬷们一同,剪了五色彩笺,取了红绳,把彩笺结在花树上,谓之赏红。
我正垫着脚尖将彩笺绑在枝条上时,背后忽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
二哥?
我惊喜的回头,那抹紫色身影不是二哥还能是谁?这一刻的心情,简直比飘在云端还不真实!大抵多日不见,他又清瘦了点,定是这段日子太过劳累所致。于是我连忙对身边近日才熟悉起来的容嬷嬷道,“快去厨房熬个十全大补汤。”
“先煮点清粥,给太子清胃。”
“对,再去帮我做的薰衣草香囊也送来!”
“还有我亲手缝的衣服。”
“……”
容嬷嬷笑道,“太子妃,你紧张都快语无伦次了,咱太子啊,现在可不需要那些?”
我纳闷,小声道,“那太子需要什么?”
一旁的老嬷嬷们皆是笑得比菊花还灿烂,异口同声道,“太子妃啊!”
说罢皆风卷残云地离开现场,东宫的伙食果然好啊,养的老么么们都是健步如飞!
我一个人呆呆立在原地,二哥一步步朝我走来,我竟紧张羞涩得手都不知道哪里放,原来爱上一个人竟是这般感觉,任凭你一颗心如何汉子,见到他时,都会变得患得患失,半是甜蜜半是忐忑。
偏偏小十一笑嘻嘻道,“一日不见兮如隔三秋……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相思红豆,入骨相思君知否……”
这不正是我写给二哥的信!这些诗词,可都是我从小言上抄下来的,这种东西,自然只适合闺阁时悄悄说,眼下被他这般口无遮拦当着众人面说出来,我顿时囧成了包子,二哥却是淡定道,“十一,把东西放下,你先下去。”
小十一刚走,我便扑了上去,气呼呼道,“你竟然把我写给你的信读给他们听,以后我再也不写给你了!”
二哥哦了一声,然后很欠揍道,“你忍得住不写?”
我装模作样,“写,不写给你而已。”
二哥凶狠的吻说罢便袭来,“不写给我,你还想写给谁?又能写给谁?”
唔,俗话时候英雄难过美人关,但到了我这儿,却变成了美人难过英雄关,只要二哥一使美人计,我就没辙了。
久别重逢,少不了一番耳鬓厮磨,世间儿女,皆是难过情关。只不过,我没想到,用心如二哥,出门办公事的时候,都不忘忙婚礼的事,当他打开一个精致的玉盒时,里面竟然是……
见我呆立在原地,二哥忽然低头咬了口我的左耳,举止轻佻声音惑人,“不喜欢?”
本道姑当初是昏了头才觉得眼前这厮是君子,呸!恁好色了!我捂住耳朵,退后三步,故作镇定道,“嫁人嘛,有什么喜不喜欢的?”
“可是金线金丝做的嫁衣不多,既然不喜欢,那我赏赐给别人重新帮你订做一套好了。”
二哥作势要收起那盒子,我连忙扑上去紧紧抱住不送,笑得那叫一个狗腿,“嫁衣什么将就一下就好了,不用太破费哈哈。”
二哥忍俊不禁,“比起金屋,确实不破费,不去换来看下?”
我心事重重,抱着嫁衣魂不守舍去换了出来。走到一半,我折回头,认真问道,“其实……你现在对我这么好?以后会不会变心,比如说,我长胖了什么的?到时候你会不会抛弃我?”
天空万里无云,久别重逢,我的心底有头小鹿一直乱撞,此刻,他的表情很是玩味,捏了捏我的脸,半晌,才吐出一句很欠揍的话,“就算我想抛,也要抛得起来才行啊。”
“……”我气哼哼道,“你要是敢始乱终弃,我就……”
“就怎样?”
“就不嫁了!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本道姑要仔细考虑考虑。”
“哦,我没打算放弃森林啊!”
我,“……小哈,咬他!”
这男人太可恶了,也是,本道姑一向没心没肺,为什么要变得这般患得患失?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哈摆起尾巴汪汪叫了两声,然后屁颠屁颠跟我一起去试嫁衣了。
嫁衣虽是金丝金线做的,却不是很重,只是有点繁复,琉璃璎珞,五彩金丝,堪堪是千娇百媚的一件衣服。我完全不会穿,两个宫女一起捣弄,才帮我穿好。当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连我自己都被惊艳到了,这衣服肯定很值钱吧?莫名的,我的脑袋里又想起了那句诗词:银钗金钿珍珠坠,凤袍霞帔鸳鸯袄。
难道,在那段失去的记忆力,二哥也曾要迎娶我?
在我神思的时候,二哥已站在了我的身后,他揽住我的腰,“还有十多天就要嫁为新妇了,没办法看到你那一日的模样,大概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我拉起他的手臂,“你可以摸一摸,然后想象一下?”
他嗯了一声,然后手开始不规矩起来,我笑着拍开他的手,只见他的眉头忽然微微皱了起来,像是被我碰到了伤口一般,我连忙拉开他的衣袖,只见他的小手臂竟裹了层层布条,“这是怎么回事?”
这世间,能伤到二哥的人,不多吧?何况随二哥一同出去办事的还有阿大和阿二。
“二哥,你那日所说的对手,究竟是谁?”
“没什么。”
“你还不说是不是?不说我当真生气了?”
室内檀香冉冉,二哥抿唇沉默良久,才伸手抚过我的脸颊,“阿鸢,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记住,你生,我生,你死,我死。生死不离。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所以,你只需好好当你的新娘便是。”
二哥不肯告诉我,我只好去找阿大和阿二,他们说,二哥最近去追查的人,是活死人。所谓活死人,便是被一种药物控制了神智的人,目前尚且不知道这批人在何处,数量有多少,而且这种人的破坏力很大,剑刺不死,刀砍不死,因而即便只有几十个人的一个团体,破坏力堪比一个军队。
原来,之前二哥出去办事,便是去追查这批人的下落,可是这批人竟是走得毫无头绪,多次正面冲突之后,伤势过重最终不治而亡。
事情越发诡异,我找师父说了这事,发觉二哥竟也在同师父讨论这件事,二哥将那活死人的尸体带了回来,自己解剖之后,提取药物,让师父去分析,药物的成分,然后配置解药。
时间很快便到了三月初,眼看即将要到大婚之日,普天同庆,到底都是喜气洋洋,陈国的每个角落里,讨论的话题无不是太子大婚,而我整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尤其是娘亲,特地找了教习嬷嬷教导我为人妇之事,所以,很快便将那些烦心事都抛到了脑后。
嬷嬷们对于房事上的教导,是比较内涵的,哪像铁柱那般血腥。
嬷嬷们是直接给了我一本书名为《春闺幽梦》的书,每每有空,我便会正大光明坐在院子里品鉴上一番,小包子说,“娘亲,你最近好生好学了。”
我摸了摸包子的脑袋,“娘亲一直这般好学,不然怎会如此文采飞扬呢?”
包子好奇道,“那娘亲知道书里都画的什么?”
我淡定合上书,“是人世间各种姿势,哦,不,是姿态,内什么人间百态。”
阿四掩面抖腿泪奔而去。
小十一掩面抱头撞墙。
果真是……人间百种姿势啊……
可是包子太天真,他在国子监里,四处宣传,说什么他娘亲好学,天天钻研春闺寂寞什么……这回轮到我哭死在东宫李里了……国子监的太师个个面红耳赤,抚胸扼腕,“妖妃妲己在世啊,太子沉溺女色,实非名君,陈国不保啊!”
于是,翌日,弹劾我的奏折一本本堆得老高,二哥把我叫过去,一本正经,眉毛挑起,“春闺寂寞?”
我干笑了一声。
二哥又道,“是我让你春闺寂寞了?”
我又干笑了一声。
二哥冷哼了一声。
我连忙狗腿,“讨厌,这不还两天就不寂寞了么?”
二哥嘴角抽了抽,招手让我过去,狠狠折腾了一番,这才肯放我走。翌日我才听说,二哥当日直接在那些奏折上批了这样几个字,“本宫的房事,干卿何事?”
找相公,就该找有钱有权有优势的,啧啧,牛逼哄哄的感觉,多威风!
一时间,二哥为我造小金屋为我力排群臣之事,在陈国传得更加沸沸扬扬,直到我大婚出嫁的那一日,达到了顶峰。
三月三,龙抬头,宜嫁娶,宜生子。
半夜十分,小豆角便把我挖了起来,一群么么宫女们围着我,那叫一个百般折腾,脸上扑的粉估计都有半寸厚,又是胭脂又是唇彩,我偶尔眯开眼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妆容很是精致,美是美,可是二哥亲起来,不会有股淡淡的忧伤?
我把我的觉悟告诉小豆角她们,她们皆是喊道,“矜持啊!”
“矜持这东西,能吃么?能当金元宝用吗?”
“……”
上鸾轿前,我又给她们上了一课,论如何倒追。可事实上,我表面看似平静,内心早已像沸腾的油锅。
金丝金线与寒冰蚕丝织成的大红喜服,宛若云锦蔚蒸霞铺万里,炫目得让人无法移开双目。
尽管我额前别着凤簪,簪上的南海红珍珠一颗接一颗垂了下来,将我的视线几乎都挡住了,但耳朵听得见四周的吸气声。
小豆角扶着我,一步步朝东宫门前走去。师父一袭白衣,端得是绝世独立,站在东宫门前,将我的手递给一袭大红喜袍下马而来的二哥,鞭炮声,奏乐声不绝于耳。
那一刻,当师父将我的手递出去时,当二哥的手坚定地握住我的手,朝万千围观群众走去时,我激动得险些被长裙绊倒,嘴角不由自主扬起微笑,笑意还没维持多久,便有咸咸的泪水沿着唇角滑入口中。
师父说,“阿鸢,你们一定要白头偕老,永结同欢。”
我忽然想起,在我出江湖之前,师父曾对我说过,阿鸢,你命中注定有一大劫……看吧,师父果然是神棍,眼下,我正朝着人生巅峰走去,哪来的大劫?
而我,又是何其幸运,能遇见一个自己喜欢的,也喜欢自己的人,而且他又是那么优秀,有钱有权有才还将我放在心尖上捧。陈国嫁娶风俗,新娘必须要跨越火盆,可是二哥却是一把抱起我代我跨了过去,一片唏嘘声里,他低笑出声,“不到洞房那一刻,我是时刻都紧张你会出什么差错,都是些古老的仪式,在乎吗?”
我摇了摇头,认真道,“我也很焦急。”
二哥大抵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嘴角缓缓勾起,抱着我的脚步更加快了,三步作两步将我放到了九重鎏金的鸾轿上,一声起轿,顿时将气氛推到最高潮,道路两旁,客栈茶馆二楼,总而言之,能站人的地方几乎都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吆喝,所有人脸上皆是羡慕的神情。
仪仗煌煌,翠羽宝扇华盖,九重鎏金的鸾轿浩浩汤汤朝宫门驶去,而二哥,则骑着一匹红色的烈马行在最前方,鲜衣怒马,张扬不可一世,连双眸的白丝绸都换成了红色丝绸。
包子亦是一袭小蟒袍,骑着一匹小红马,跟在二哥的旁边,偶尔他会放慢速度,跟轿子走一块,一口一句娘亲今天真美,夸得为娘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沿途十里红毯,皆是红色玫瑰铺成,洒以金榍,行过之处,金光闪闪,香飘十里。两边树木,柱子之上皆挂了红绸缎,喜气扬天。拐过街角,我回头,终于再也看不见师父的身影,心底涩涩的,却也是欢喜的。
远处长空万里,碧色无边,宫城隐现。
约么半柱香时间,队伍终于到了宫门的正门,煊赫仪仗从宫门展开,远迎十里,宫人匍匐跪候道旁,内官各持礼器侍立在后,皇家护卫执仗阵列,近了,所有人皆是俯身行礼,三呼贺词。小豆角说,便是皇后,也不一定能有这般待遇,太子对太子妃简直没话说。我点了点头,“有生之年,总算感受了一把当人上人的快感。”
小豆角,“……”
一旁靠近的大臣,嘴角抽了抽,嘴巴扁了扁,这看家伙大抵就是弹劾我的言官吧,他刚想说什么,二哥忽然转过头,意味深长一笑,然后这伙人立刻将扁起的嘴扯成月牙,一个个笑得恁甜了。
进入宫门,前往金銮殿的路需要步行,且是九百九十九层阶梯,百官命妇全立于两侧,齐诵百子千孙经。二哥拉着我的手,让我小心脚下的阶梯,别被长裙绊倒。一旁的礼官一个劲嚷嚷于礼不符,这个环节不能牵手,需太子妃自己爬上去。我想了想,连忙作势要将手扯出来。
可是二哥却露出一个如沐春风的笑,“今日我若不这般做,往后指不定你们这群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一个劲儿弹劾你。姑且让他们看清了,你背后靠山是谁。”
明明如此温柔的一句话,配上二哥纯良的笑容,却是警告味十足。
丢下这句话,丢下一群叹息不已的老臣,二哥继续牵着我,朝阶梯上走去。
礼炮齐鸣,钟鼓齐奏,阶梯的尽头,帝后并肩。每上一个阶梯,我觉得世界变得不真实一分,九十九层阶梯,漫长而短暂,二哥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得不像话。我却觉得有些心虚,高处并肩而站的男女,一个是我的亲生娘亲,一个是二哥的亲生父亲……
终于,爬到了金銮殿前。
礼官高呼行礼,群臣百官齐刷刷跪下三呼万岁千岁,在一片吵杂中,二哥牵着我,跪在了皇上和皇后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
赞礼官唱颂,宣诵吉辞。
礼成,圣旨大赦天下。
自陈国有史以来,因为太子大婚,圣上便要大赦天下的,只有夜祁言一人,可见当今圣上对太子的宠爱有多深,尽管传言纷纷,皆言太子有逆反之心,盗窃兵符,欲谋害当今圣上。
而真正要谋害圣上的,是我的娘亲,可是这事,无论如何我都不敢去跟二哥说。想到这一点,我抓着二哥的手更加紧了。二哥不解回头,“怎么了,紧张?”
我摇了摇头。
二哥又道,“不开心?”
我一笑,“怎么会,我只是……太开心了。”
拜过帝后后,还要去拜见太后,以及去宗祠拜祖宗,一整套礼仪下来,委实能被折腾掉半条命,可是能当太子妃,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本道姑也很乐呵呀!午时过三刻,我终于被送到了宫中临时的宫殿,重新进行梳妆打扮,参加接下来的宫宴,大抵是去见一些他国来贺的使者,接受他国乃至朝廷元老的祝福。
大红的喜袍被换成了更加端庄大气红黑交加的束腰长裙,小豆角说,“这么一番打扮,太子妃委实有种母仪天下的风范。”
我笑眯眯,“真的?”
小豆角信誓旦旦,“比金子还真!”
“好,赏金子!”
换好衣裙之后,二哥便过了来。他委实不必亲自接我去参加宫宴。
我想到一千种和二月雪重逢的方式,却没想到,会是在这里,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二哥牵着我的手,在奏乐声里朝大堂走去,乐声停,一抹孤零零的掌声忽然响起,我循着掌声望去,一瞬间如遭雷劈。那一袭黑衣,神色冰冷中透着杀气的男人,不是二月雪还是谁?见我望过去,他忽然笑了,然后冰冷的神色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李九霄的邪魅与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