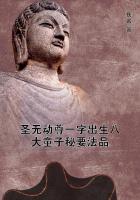二十分钟后,陆清浅盘着腿坐在左晨辉的副驾上,手里抱着一盒抽纸,勾着脖子低着头歇斯底里的哭。
左晨辉嫌她哭得闹心,干脆把音响的声音开到最大,遗憾的是仍旧淹没不了她鬼哭狼嚎般的哭声。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陆清浅突然从满车的纸团中抬起头,一本正经的问左晨辉怎么会去医院。
左晨辉心想总不能说老子在机场被你放了鸽子,心烦意乱的开着车不小心撞了人吧,于是别别扭扭的说了句“关你什么事儿”。
陆清浅一撇头,声音里带了浓浓的鼻音:“我说小左哥哥,你今天不会去机场接我了吧?”
“想得美吧你!今天起床没照镜子吗你?”
左晨辉心虚的踩了刹车,惯性震得没系安全带的陆清浅险些撞到前挡风玻璃上。
他清了清嗓子,胡编乱造:“我有个女朋友病了,刚刚送她来医院,没时间去接你。”
陆清浅“哦”了一声便转了头去看窗外的风景,车开进市区她忽然说:“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没想到你肉麻话说的这么溜。”
左晨辉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没搭腔。其实他自己门儿清很,刚才那番话半真半假。
陆清浅见他板着脸开车,吸了吸鼻子说:“要不咱们去佳期宾馆吧,我请你吃KFC。”
左晨辉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滞,脚底下松了油门猛地踩了刹车,汽车就这样突兀的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
左晨辉一手搭在方向盘上,视线落在浅灰色的路面上,额角的青筋跳动着,身体里的岩浆翻滚着,仿佛随时都会突破火山口喷涌而出一样。
他解了车门锁对陆清浅说:“你就在这儿下车吧,我待会还得回医院看看我女朋友怎么样了。”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拒绝陆清浅,并且编了个实在不怎么样的理由。
在他们这段持续一年的混乱关系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左晨辉舔着脸去约陆清浅,而在为数不多的陆清浅主动的时间里,左晨辉全都有求必应,就算他正窝在房里看盼望多时的欧洲杯决赛,也会毫不犹豫的关了电视买好condom去学校接她。
可是这次,他真的不想再这样了。
他怕受了伤的陆清浅会向去年中秋节那次一样,搂着他的脖子忘情的喊别的男人的名字。
看着陆清浅走远的背影,左晨辉愤愤的一拳挥向方向盘,手上的疼痛感只是一瞬,而心里那愈演愈烈的疼痛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纽约时,她和姜云瑾说:“我没什么太多要求,还是喜欢中国人,人白净一点,温柔一点,会做饭就成。”
那样的男人,大概就是刚才医院楼下的那个吧。原来她心里装的是那个男人,原来她从前整出的那么多次局子闹剧都是为了他。
左晨辉拿出手机翻了通讯录,找到了城北那个派出所所长的电话号码,拨通了还没等对方说话就劈头盖脸的问:“我是左晨辉,之前给陆清浅做笔录的那个小警察是不是叫陈皓?”
陆清浅下车的地方刚好靠近地铁站,可是她的包放在陈皓妈妈的病房里,现在全身上下连个钢镚都搜不出来。
她知道左晨辉生气了,虽然他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惯了,连生气几乎都不会对人大呼小叫。
左晨辉这人虽算不上温润如玉,但是在她那个冰山哥哥夏榆柏的衬托下,简直就是三月里最暖人的那阵春风。
陆清浅心知肚明,她在高潮时叫陈皓名字的那一夜左晨辉亦是生气了的,而且生了很大的气,否则他怎么会把宾馆的门摔的那样重?
去年中秋节那天晚上,陆清浅收到了银行的一条转账消息,陈皓把她寄给他妈妈的五万块钱医药费又还给了她。
她心烦意乱的站在宿舍阳台上吹着凉风,烦躁的删掉那条短信,只怪她从小爱吃鱼,视力好的不像话,在抬头间就看见了离宿舍楼不远的小花园里和姑娘调情的左晨辉。
那天夜里,陆清浅在叫出陈皓名字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清醒了,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居然会有些害怕看见左晨辉失望的表情,于是认怂的装了晕。
天花板上的繁星隐匿在一片黑潮之中,她躺在一片黑暗里,将手机的屏幕按亮了,又看着它慢慢一点一点暗下去,然后再把它按亮,周而复始。
【我有事先走了,晚安。】
左晨辉一个小时前发来的短信依旧显示在屏幕上,看上去像是一口漆黑冰凉冒着森森寒气的棺材,宣告着他们这段短暂的混乱关系就此结束。
陆清浅目光痴痴的望着蓝底缀着繁星的天花板,她抬起手,用手背抹了把眼泪,拨通了左晨辉的电话,哑着嗓子喊电话那头的人“小左哥哥”。
她说:“小左哥哥你知道吗?两年前的夏天,夏女士又结婚了,不出意外,是和那个不需要工作每天靠着信托基金安然度日的有钱人。
我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一个人偷偷买了机票回国,飞机在S城降落,我混在一个旅行团里顺利躲过了你和我哥,直接溜到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去C城,然后从C城坐汽车去古城,却在半路遇上了大地震。
大巴司机发现前方的路面发生了地陷,慌乱间猛打方向盘,错估了山路的宽度,造成大巴坠下了山崖。
汽车掉下来的时候有一根粗壮的树戳穿了窗户,直直戳进了坐在我斜前方座位上那个中年女人的心脏。
她死了,就在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死在我的面前。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惊恐的看着我,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车翻了,我被卡在座位里动弹不得,大腿不知道刮到了什么尖利的东西,我能感受到到那里的血正咕噜咕噜的往外冒,脚趾骨不知断了几根,已经痛得没了知觉。
当时我觉得我可能也要死了,那时候我想与其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还真不如******去参加我妈的婚礼算了。至少看她虚情假意的搂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恶心的结婚誓词要比死掉强上百倍不是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意识已经有些涣散了,然后模糊的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脸,可能真的是下了狠手,后来到了医院有了镜子我才发现我的脸上都是鲜红的手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