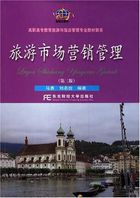(一)宋代“说话”的兴盛
1.兴盛的条件
唐代已经开始专门化的“说话”伎艺,到宋代空前兴盛起来,这种发展变化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原因的。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夺取政权,逐步结束了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封建社会从此进入后期。
唐末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残余,使中唐以来的封建生产关系完成了由授田制向庄园制的过渡。宋代地主、官僚主要以购置的方式兼并土地,而不再享有按等级占田的特权;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以出租田地、榨取实物地租为主,而不再以劳役地租为主。佃农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较自由的租佃关系成为普遍形式。同时,农民还可以自由购买土地,成为自耕农,劳动果实能较多地属于自己,这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这一时期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知识,并使用犁耙、锄锹、镰刀、水车、辘轴等先进农具,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更高水平,城市迅速繁荣起来。而且北宋长期少战事,也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北宋京城汴梁(开封),到北宋末年,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商业非常繁荣。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更是繁荣,从北宋初到南宋,户口数量翻了近十倍,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的特大城市。城内店铺林立,茶馆酒店遍布,有经营不同项目的商业区,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才开始稀少,而五鼓钟鸣,早市的人又开店了。以至杭州有“乐园”之称,西湖有“销金锅儿”之谚。民间更流传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语。
随着商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加强,到宋代,坊市制和传统的宵禁制度完全被打破。从北宋中叶以后,就再也听不到街鼓声了。坊制的破坏,使市民可以随意开门经营商业;市制的崩溃,使市民可以自由进行夜市。商业店铺营业时间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天明后开始营业,天黑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馆的营业时间大都在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坊市制的取消,大大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场面貌大为改观,商店临街,到处是商贩和手工艺人。交易时间也没有了限制,形成繁荣的夜市。除都城外,许多城市如长安、扬州、镇江、徽州、成都、广州、泉州等也都十分繁荣。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城才十多个,到宋徽宗时已发展到五十多个。
城市的繁荣、工商业的兴盛,使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成为一股可观的社会力量。市民们集中在城市里,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除了一般市民外,由于宋代推行禁军制度,兵士集中于京城及大都市。据统计,宋仁宗时代,竟有禁军1259000人之多,半数以上散居在京师汴梁附近。这些士兵加入到市民阶层中,除操练武艺外,也需要娱乐。北宋“承平日久,国家无事”,于是大量聚集在都市中的人便在闲暇中寻求享受娱乐,古老的农业大国形成了都市的繁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杰作《清明上河图》生动展现了东京汴梁的繁荣面貌。繁华富庶,催化了市民们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市民,是一个文化素质比贵族文人低,但阅历见识又比乡村农民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皇宫贵胄的官场,不是高雅的书斋,也不是宁静的山村,葱绿的原野,而是熙熙攘攘、闹闹哄哄、巧营精算、风波丛生的都会商市。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审美趣味可能不高,甚至俗不可耐。他们并不追求典雅的文化诗意、品赏韵味,又不甘冷清孤独、寂寞无聊。他们所倾心的是有生动情节、生活内容的故事,是色调浓烈能满足感官享受、引发笑声的伎艺歌舞。这样,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诗词文赋等雅文学,就不能适应市民大众的口味,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既适应市民口味又反映市民生活的民间伎艺的兴盛便成为必然。可以说,广大市民群众的需要和爱好 ,为“说话” 伎艺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同时,宋代统治者也爱好听“说话”,为其发展推波助澜。北宋后期的仁宗赵祯、徽宗赵佶,南宋的高宗赵构都很喜欢听“说话”。当时朝廷还特设专局采访各种伎艺。“说话”艺人中著名者往往被皇帝召到内廷去献艺,即所谓“御前供话”。大都市的游艺场——瓦舍中,常有许多伎艺高超的“说话”人演出。
在这样的条件下,宋代“说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规模、普及程度及艺术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唐代,为历史之最。
2.宋代“说话”的特点
与唐代相比,宋代“说话”有其新的特点:
(1)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瓦舍勾栏
宋代禁止僧侣在大庭广众之中讲故事,所以唐代寺庙盛行的“俗讲”,受到严重挫伤,但民间仍如唐代一样流行“说话”。北宋早期,民间“说话”只是在市井街边旁进行。
后来,由于“说话”等民间伎艺的大兴盛,市井路旁、茶肆酒楼虽仍有人表演,更出现了固定的大型演出场所——瓦舍。“瓦舍”是宋人市语,也称“瓦”“瓦子”“瓦市”或“瓦肆”,是都市中游艺场所的总称。“瓦舍”的中心是被称为“勾栏”的演艺场。瓦舍的范围大小不等,其中往往有若干个“勾栏”,分别上演杂剧、傀儡戏、诸宫调和“说话”等。“勾栏”原是栏杆的意思,用栏杆围成一座演艺场所,后来就习称“勾栏”,也称“勾肆”。“勾栏”内有“棚”,也称“邀棚”或“乐棚”,张开巨幕用来遮避烈日风雨,也可遮外人眼目。一切伎艺多在“棚”内表演,游人出钱进去欣赏。
北宋时,京城汴梁的瓦舍勾栏就更多了。到南宋就更为盛行、更为普遍了。瓦舍第一次把大量民间伎艺和市民群众稳定地聚集在一起,提供了满足广大市民精神渴求和审美需要的固定场所。瓦舍的出现,是市民文艺兴起的标志。在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宋代,文、诗、词、画,把贵族文人高雅的审美趣味发挥到了极致。宋代理学则阐扬“内圣”之学,言必称“天理”“心性”,融合佛道,把传统儒学发展到具有精致哲学思辨形态的新阶段,重建礼治秩序以强化对人情人欲的扼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却出现了一个个情调格格不入的瓦舍勾栏。这里嘈杂喧闹、粗鄙浊野、充满市井低俗情趣,以至被认为是“放荡不羁之所”。但正是在这里,这些被上流社会轻视压抑的市井小民,这些从来被认为上不了台盘的小商小贩、“愚夫冶妇”、仆役走卒,却俨然成了这片天地的主人,笑逐颜开地欢聚一堂,随心所欲,纵情享乐。这里的娱乐活动、伎艺表演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为转移,而市民们高涨的热情,也促进了民间伎艺的兴盛。瓦舍在农业文明的古老中国催生出市民文化,“说话” 伎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得到蓬勃发展。而且,与唐代“说话”盛行于寺院,多在参加宗教集会(如斋会)时进行不同,瓦舍勾栏中的“说话”等伎艺完全是娱乐性的。
当然,宋代“说话”还不仅仅限于瓦舍勾栏,有的还在茶肆酒楼、城镇市集、宫廷寺庙、私人府第、乡村田舍等处作场,可见“说话”伎艺在宋代的繁盛和普遍。
(2)有很多专业化的“说话”人
“说话“发展到唐代,在百戏中独立专门化了,而发展到宋代,在极度的繁盛中涌现出了许多专业化的“说话”艺人。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中有“两宋说话人姓名表”,将《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出现的“说话“人作了一次统计,共129人,除去重复的情况,仍有110人。这是见于文献的,不见于文献的无法统计。这些“说话”人一般出身于小商小贩、城市贫民,也有落魄的知识分子,而且多是男性,少有女说话艺人。可以说,“说话”是男性的天下,而从事其他说唱、戏曲表演的则多是女艺人。
(3)成立了“说话“人的行会组织——雄辩社
宋代工商业繁荣,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分工细致,出现了行会组织。各种伎艺人员,为应付官府差役和保护同行利益,也成立了行会组织。“说话者谓之‘舌辩’”,所以其行会称“雄辩社”。雄辩社是“说话”艺人磨砺唇舌、训练伎艺的组织,纯粹是一种职业性的团体。说话人经常在这里交流经验、切磋伎艺、取长补短,提高“说话”的技巧。其中名位高、年辈长、伎艺精湛、有学问的职业艺人称作“老郎”。“京师老郎”就是南宋临安说话人对汴京前辈艺人的称呼。
(4)有了编写话本的团体——书会
“话本”是说话艺人用来“说话”的底本。除了继承以前流传下来的话本表演外,由于“说话”的兴盛,对“话本”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于是要编新的,这样就出现了专门为说话人编写话本的文人。这些文人拥有自己的行会组织——书会。当时较大的城市都有书会组织,如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成员一般称作“书会先生”,也叫“才人”,少数名重才高者则被称作“名公”。“才人”多是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文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有较娴熟的文字表达功力和较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他们沦落为书会先生,熟悉市民生活,谙熟人情世故,与艺人合作,既为他们编写新的话本,又依据他们的讲唱,把流传的话本加以整理提高。书会先生以此谋生,本身已转化为市民阶层之一,成了市民阶层的代言人。
(5)“说话”人的水平大大提高“说话”的兴盛和受到广泛欢迎,对“说话”人的要求也高了,为了竞争,他们的业务知识水平大大提高。“说话”艺人必须广泛学习、积累知识、提高水平,能从现实生活中经常发掘题材。正因为宋代“说话”艺人已是专业化的,经过了广泛学习,又在雄辩社中得到提高,所以“说话”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具有讲说流畅、随意据事演说的本领,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6)“说话”分了门类
宋代说话门类,即所谓“家”“家数”的形成,是“说话” 伎艺高度发展的标志。分工的细致、说话艺术的风格化,是市民欣赏水平提高以及同行竞争的结果。关于宋代“说话”门类,历来说法不一,至今认识仍不同。
北宋汴京瓦子中的说话门类,成书于建炎十七年(1147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提到的有:讲史、小说、说浑话、说三分、五代史五个门类。但“说三分”与“五代史”都应属“讲史”,只是因为这两类“讲史”特别发达,所以独立出来。从门类看,只能算三个。
到南宋,说话分为“四家”。最早谈到说话“四家”的是成书于端平二年(1235年)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