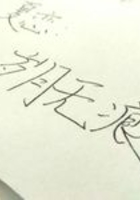候月梅的这桩婚事,村里最尴尬,最不顺气的就属馋猫小顺子了。这孩子这几年和候月梅生活在一起,受了不少委屈,也得了不少的便宜。初时,他一门心思是对候月梅的感激,除了言听计从,俯首贴耳外,还百般的殷勤讨好,到了后来一切就变了。
候月梅平空得了这么个听话的准男人,又撕破了脸过活在一起,也还诚心实意了两年多。后来,候月梅人就变懒了,馋猫也开始有了抵触情绪,原因是候月梅卖了两年菜,接触的人多了,家里收入也宽裕了不少,对馋猫开始颐指气使,吆五喝六,指挥馋猫整日没个消闲,还落不下好。候月梅的几个女娃也大了,懂事了,对自己的娘不敢怎样,对馋猫就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有时就恶作地有意为难这个年龄不大,长像丑陋,身份特殊的外人,让馋猫在候月梅的心目中的位置,一天比一天远了,坏了,讨厌了。
有一天候月梅不在家,大女儿骂馋猫是贱种,还说了许多不入耳的脏话。馋猫一时火气上来,给了那女娃子两耳光。那女娃这下有了理由,把头发弄乱,把脸弄脏,等候月梅一进门,哭得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告状说:“唉呀妈呀!我不活了,他对我动手动脚,想流氓我。我骂他,他还打我,揪着我的头发往地上按我。妈呀,你瞧我的头发都让他给弄成什么样了!他还对我的脸吐唾沫,骂我和妹妹是驴仔子,说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都那个了。妈呀,我不活了,我要跳河死去呀。“
“啪“,候月梅不假思索,顺手就给了站在一边鼓着腮帮子、喘着气、歪着眼的馋猫一耳光。耳光的脆响,打住了女娃的哭诉,也打愣了馋猫原想说出的辩解。这个耳光,不同于平日里的那些个耳光,它太令人屈辱,太无中生有,太岂有此理了。馋猫的怒火爆发了,冲上去把女娃推了个屁蹾,人泥鳅一样溜出了屋门,身后传来候月梅的咒骂:“王八羔子,这么小的人居然给老娘做出这种事来。你滚着跑了,你跑了再也别想回老娘这个家来……。“
馋猫跑出了村子,跑到村西的那片柳树林,一个人呜呜地哭得好伤心。
那天晚上,馋猫回到了自己父母留下来的那个窝,一拉灯盒,灯没亮。他摸黑挺了身体往冷炕上一躺,只一会就觉得冷气刺骨,觉得硬炕板搁得人皮肉难受。馋猫捱不过,摸黑跑到零乱堆放了麦秸的场院,把棉裤和上衣的襟子挽在一起,腾出裤带,也不管是谁家的麦秸,扎了一大捆背到身后,一只手在胸前揪着挎过肩头的裤带头子,另一只手提着棉裤的后腰回到了家里。
火在炉堂里烧着了,炉堂前不时往里添加麦秸的馋猫飘忽的身影,映在矮房子的后墙壁和屋顶上,如魅如幻。身体暖和了,饥饿的肠胃叫唤起来。馋猫的被褥和家里能用的板凳水桶,以及粮食作物全数都并入了候月梅家,就连生产队分配的土地和集体财物,也在他的亲口同意下,和候月梅分到了一起。现在,馋猫被逐出了候家,身无分文,家无一口能吃的东西。
半夜里,馋猫偷偷翻进了候月梅家的院子,从地窑里取了十几颗土豆,从凉房的一个大瓮中拽出了一条冷冻的生猪肘子,然后借着月光把一切恢复了原样。临出门时,他顺手从菜瓮里抓了两把冻成冰块的烂淹菜,塞进了衣服口袋。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候月梅一家睡得连点反应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小家,馋猫把土豆煨进了灶火的灰中。没有刀具,就用牙咬下一块块生猪肉,找到了两根细铁丝,穿着用小木棍搁在灶火上烤。烤熟了,一品尝有肉香却少盐味,想起了那两把烂淹菜,谁知从口袋里掏出的是黏黏的水湿。馋猫掏出淹菜后无处搁放,就放在土锅台上,对着炉火,一口肉,一口淹菜,一口烧土豆,吃得浑身上下暖洋洋后,把剩下的麦秸铺到炕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在随后的几天,馋猫没有回候月梅的家,候月梅也没有来找馋猫,一大一小似乎都抱着就这么算了的决心。也就在这时,候月梅认识了外省来的菜贩子能人,没几天就领回家住在了一起。馋猫一切都看在眼里,肚里憋气,又到候月梅家偷了几次。候月梅与新人正经历欢心,居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结婚的那天,馋猫看着全村老老少少都涌向候月梅家吃饭喝酒,嘴馋的毛病无数次难为着他。有一阵子,他差点就去了候月梅的家,人都快到门口时又狠劲把自己拉了回来。馋猫一个人来到空旷无人的野地里,放声咒骂发泄,却随了咒骂,想起了候月梅当初对自己的好,和那些个肉体间的事情,想到了现在候月梅就新找了一个外地男人,而自己从此再也没有重新回去的可能了。馋猫哭了,眼泪让多日没有洗过的脸,变得更加脏污。
当晚,参加婚礼的人们散去后,候月梅家的灯也关了,整个村子进入了热闹之后的沉静。弯月在惨淡的云丝中穿行,树影半明半暗,树木和房屋形成了黑影幢幢。馋猫真如一只大猫一样,快步来到候月梅家院门外,爬上了门口的凉房顶,卧倒了屏声静气观察了一会,发现两间住人的屋里没什么动静。馋猫顺着墙角,凭着年轻人的轻巧,几乎一点声音都无就溜到了候月梅的窗下。隔了窗纸,屋内传出了两人不同的鼾声,一个熟悉,一个难听又陌生。馋猫在院子里像根树桩一样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做了。
馋猫无意间看见自己的影子,瘦长地爬在西边院墙上,还有半截不知虚到那里去了。他浑身打了一个寒噤,身体感到了冬夜的寒气之浓。他想放嗓子喊叫,向屋里熟睡的人表达自己的愤怒,最后一狠心,在熟悉的地方抱了一块闲放的淹菜石头,鼓了鼓气,双手举高了,使着劲向候月梅的屋门砸去。一声“咔喳“的脆响之后,是石头落进屋里地上的“咚“声,跟着是一声女人的尖叫,一阵男人的恐慌骚动。
馋猫早窜上了刚才骑过的墙头,慌乱跳到了院子外,双脚落地不平稳,摔得屁股生疼,爬起来就跑,不想碰到了几个人影,绕开再往前跑,听到身后的村庄喧闹起来。他以为是候月梅喊醒了众人来追自己,就没命地往村外跑去,却不知,那是高锁锁老婆担心男人冻死,通过队长黑玉英,又叫醒了更多的村人,在村里折腾着寻找呢。
馋猫在村外躲藏了不知多久,听着村里安静下来,刚才的紧张放松下来,恐惧一阵阵来袭。馋猫在村外狂跑起来,只是步子错乱,有时踩空,有时被拌住,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跑,来到了堆满了麦秸的场院,在最大的一堆麦秸上,使出小时玩乐学会的方法,老鼠打洞钻进了麦秸的深处,然后用脊背使劲扩大容身的地方,还用麦秸堵塞了钻入时的洞口。
躺在麦秸堆的深处,闻着麦秸的干爽而又略有霉腐的味道,馋猫慢慢安下了心,手脚也不像先前那么冷得发抖了。他先还想着天亮后咋办,很快就睡的连梦都没做一个。
馋猫第二天前半晌才醒过来,爬出麦草堆,睡眼醒松了好一阵,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不由迷迷茫茫没了主意。顺着风,村里的喧闹之声传了过来,馋猫好奇又胆战心惊绕回村里,看到高锁锁家周围站满了交头接耳指手画脚的村人。候月梅和她那个新男人也在其中。馋猫从路过身边的人们嘴里,知道了高锁锁的事情,也明白了昨天晚上村里的闹腾,原来并不是针对自己的原因。
馋猫绕回自己的小屋,冷吃了几口前几天准备下的食物,安分了心思,翘腿在冷炕上躺了一会儿,就又来到了候月梅家的大门外,也没多想,从多次进出的地方跳进院子,从昨天晚上砸烂又被用纸糊住的门洞钻进了屋子,开始了一场肆无忌惮的翻箱倒柜。
半个多小时后,馋猫拿了候月梅放在箱底的一百多元钱,拿了能人提包里的钱和东西,嘴里吃着昨天办事时剩下的熟肉,看着一片狼籍的屋子,发出几声咬牙切齿的冷笑。
要离开屋子,馋猫看见墙上的旧年画,顺手扯了下来;看到已经被自己抖乱在炕上的被褥,用脚踢到了地上。馋猫越破坏越兴奋,就找到了昨晚自己砸门的那块淹菜石头,抱起来只一下就把灶上的铁锅给砸塌了。他还从碗柜里取出两只白瓷碗,往其中的一只里拉了屎,放到后炕靠近拐角的地方,用另一只碗盖在上面。做完了这一切,馋猫从门洞钻出来,身上穿了那男人漂亮的牛皮夹克。
馋猫溜出了村子,走在通往公社的那条路上,乱喊叫着无词的歌,想象着自已的杰作会闹出的后果而快活不已。他在公社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就坐上去县城的汽车。在县城,馋猫节衣缩食,假装成乞丐,用那些钱熬过了严冬,熬过了又一个春节。期间,馋猫遇到过进城的一碗村的人,只是眼尖,看见了早早就躲开了对方。那件暖和的牛皮夹克,他用塑料袋装着,埋在城效一棵歪脖子树的根部。过几天瞅着没人的时候,挖出来穿上感觉一番。
钱只花不进,在开春的时候,就所剩无几了。长了见识的馋猫,提着那件皮夹克,乘上了到地区的火车。毕竟是头一遭,心理紧张又兴奋,结果在离目的地的前一站就下了车。没办法,一个人顺着铁道,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进到了比县城更大的城市。
在新的城市里,馋猫的那件夹克,和仅剩的几个小钱,被同样是乞讨的一个跛腿的家伙给抢走了。走入了身无分文境地的馋猫,在饥饿了两天后,向行人伸出了乞讨的手。在饥一顿饱一顿中,他渐渐熟悉了城市生活方式,开始学着乞讨度日。
此时的馋猫对一碗村那份旧有的依恋越来越淡薄了,但一盏往事的油灯却始终亮在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