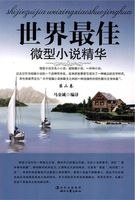白萍又颤微微地道:“你不说吧,不要感情用事,要知道现在……只有我和她同在一个房里,当然使你震动。可是实际她仍是你的,和前几天绝没什么两样。我是病了,她以老朋友的情谊来看护我的病,这是实情呀。”仲膺对白萍的话,没一句不相信,此际已明白自己是卤莽了,但已无法收煞,只可咬牙做下去,便又问了最末的一句道:“白萍哥,我知道你向不诳语,你的话我都信的。不过我还要问你一句,希望你也用这诚实的态度答复,请问你这病的发现是不是在见了她的面以后?”白萍茫然的点点头道:“是的,前天夜里。”仲膺又道:“那么你若不见着她,这病还不会发生吧?”白萍翻着眼儿,没答应出来。仲膺道:“白萍哥,你说啊,我信服你的人格,知道你必给我一个诚实地答语。”白萍被他逼得没有寻思的余暇,就含蓄着道:“那不……尽然,可是见了她多少有些感触。”仲膺听着,忽举手高叫了一声,又低头道:“白萍哥,我佩服你的伟大人格,光明磊落的心胸,你太好了。我总能想得到,你这欢遇到她,心里是怎样况味,你宁可自己苦、病,以至于死,还记着当日和我赌博后的条约,不肯说出一句破坏我的话。唉,白萍,你太好了,也太痴了。因为你太高尚,更显着我太卑鄙。你对一个卑鄙的人,还这样守无谓的信用,岂不冤枉?现在我实不能再卑鄙下去,要把一切都明白说出来了。固然我现在说不说无关重要,因为我已决定独自远走高飞,走后当然你们要变一个必然的局面,你总可把这秘密叫芷华知道。不过我仍怕你太好太痴,不肯对她说我的劣迹,而且这秘密有一部分只我个人知道,所以必须由我说出,才能彻底明白。”说着便眼望芷华道:“林太太,你必正在纳着闷呢,并且你听我说要走,或者难免恋恋不舍,你要知道,你现在对我的感情完全由我诈欺手段取得。再深一层说,便是你已被我骗了个长时间,这真象在十分钟内,你便可明白,那时真不知你要鄙薄我到什么程度。林太太,你听我要自诉供状了。”这时白萍哑声顺喊道:“仲膺,仲膺,你不要胡闹,你是神经有病了,你不要再弄出许多纠纷,大家都不好。现在你带她回家去吧,什么话也不必说。”仲膺向白萍微微一笑。又把这微笑的跟光回头望望淑敏。接着摇了摇头,没答白萍的话,仍对芷华继续说道:“林太太,你不要记忆着咱们那次婚礼,那婚礼是由虚伪、诈欺、残忍、懦怯,种种罪恶造成的,我从头告诉你吧。”说着就从去岁在天津寓所外夜遇白萍说起,说到两个情敌如何到了旅馆,如何用赌博方法解决这三角角主的前途。如何自己赢了,如何白萍定下约会,如何自己估计而行,得了成功,说完才转入正题道:“我所说全是事的表面,就这表面看,除了我不该和原有夫权的白萍争夺他的妻子以外,其余一切都是靠着命运,没什么罪恶。可是向隐微处看,我可罪大恶极了,我从遇着白萍到和你结婚以后,中间有许多次都是昧着良心作事,第一,我在旅馆和白萍作那样赌博,诚然是由于他的逼迫,可是在那时我若肯斩钉截铁地自认并不十分爱你,事情或者能有变化,但是我口虽不言,态度上总表示没有你不能生活,才逼得白萍想出赌博的方法反而逼我。第二,我胜利以后和白萍分别,也曾几次觉悟不该作这样事,想到自己可以远游躲避,无形中废止了那赌博的条约。到我失踪日久,白萍自会与你重圆。否则我也可先跑到极远的地方,然后给白萍来信,声明白己已出了家,或投了军,前约作废,白萍也必能去保护你。可惜我想得到竟做不到,私心把良心战败,仍自承受白萍那不合理的帮助,以自得到快乐,而使帮助我的人沦于痛苦,这还只是我愧对白萍的。第三,我既承受了白萍的帮助,在梁园中遇到你,被你接到家去。你把白萍的信和照片给我看,我那时自然明知道是他假作的,而他作假的原因无非要毁坏你对他的希望,完全归心于我。我看着连心都疼了,对白萍真有说不出的感激,但是你却对白萍的寡情有些怨恨了。我想到只为我的原故,竟使他在你脑中留下不良的印象,不由一阵良心发现,几乎要把真相对你说出,替白萍洗刷,无奈我还是私心太重,到底忍住了没说,反对白萍旁敲侧击地说些坏话,加重你们的恶感。”
仲膺说着,见芷华面上颜色的惨白和和肌肉凝滞好似变成石膏所塑,只两个眼儿特别放大,既像瞳人将跳出来,撞到自己面上,又像她的眼眶要把自己吸纳进去。但在她那眼光中,绝看不出是怒,是怜,是爱,是怨,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片茫然,便知道她此际神经已被刺激到极点,转成麻木。再看白萍,白萍却没瞧自己,只低了头摇着,那情形好似因搁阻自己不得,正在发无计奈何的叹息。仲膺猛想到自己莫再看他们作此状态,赶快说完要说的话,应该离开这里了,便接着说下去道:“林太太,大约我所说出来的已很够你气恼了,可是我还没说出那最对不住你们的事呢。再从白萍说起吧,他的好法,真叫我寻不出一个相当的名词形容,什么仁慈宽厚多情好义重信,在他却只是一小部分,我真不知他道德有多么高。在第一次,他发现了你和我的秘密,两个亏负他的人,一个是爱妻,一个是良友,叫他怎样呢?他只可走了。但是他走后,你怎样忏悔,怎样把我也赶将出去,怎样奔波着寻他,他都不知道。到以后从旁人口里听到了,他十分感动,完全对你原谅,跑回来想和你重为夫妇,那时候就是去年的秋天。我天生是你们伉俪的魔星,偏偏在那时候每天夜里总到你的楼旁去站一会,大约是神经病的原故吧。谁想这么巧,在白萍挟着一片热情从外边归来的时节,恰巧在你的寓楼旁遇到了我,这当然叫他起了种种的感想,由感情使他生出一种误解,认为我对你的需要比他还甚。又认为我和你既有过关系,他已失了独有的丈夫地位,与我同成为你的情人,才想出用赌博办法,决定命运。及至我得着胜利,他许给我帮助就分手了,这以后他就去假造那照片,预备对你作离婚交涉了。他那照片中所谓新婚妻周梅君,虽有其人,却只是个窑子姑娘,被他用金钱雇用,合摄了这张照片,于是他又写了那封信和离婚书,一并给你寄去了。你以为他这件事做得对你过于寡情么?可不然啊,他最大的误解是认为你和我同居比随着他还能幸福,这样作正是对你爱护。见解虽然错误,动机却由于爱你过度,才看轻了自己的幸福。他又以为自己越绝断得斩戳干净,越是于你有利。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你恨了他,忘掉他,才能同我过更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便假造出那最足使你伤心的照片。但是他毕竟是想得开抛不下,在要把照片寄出的时候,想到恩爱的旧侣从此永远属于他人,和自己永远隔绝,他如何割舍得下?不知展转思量了多久,才用他那苦痛的心,想出听天由命的办法,在照片的夹层上,写了一行字,声明他的苦衷,藏在隐微之处,那意思就是求上帝判决。倘然上帝判你重归白萍,就使你发现那秘处的文字;若判你嫁给仲膺,就使那秘密永远不发现到你的眼里。”说到这里,忽听白萍惊叫道:“这……你怎知道?”仲庸向他点头笑道:“你不要诧异,这里面没什么玄秘,只就我看见听见的事,再加以揣度,就很能明了了。”说着又转向芷华道:“白萍费了这一片苦心,若在你接到那照片时就把秘密发现,那真是好事,不特白萍少受痛苦,你少经波折,并且你也就根本只去寻他,而不致和我发生这番不道德的关系,无形中更消弥了我的不义行为。哪料你竟只看了表面,就使一切都转入罪恶的途径。当你从粱园把我带到家中以后,将白萍的照片给我看,我当然明白这是白萍对我践约的一种作品,也明白那周梅君绝非他的新爱人,只感激他守信不渝,佩服他思想周密。及至在无意中翻弄那照片,竟发现了夹层中的字迹,我才猛然醒悟,自己作了恶事,领会了白萍的苦衷,他原不忍舍你,而迫于信用,使他定要作这违心的事。那几十个秘密的字儿,显露了他心酸肠断和无可奈何的情形。我当时惭愧悔恨,本想要把这秘密和盘托出,然后自行退却。无奈我终是个坏蛋,是个自私的人,把白萍的痛苦和自己的幸福一加比较,决定要以自己的幸福为重,于是把这秘密藏在心中,一点不使你知道。所以你要明白,从粱园相遇的那一天直到今日,在这样长时间里,我一直昧住良心欺骗着你,把你的忠实的丈夫的热情给扣留起来。你也一直被我蒙蔽着,反倒怨恨你那忠实的丈夫。”说着一举手道:“我把自己的罪状宣布了,只于稍稍安慰自己的良心。最要紧的是叫你知道白萍是从始至终的爱着你,而他时常反像对你寡情的原故,就是误会你的爱我比爱他还重,故而屡次牺牲自己,甘心退让。这退让当然也出于爱你的动机,不过他没想到如此反加重你的痛苦,加深我的罪恶。如今我完全解释开来,愿意你们从此恢复二年前的原状,只当这二年的光阴是做了个颠倒的乱梦。永远把这梦境忘掉,尤其要忘掉了我,以后便是再做起真的梦来也不要忆起我的影子……”
正说着,芷华在如痴的僵态中忽然震动起来,立起身张着手,颤声道:“那照片……上面……上面……”仲膺不等她说完,忙从袋内把照片取出。递给她道:“巧极了,居然给你带出来,这该谢谢淑敏小姐。”
芷华接过那照片去,顾不得听仲膺说话,就向那照片的背面看。见没有字,又看正面,又用手指去揭中间的方孔。仲膺忙指给她道:“你得从夹纸中把照片抽出来,再看背面。”芷华手儿颤得无力,正要依他的话去作,不想白萍在她身后忽然挣扎着坐起,冷不防伸手要抢那照片,却因芷华已然立起,距离稍远,他的手只能伸到芷华肋边,并未夺得,倒把芷华吓了一跳。芷华回头看他,白萍喘吁吁地道:“你不看吧,给我……”芷华似乎明白他的意思,就把照片交到左手,藏到背后,却用右手把他轻轻扶倒,使他仍安睡在枕上,说了句“你好生躺着,别管我。”就又走离床前,急忙抽出那照片,向背面注目。立刻眼光凝住了,通身抖战起来,叫道:“呀,萍,你好……苦了你……傻呀……”叫着眼泪直涌。把泪眼向仲膺一扫,猛地柳腰一翻,上身一伏,霍然扑到床上,两手抱住白萍的脖颈,脸儿紧压在白萍额上,嘤嘤地哭起来,只听得“你傻,你苦,你太爱我,我太对不住你。”其余的就哽咽听得不清了。
仲膺瞧着她这情形,立觉心内轰的一声,似乎心肝脏腑都已飞到无何有之乡了,心里只剩下了空茫。说不出是难过是好过,怔着瞧了一会,只能看见芷华身体的微颤,她口里说着什么已听不出来。继而忽然想起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这么大的世界,好似全和自己失去了关系,这小小的房中尤其是世界离去自己的第一部分。实已无可留恋,应该及早走开了。而且芷华和白萍到了这个时候,正是紧要关键,他俩想有许多话要说,局外人更没有再留下去的可能。想着便望着他们,发了个凄怆的苦笑,回头就向外面走。
走了没有两步,又想起房内还有个淑敏,正要看看她作何动静。但又想到自己才拨弄了她,她不知如何气恼,自己还是赶快漓开,免得再发生无味的纠缠,便不回头看她,只自蹑着步儿溜将出去。出里间到外间,出外间到了院中,猛然被当头的阳光照到身上,忽觉一片光明,好似从一个世界里又踏进另一世界。向前一看,心里的空阔已达到顶点。向后一顾,心里的凄冷也达到极端。然而无论如何,身体已似落到虚空里了。他直忘了现在何处,把身体在虚空里移动,凭着下意识的动作,居然没有走错了路,飘飘地出了公司的大门。此际已不知道这空气中还有个自己,更不知道出门要向哪里去。下了门外石阶,就直奔巷的东口。哪知走出不到一丈,耳中忽发现了一种声音,这声音使他脑中一阵活动,就回头看,他立刻心里不那样空茫了。因为他瞧见淑敏已提着那小旅行箱走出门外,正回头和高景韩说话。他这时才有了思想,诧异她怎也出来了。接着见淑敏用十分匆忙的态度向高景韩道:“白萍的病已有了好的希望,请你对他多关照些。还有看护他的那位太太,就是他的夫人,她要陪伴她的丈夫,不再走了,请你也要多给她帮助。”高景韩似乎大惊道:“呀,那是白萍的夫人,是么?怎。”淑敏道:“我现在急于要走,没工夫和你细谈,只能告诉你大概。白萍和他夫人,在以前曾因一种原故发生意见,离开了两年,白萍这次的病也是由思念他的夫人所起,现在我们已把他夫妇调解得重归于好了,所以白萍的病定能在他夫人看护中得到痊愈。至于细情,我改日再写信报告你吧。”说着就扬手告别。
仲膺在她说话时怔怔地听着,及至见她和景韩告别,才想起她未必不追着自己来,忙转头就走,但身后高跟鞋的声音格格地跟上来了。仲膺心跳着想,这真讨厌,她追了自己来,是什么意思,莫非因自己欺骗了她,故来质问么?果然如此,这女将军的口舌可不易对付,只后悔自己为何出门还不快走,等着受她缠磨,只盼这时她能负气不理我,或者只骂我一场便行了事,那就是如天之福。但求脱过眼前是非,我明天就鸿飞冥冥,任何人都没法寻觅了。
仲膺想着,几乎要放腿逃跑,又觉没有道理,只低头疾行。哪知后面的淑敏走得飞快,已赶将上来。仲膺听着她的履声,将要和自己并肩雁行了,暗叫“不好,逃不开了。”只得静待她开口第一声质问和责骂,先觉着自己腿下被什么东西触了一下,低头看时,原来是淑敏手里的小旅行箱,接着就听她低声说道:“谢谢你,劳驾。”仲膺便知道她是要自己代携着这小箱。本来像仲膺这样有知识的男子,都久已养成替女人提携物事的习惯,仿佛是一种当然的责任,不可避免。对陌生的女子,有时还要帮助,何况又是熟人?于是在淑敏说完话把小箱向他一递,仲膺不加思索,很自然地接过。但小箱到了仲膺手中,情势立时大变,方才是淑敏追着仲膺而来,此际仲膺倒失了自主能力,要追着她走了。因为那小箱总要随着主人,仲膺不能随便拿着走路。淑敏反不顾仲膺,自己轻轻爽爽向前走着。仲膺反变了随从,一步步跟在她后面,心里暗自懊悔,方才安置了白萍芷华,觉到一身无累,如今竟被这小箱累住了,这位小姐想叫自己随她到哪里去呢?她的家是在这本地,但盼她要回去,雇着洋车,自己就可把这累赘物交回,道声“再见”了。但淑敏却直向前走,毫无表示。仲庸不由发急,见路旁有停着的空车,就唤淑敏道:“喂,张小姐,您不雇车么?”淑敏回头望着他道:“您累了么?’’仲膺却仍是不好意思,只摇头道:“不累。”淑敏笑道:“您不累,再走几步也就到了。”仲膺道:“您上哪里?”淑敏道:“已过了午餐时候,我们该去吃些东西。”仲膺听她要去吃饭,当然一个男子对于一个女子有请吃饭的天然义务,任得如何心怯,也不能听着女子表示饥饿而置诸不理。仲膺忙道:“真个够时候了,您想上哪里?”淑敏道:“撷英吧。”仲膺点头道。“好,撷英虽近,也是坐车去好。”说着就喊了两辆车,直到撷英菜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