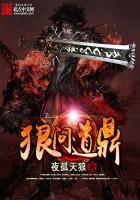到底钱太太气微,被老四压到下面。把她才穿上的衣服都撕烂了,又咬又打。钱太太吃得亏可不轻,在底下也按住老四的大腿乱咬,闹得沸乱盈天。小王立在旁边,只管拉老四。老四以为他偏向对方,就更向钱太太下狠手。钱太太疼得吱吱乱叫,正在这个当儿,马老婆才跑进来,大惊小怪地拉劝。老四死也不肯松手,一阵翻滚。连马老婆和小王也跌到地下,跟着她们绞成一团。闹得马老婆房中那一对野鸳鸯,也都出来,跟着劝解。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叩门。里面打得正热闹,马老婆哪听得见。外面的人因不见答应,就自走进来。到了房中,看见四个入在地下滚。两个人在旁边高叫别打别打,都不敢上前。这个来的人也怔住了。立着瞧了一会,才看清几个打架人的面目。立刻叫了一声,奔过去一把拉住了钱太太,一手推着那老四,想把钱太太拉出来。老四疑惑这人是来替钱太太助阵,就要与她动手。来人叫道:“您几位停停,我问问是怎么回事。”马老婆见来者面目甚生,忙拉住老四。老四原是马老婆送信请来的,二人心里早有默契。方才马老波虽然喊着劝解,暗地却鼓励着老四收拾钱太太,代她施行惩罚,所以老四不肯休止。如今见打得够了,又来了生人,就止住老四。钱太太已是满面灰尘,一身碎布。昏头转向的喘着,才听有人叫了声“姐姐。”她连忙转脸看时,几乎疑惑自己在做梦。原来面前的竟是自己的妹妹龙珍。不由一阵凄惶惭愧,低头哭了。龙珍此际不暇细问姐姐,只可先把身子护住她。向老四问道:“这位姐姐,你们为什么打?”老四瞪着眼道:“你是干什么的?来管闲事?”龙珍道:“我是她的妹妹,前来瞧她。正遇见这事,怎能不管?”老四道:“原来你们是一家。你出来帮她,我也不含糊。”龙珍道:“我不是帮她。你别错疑了。我这姐姐素来就有神经病。短不了胡说乱道,得罪人,您瞧我的情面,恕过她吧。”老四道:“没有那么容易!非毁了她不可。”龙珍道:“你们到底为什么?积下这样深仇呢?”老四虽然理直气壮,但她和小王也是暖昧关系,怎能说出口来?就指着钱太太道:“你问她。”龙珍道:“我也不必问了。她向来作事糊涂,有错也就在她身上。您高抬贵手,让她一步。”说着连连向老四拜着,老四本已占够便宜,又怕闹久了,被巡警知道,正恨不得顺风收篷。见有人来劝,就趁坡儿下梯,把钱太太臭骂一顿,又对龙珍说了许多光棍语,才指着小王道:“没皮没脸的,你就跟着这臭婊子吧。从此不必理我,我算知道你。咱们是一刀两断。”小主见事已将要成为尾声。知道老四气已消了,就央告着她,老四还是不依。但二人竟吵嚷着出门走了。这里龙珍听老四说的话,和小王的情形,便已明白姐姐落在这里,定又作了不正经的事,和人家起了纠葛。好容易劝对方走了,才扶起钱太太,坐到床上。这时那看热闹的人已又退回那对面房中。只有马老婆还自不走。龙珍本因知道钱太太向畏先起诉的事,又由畏先那里知道了她的住址,便跟踪而来。遇到姐姐,忙要询问别后的情形,但见有个老婆儿紧跟在旁,不能开口。钱太太虽被妹妹解围,但觉羞愧难当,低头不语。马老婆却因听龙珍说是钱太太的妹妹,知道来了亲人,哪肯离开?
正在这时,钱太太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她看见龙珍,不由想起当年和畏先同居之时,清清整整的家庭,自己贵为家主,唯我独尊,手里又有积蓄,过着极舒服的日子,那是何等享受?况且自己本是妓女出身,只为厌倦风尘,又瞧着畏先疲软易制,才出水嫁他,预备作个久远归宿。畏先也绝没对不住自己的地方。本当过下这一世去,怎奈自己有福不会享,无事生非,偏要和周瑞楼勾搭,抛弃大好家庭,随他奔跑,结果上了大当,几乎死在他乡。好容易逃回北京,受尽困苦,才又遇见畏先。蒙他收留,总算畏先情义够深,自己运气不错,实该收心学好,怎又胡作非为,落得受许多光棍凌辱。到头还嫁了个老头儿,不妻不妾,不明不暗的,已不像回事。想不到今天和小王偷情争风的丑事,又落到龙珍的眼里,自己可有什么脸儿见她呢?她悔恨羞恼之下,这一痛哭,龙珍倒觉手足无措起来,忙用言语安慰,钱太太好半晌止哭。龙珍悄悄道:“你把这老婆先支出去,咱们好说话。”钱太太就向马老婆道:“大娘,你去给我们弄些水喝。”马老婆知道她的意思,才应声儿出去。龙珍道:“姐姐,你住的这是什么地方?自咱们分手,你都作了些什么事?怎落到这般光景?”钱太太叹道:“妹妹你别问我,我简直不是人了。你倒好吧?”龙珍道:“你先别问我,我倒没有什么。只是我听畏先说,你从第二次跟他离散,又叫律师写信向他索要赡养费,有这事么?”钱太太愕然道:“你怎知道?’”龙珍道:“我见着畏先来,就是你这儿的地址,还是他告诉的呢,姐姐你可不应该。当初你那样狠心的把畏先赶出家门以后,你被周瑞楼害了,落到讨饭,他居然能念旧情,又收留了你,你还不好好跟他度日,又反脸讹他,这未免太说不下去。畏先在公司每月只有四十元薪水,你倒要向他每月讨五十元,畏先急得红眼,要打官司告你,是我知道,忙拦住他。跑来问你是怎回事。”钱太太低着头道:“这不是我的意思。”龙珍道:“不是你是谁?”钱太太道:“咳!告诉你吧,我现在算受了报应,落到一个老头子手里。就在这里住着,是这老头子架着我讹畏先的。”龙珍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形,又嫁了人么?”钱太太道:“也不算嫁,以前阴错阳差的。遇过许多事,如今就算落到这儿。”龙珍瞧着她,又气又恨道:“不是我说你,你七乱八糟的都不成话了。快把实情告诉我,咱们做个打算,我不能瞧着你这样流落。”钱太太摇摇头,流泪道:“你是我的好妹妹,我知道你一心疼姐姐,可惜我自作了孽,现世现报,你不能救我了。你可记得,当日我在家中打发你走的时候,你也曾劝过我。我那时不是对你说,明知道自己是走错路,无奈天意该当。自己管不住自己。接着被害去,应走这步运气。我所经的事,都是这个情形,好像一个人从高处跌下来,如今算跌到地了,你还想拉我上去么?”龙珍听姐姐所说的话,又似有些觉悟,又似甘心堕落。忙道:“你不必说这些没用的话,快告诉我眼下有什么打算?”钱太太道:“我也没有打算,既落到这步田地,你们谁也不必管我,让我自己混下去。本来像我这倒霉的人,死死活活,都不算回事。”龙珍道:“你也不要这样灰心,我更不能瞧着你在这里受罪。依我的主意,你还是回去跟畏先度日。”钱太太摇头道:“我不能了。”龙珍道:“你何必不好意思?畏先跟你终是老夫老妻,总有旧情,你回去他也未必说什么。便是他不肯,我也要央告他点头。姐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在外面飘荡着,日后上哪里归宿?只有回老家是正路,你依我吧。”钱太太半晌才道:“你的主意全对,我也知道回去是正路,可是办不到了。现在我要离开这里,就有人不饶。”龙珍道:“怎么呢?你在这里是什么情形?”钱太太只得把从姘赵八起,直到现在归了褚老头儿的事,都源源本本说出来。龙珍想不到姐姐竟一串珠的作了许多无耻事迹,瞧着她又是气又是恨,暗想自己若不是从小跟她长起来的,真想不管她,太无耻了!但是她终是自己姐姐,实不忍看着她流落,只得说道:“你的意思是怕这姓褚的不放么?”钱太太道:“自然,他为我花过钱,我现在就算嫁了他。”龙珍道:“你也太容易嫁了,这样随便凑合,不能算数。我劝你还是回去,姓褚的不肯,咱们可以把他所花的钱偿还。”钱太太道:“咱们哪里有钱呢?”龙珍道:“多了不成,三二百块还有。当日你打发我离家的时候,不是给了我些首饰银钱么?我把现钱都用了,首饰还原封没动呢。”钱太太听了,想起自己那些积蓄,都已挥霍净尽,龙珍得到一点儿,居然还存到如今,拿来救我,不由大为感动,流泪说道:“妹妹,我明白了,你们都是好的,连畏先都很对得起我,只有我一个人不够人味儿,一直的向下路里溜,把丢人现眼的事都做尽了。可是只落个受苦受难,像我才是贱骨肉儿呢。如今可回过味儿来了。一定跟你回去,咱们姐妹还像当日那样厮守下去。你也不必用钱,我偷着跟你跑吧。”龙珍大喜道:“姐姐,你这才是明白,咱们快走。”钱太太道:“你在哪里住着?”龙珍道:“你先不必问,出去再说。”钱太太匆匆下床,附着龙珍耳朵道:“你瞧见那老婆了,咱们得瞒过她。你先出去,在胡同外等我,我随后再溜出去。若是一同出门,恐怕她疑心。”龙珍听了,忙向外走,到院里还回头叫道:“姐姐,我走了,后天再瞧你来。”钱太太在房中也说不送不送。二人以为这样便能瞒过马老婆。哪知马老婆从头儿就没离开窗外,把她们的话都听去了。见龙珍出来,闪开了让她出去。便掇了张小几儿当着大门一坐。钱太太在房中把破碎衣服换了,向外溜走时,见马老婆在门口拦路,不由吃惊,忙道:“大娘,我房里没茶叶了,要出去买一包,你给看着门儿。”她说这话满以为马老婆若不放她出去,便得替她去买,她怎样都有出门的机会。哪知钱太太话方说完,马老婆竟摇头道:“你在家里呆着吧,茶叶我房里有,稍迟给你送过去。”钱太太道:“我还有别的东西买呢。”马老婆道:“买什么都得等一等儿,褚爷回来叫他去。”钱太太着急道:“我出门买东西,碍你什么事?”马老婆道:“这几天你都没出去过,偏今儿非往外跑不可。你们褚爷烦我照应你,你又才同人打完架。出去我放心么?”钱太太和她争执半晌,马老婆只是不允。这时龙珍在巷外久待姐姐不见,又走回来。看见她被阻不得脱身。知道马老婆必是监视她的人。如今看出破绽,定然不放她走。看情形用强是不成的。想着又见马老婆正面向内,对姐姐说话。钱太太却面向外,已瞧见龙珍。龙珍忙对她摆手,暗示叫她不要争竞,快回房里等侯。钱太太瞧得明白,龙珍已开步走了。钱太太知道她是去设法搬请救兵,便不再开口,笑一声道:“大娘你真死心眼儿,我出去又算什么?值得这样横拦竖遮。我不出去成不成?”说着又赌气回到房里。她心中以为龙珍定然很快地寻了助手,或者就近报告警察。须臾可到。哪知等了许久,龙珍竟没有来,褚老头儿倒先回来了。
马老婆顾不得钱太太看着,就将老褚唤到一旁,把钱太太一天的事都报告了。并且言说小王那面,被她勾出老四来打散了,已是不成问题。只这凭空闯来的女子,好像是钱太太的妹子。咕咕唧唧的只劝钱太太走。钱太太已活了心,这可要留神防备。老褚听了倒为难起来,他所以要钱太太的原因,不过想借她向本夫那边讹钱。并且放在马老婆手下作些暗娼生意。如今作生意这一层,经小王这一番试验,已知她人老心少,不是赚钱的货物。向钱畏先讹赡养费一层,也不特没有希望,反而把她的家里人勾出来。若非马老婆监守,几乎落个人财两空。但还怕她家里人不死心,再来勾引。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只可急速想个简捷办法。便和马老婆商量,要把钱太太转手卖出,弄些现钱,也图个心静。马老婆十分赞成道:“这是个又赔钱又扎手的货,你留着她终要上当。这院里只我一个人,出来进去,偶一失神,就许被她跑了。我可担不了这沉重。你趁早想法子。”老褚犹疑一下,便又出门去了。
钱太太见他俩鬼鬼祟祟,知道是为着自己。老褚又没进屋就匆匆出去,心里更忐忑起来。只盼着龙珍急速快到。但是一直没有音信。天到十点多钟,老褚回来,竟带了两个雄纠纠的中年男子,向钱太太说:“这里住不得了。警察查着马老婆开着暗娼,眼看便来抄查。现在只可赶快躲避。”钱太太知道老褚说谎,他定是听见马老婆说龙珍来了。自己想要逃走,故而换个地方,以便监视。自己若随他走,不知落到哪里,龙珍便再领人寻来,也不能见面了。便对老褚道:“马大娘房中不留人住。咱们清门静户的,就有巡警来查,也得不着证据。何必躲呢?再说马大娘和我这样儿。”老褚不等她说完,便抢着道:“你懂得什么?要没有危险,我能无故的搬家。你趁早快走,迟一会警察来了,就后悔也来不及。”说着便拉着她向外走。这时钱太太还想挨延一下,便道:“我走是走的。可是也得先把房内东西移开呀。”老褚道:“你不必管。只要人躲开,东西慢慢地搬,没关系。”钱太太想了想,正拿不定主意。老褚又连声催促,钱太太忽然赖在床上,叫道:“我不走。大黑夜的上哪里去?情愿守在这里。叫巡警捉去受罪。”老褚见钱太太有意反抗,知道她已不受络笼,只可用强硬手段对待了。当时就吩咐带来的那两个壮汉,将她殴打。那两人便应声而来,马老婆忙拦住劝道:“你快跟他去吧。为什么自讨没趣?俗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了他,想不跟他行吗?”钱太太见势不好。老褚一边共有四人,自己却只单身,恐怕吃亏。就也缓和了口气道:“我也没说不跟他,只是这三更半夜,定要带着我走。我知道他安着什么心儿?他若真是搬家,明天连人带东西一齐走。现时出去,我还怕受了害呢。黑灯下火,又带着人来。谁不怙惙呀。”马老婆道:“他是你丈夫,怎能害你?若不为有来抄查的信儿,也不会黑夜叫你走。再说他带人也为保着你的。”钱太太任她怎样劝说只咬定:“今夜绝不出这大门,明天说走就走。”老褚听她这样说,疑惑是她已约下救兵,更不肯容她推延,吩咐那两人动手。那两人过去把钱太太按住,她只喊叫出一声,便被掩住了口,接着两手也被用布条捆上。老褚知道她顽强的时侯,是没法子离开这里。虽可将她捆上,派人抬了出去,但恐走不多远,便被巡警盘诘。只有立时给个下马威,把她打怕了,便可以指挥如意。于是喝令那两人将钱太太翻身向下,用藤条打将起来。才打了几下,忽听外面有脚步声跑进来。马老婆先听见了,想起街门未关,忙跑出去看。还未走到外门,只见黑影中有三四个人闯将进来,忙问“是谁?”来的人不答,仍向里跑。第一个便是龙珍。第二个柳如眉,第三是祁玲,最末便是钱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