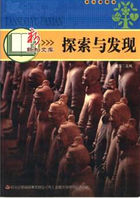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实物幻影”的现象。这些幻影就像从一件事物最外层表皮剥离的薄膜,在空气中四处漂浮。这些幻影在我们不能入睡时和我们遭遇,使得我们心生恐惧。即使在睡梦之中也是这样。我们似乎时常看见死者十分古怪的身影,以至我们惊恐而醒。也许我们会认为灵魂已经从地狱里逃了出来,并且在生者中间翱翔。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实物的假象和淡薄的影子是从实物表层脱落下来的。这些形象幻影可以被称为事物的皮。因为这些幻影具有和发出幻影的物质实体非常相似的样子以及形状,就像知了在夏天褪去薄薄的蝉衣,牛犊生下来时从其外层脱去胎头羊膜。一个淡薄影像也必须从这些东西表层脱落,因此就会出现影子固定的形状和精细的纹理。它们四处翱翔,但是单个却看不到。不管我们在镜子中、在湖水里、在任何光亮表面看到的是多么相似的影像,既然其拥有与那些东西高度一致的外形,其就一定是由那些东西脱落的幻影构成。因此,存在着实物的淡薄模糊的影子和相似的假象,不过没有谁能够个别地感知其存在;然而其被持续不断的排斥力反弹回来后,就从镜子表面反射出具体影像。
……
似乎也没有某种办法可以保存这些幻影,以反射彼此十分相似的形象。实物的最外层表面总拥有某种东西流溢而出,以供实物发射幻影。幻影遇到某些东西会透过去,特别是玻璃。一个形象可以在镜子之间传递,因此常常能得到许多个幻影。不管在房子内部隐藏什么,不管其间通道如何迂回、曲折和隐秘,依旧可以借助一些反射镜通过复杂的通道将房子内所有事物尽皆显现出来。形象在镜子间显示的就是这样真切。无论把什么东西浸在水下,其看起来似乎都是折断而弯曲,在上部变平,好像弯了回来。当风儿裹挟着零碎的云朵穿越夜空,闪烁的星光似乎擦着云边滑了过去,在云上面朝着与云朵真正的运动路线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迅速移动。
卢克莱修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其不符合现代科学理论就将其视为绝对错误。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善于在不同观点之中寻找真理隐藏的位置。光学专家们一定会严厉地批判卢克莱修这套见解缺乏有关于折射、反射的最基本的几何学常识。然而这些只知道从几何学角度研究光学现象的所谓专家们似乎彻底地遗忘了量子物理学对光学的最大贡献: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
20世纪初叶的量子物理学革命从本质上证明了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实际上是一种波——既具备了粒子的个体属性,又可以借助于用来描述机械波的方程加以完美诠释。各种折射、反射现象虽然可以被看作符合几何原理的光波运动,但其本质上还是由光子的集体行为所引起。科学家只会教育我们太阳散发出的一束光被一汪湖水反射因而在湖中留下了太阳的影子,却从来不愿告诉大家上述过程中伴随着物质的“亲密接触”,即光子与湖水外表面的接触。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定光学现象仅仅是纯粹的几何学问题,却从未思考这种“亲密接触”可否引发物质交流,比如物体表层的部分粒子随着光子离去,像脱膜似的进入空气里居住。非常有意思的是:上述种种科学家至死不愿意考虑的思路恰能说明许多视觉心理学问题,比如水晶透明体的意识催眠作用,抑或在神话中经常述及的镜面自我着魔。普鲁塔克在《道德论之漫谈录》(Table Talk, VIII of Moralia)这部作品中就曾介绍过后者的情况并进行了稍显粗糙的解释:
自我着魔通常是由大片水面或其他镜状表面反射的粒子流所引起的。这种反射像蒸汽一样升腾而又回到观者身边,因此有恶毒眼光的人会被他自己用来伤害别人的同样方式所伤害。在小孩子身上发生这类事情时,往往应该归咎于盯着他们看的人。
……
一次在席间谈起据说眼光恶毒且能施妖术的人。大家无不认为这些事纯属无稽之谈,因而嗤之以鼻。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弗洛鲁斯(Mestrius Florus)却宣称:现如今已经掌握的客观事实惊人地支持这种普遍信念。反倒是有关客观事实的报道通常遭人摒弃,只因为其缺乏合理解释。但是根据其他无数我们仍未找到合理解答却不容质疑的客观性事实来看,拒绝考虑这类事情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上文提及了“粒子流”。该词说明这位德尔菲神庙的大祭司并没有像许多近代科学家一样将光当作一种波来研究。似乎古人很清楚光其实是一种粒子,至少具备了粒子的个体属性。我们确实应该对此感到惊讶:难道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也曾经取得过量子物理学成就?难道说他们在类似领域之中的探索征程比发现波粒二象性还不足一百年的我们更加长久?难道说他们是因为某些我们还未发现的物理学知识才会使用在我们看来如此荒谬的理论去解释奇妙的海市蜃楼?我们其实应该意识到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仅仅是一种假说,一种不能正确解释全部现象的假说。然而古人却成功地解答了几乎所有问题;他们曾经断言说:宇宙即是和谐音(Musica Universalis)。
7.和谐音——宇宙的密码
我们在第二章留下了一个重大问题还未解决:为什么说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是宇宙间最大的秘密?现在是回答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了。不过在回答该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行理解究竟什么叫做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
事实上,音差常数(和谐音程常数)对于学习音乐的人而言不算陌生。因为其涉及到两个最常见的乐理知识:八度音程以及五度和弦。在钢琴上每连续弹奏八个白键便会回到初始的音符,只不过高了八度。相差八度的两个音拥有一致的名称和音色,而振动频率则刚好差一倍。在原则上,可以人为地将音符频率不断加倍从而得到一系列高八度的音符。然而差八度的两个音符在一起奏鸣却并不能够让人感到悦耳。于是乎古代的音乐家们试图寻找更加令人心情愉快的组合,他们因此而发现了五度和弦。所谓“和弦”,其实是指同时弹奏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音符。在所有和弦当中,钢琴上每隔开五个白键所弹奏的声音最为悦耳动听。这是种普适规律。
而毕达哥拉斯及弟子经过研究发现:五度和弦作为最容易打动聆听者的音乐形式竟然存在着魔术一般令人难以置信的最简单的纯粹数学比例关系!对于任意两个能够组成五度和弦的音符来说,其弦长之比(或振动频率之比)总会显现为严格而规律的二比三!而该比例恰好是古埃及祭司在各种宗教壁画中以及古代中国人在《易经》体系里曾反复描述的“阴阳和谐”!似乎音乐并不是一种简单而无规则的振动发声,而是被宇宙间某种最精确的规律所支配。不过这种规律显然存在着内部矛盾,因为其中最简单的两组比例关系,亦即八度音程中的二比一以及五度和弦呈现的二比三,竟然不可以通约!当人们想要跨越八度弹奏五度和弦时,就会发现音阶规律突然被打乱!八度音程和五度和弦竟然没办法共存!正如弗洛拉·莱文女士(Flora R. Levin)在研究古希腊音乐思想时曾经描绘的这样情况:
毕达哥拉斯对宇宙和谐音的分析导致了不可通约数的发现。不管他们可能将这些数字如何排列比较,不管他们将其拐弯抹角的数学论证可能推进到何种地步,事实依然不存在把全音分成相等两部分的分数m/n。至今这一事实仍然未能从数学上给出任何合理解释。
音乐领域中这一如此根本的矛盾日后被一名中国贵族予以圆满解决。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嫡孙、号称“律圣”的藩王朱载堉于万历十二年证明了理想均律音阶的音程可以人为地修剪去二的12次方根,并基于此项发现而创立了着名的“十二平均律”。不久之后,荷兰传教士将此体系介绍到了西欧国家,并迅速赢得了广泛的采纳以及认同。李约瑟博士甚至将其称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巴赫的诸多作品正源于这位“圣人”的伟大贡献)。
然而朱载堉是不是圣人并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话题。“十二平均律”也仅是帮助音乐家造出了无须每一次变调都需要调弦的钢琴。至于为什么音乐中最为基本的两组比例关系不能够共存,智者们依然抓不住头绪。不过,毕达哥拉斯作为提出此问题的哲学家,确实曾做出过无比绝妙的尝试。他试图通过无限倍增寻找两者的“最小公倍数”。这种尝试使得他最终发现:从同一个指定音符出发,跨越七次八度音程或12个五度音程能够近似到达同一个音符!若借助数学的语言帮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将某个音连续地提升七个八度,最终会到达相当于原始频率128倍的位置,即二的七次乘方运算;而该原音连续地提升12个五度音程后,即1.5的12次乘方,同样能到达原始频率的128倍。唯一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跨越七个八度到达的128倍是精确的整倍数;跨越12个五度音程收获的128倍却只是个约数。12个五度音程其实仅能引导人触及原始频率的一百二十九又四分之三倍!这两个倍数的细微差别即是毕达哥拉斯音差:129.75 ÷ 128 = 1.0136(一般情况下取其小数部分0.0136)。
大多数人或许会问:这个源自音乐中的常数又具有哪些现实意义呢?难道其不是仅仅说明音程的问题吗?事实上,就连许多自以为见多识广的数学家也倾向于这样认为。他们并不知道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其实是宇宙间堪称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时常不假思索地认定这个数字不过是音乐领域里的发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这个数字的观点倒是非常鲜明:这即是宇宙万物的答案!
古希腊数学大师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在自然哲学家眼中较之毕达哥拉斯常数“看上去显然更加基本”的科学常数都与这个数字有着最本质的联系。数学王国里最重要的圆周率以及量子物理学领域中“独领风骚”的测不准系数实际上恰好是该常数的简单函数。这种现象说明宇宙间最重要的参数在本质上有且只有一个;正是该参数以不同形式严格地支配着一切表观的法则。正如牛顿所宣称的那样:宇宙是一座精准的大钟表,而上帝则是一名藏在幕后的钟表匠!至于这个最核心的宇宙参数究竟是哪一个,罗伯特·坦普尔确实拥有着一套超凡而独到的见解。这位渊博的科技史学家向人们指出:最核心的参数体现了测不准原理的本质原因!由于人类总借助于模型对客观世界进行观测和解释,因此理想和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系统的差别。五度和弦是人类审美模型的筛选品,故而与作为乐器固有属性的八度音程难以完全协调;两者间的差别(即毕达哥拉斯常数)实际上是真实世界与人类认识手段之间固有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具备了惊人的普适性。罗伯特·坦普尔在其作品中委婉而不失坚定地写道:
如果将圆周率之尾数乘以10的较低次幂运算的通用测不准系数如0.09604,就会得到毕达哥拉斯常数的细量。(0.1416×0.09604=0.0136,0.1416是圆周率3.1416的尾数)。据此我们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常数细量是圆周率尾数的函数。
……
就圆周运动来说,可以将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和圆周率看作是同一现象的两个用数值表示的不同方面。根据基本数学原理,这又意味着,对于所有圆周运动来说,表示宇宙间一切圆周运动最微小的数值偏差的系数是其固有的,可以将它们理解为实在之基本构件。反过来又可以将其视为任何体系原点测不准的结果,即那种我们在几何学中应用的虚构的“点”并不存在的结果。这种“点”只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真实世界,其实际上有一定的大小,而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限小。因此,这才是理想和现实两者间拥有的真正差别。
坦普尔令人们信服地解释了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但是他并未说明这种差别为何会具备惊人的普适性。使得他错过深层真理的原因是他并未思考音乐的本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宇宙间所有事物实际上都是一种音乐!因为万事万物究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振动频率,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人类的灵魂。中医里存在一个很古怪的理论,即认为奇经八脉是药物和针灸均难以达到的位置,俗世间只有一种事物有资格进入奇经八脉,而这种幸运的事物就是音乐。根据同性相融的原则,我们大概可以推知音乐与灵魂拥有着相似的属性:它们皆是宇宙间最优美的频率。
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描述的恰恰是频率的不同,而非音色的差异。然而不同频率体系之间广泛存在的难以协调性其实暗示了我们某些最深刻的宇宙学原理:作为乐器本身自然属性的八度音程和作为人类审美规则的五度和弦难以协调,恰恰说明了我们人类实际上在追求一种超越自然的美!
更加重要的暗示是:人类所持有的审美标准似乎影响了客观规律。否则测不准系数及圆周率也不会和毕达哥拉斯音差牵手,共同担当着某种终极隐秘力量的表现形式。该现象从侧面证明了量子力学中有关意识决定存在的假说和推论,也引导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难道眼睛才是宇宙得以存在的原因?
8.荷露斯之眸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永恒的谜。巍峨的金字塔、壮丽的方尖碑、神秘的象形文字,还有尼罗河畔延绵五千年而不朽的文艺气息,尽皆承载着人类内心深处那份最原始的精神冲动与渴望洞穿真理的天性好奇。智慧凌云的古埃及人为我们这些后辈留下了太多深邃谜语,引领着我们不断地进行知识的自我超越,去亲自解答有关于人类和宇宙的终极难题。他们或许是害怕后人在寻访真理的漫漫征途中会出于人类本性的懒惰而自我放弃,于是为我们设计了一条几乎可以解开所有深邃谜语,看上去却又如此之简单的小小暗示: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荷露斯的眼睛”(Udjat, the Eye of Ho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