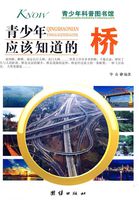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知名儿科专家梅尔文·莫尔斯(Melvin Morse)却将研究对象大胆地推广到了儿童。他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西雅图的一所儿科医院里,由多位不同领域的医学家参与,采用了自然科学研究当中最具典型性的双盲对照法研究了两组患各种疾症的孩子。他还与美国《健康》杂志执行总编保罗·佩里(Paul Perry)合作,先后刊印出版了《趋近光明》(Closer to the Light)、《光之改造》(Transformed by the Light)和《临终视像》(Parting Vision)总共三本书。作者在其书中讲述了许多儿童的濒死体验,通过完美的案例证明了儿童与成人在濒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事物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
而当《临终视像》这本书最终于1994年发布面世时,临床濒死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包括穆迪与梅尔文·莫尔斯等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载入了标准的医学教科书,成为了自然科学王国里的又一重要分支。莫尔斯如是说:
当穆迪博士的着作刚刚出版时,所谓的医学专家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嘲笑。他们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不过就是简单的幻觉而已。25年后,科学证明了穆迪博士是正确的。我所了解的所有相关主流学科都已得出了与穆迪博士相类似的结论。在过去7年里,濒死体验领域,有三种主流观点;无论是哪一种都与穆迪博士最初发现的不谋而合。先行者们从前面对的那些怀疑和敌对的气氛现在已经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在主流科学期刊上发表一篇又一篇有关濒死学的论文。目前在美国的大学,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医学院都已在课程中引入了“精神死亡”的概念。
就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出版后第20年,又一位重量级科学家加入到了穆迪所领导的濒死研究团队。他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着名的精神分析学专家彼得·芬维克(Peter Fenwick)。芬维克与其妻伊丽莎白·芬维克(Elizabeth Fenwick)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名为《光中之真相》(The Truth In the Light)的濒死研究专着,以大量合理设计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基础,讲述了总计350名不同国籍欧洲人亲身经历的濒死体验。作者在这部书里运用自己精深的脑科学知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论证了现代医学所能够提供的各种“科学解释”在试图分析濒死体验时,将会遭遇不可避免的困境和矛盾,一种近乎于古希腊两难悖论的致命矛盾。芬维克夫妇的系统论着,从本质上将那些试图以机械唯物论来解释濒死体验的科学家挡在了这项研究的大门之外。
不过,这种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5.神秘的灵魂脱体
2001年12月,全球医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核心科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篇荷兰心血管外科医生皮姆·范·罗梅尔(Pim Van Lommel)递交的濒死学研究论文。文章内容围绕罗梅尔医生及其同事在1988年至1992年间救助的334位年龄在26至92岁之间的突发性心肌梗死症患者的濒死经历而展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罗梅尔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濒死经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意识脱体现象根本无法通过神经生理学知识予以解释!因为在很多患者经历濒死体验时,他们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即所谓的脑死亡状态;心跳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甚至是已经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脑电波消失,整个神经系统失去了任何生理或病理性电冲动。如果按照现有科学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是经由脑神经的生理电活动而产生和运行,那么当患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时,不可能具有独立于其躯体的意识或者任何类似于思维的活动,更不要说濒死体验报告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系列清醒而有秩序的认知和奇妙感受!
罗梅尔所提出的问题与六年前彼得·芬维克夫妇所讨论的致命矛盾一脉相承。芬维克作为一位全世界顶尖的神经生理学专家,曾经试图通过神经的生理或病理性活动而寻找出破解濒死之谜的科学钥匙。他曾经严肃地指出:人类的右侧大脑主管着思维情绪,左侧却负责掌管语言和记忆分类,由于左右脑在死亡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一致,所以才造成种种难以解释的所谓濒死体验。
右侧大脑的积极参与,使得濒死体验经常会呈现出某种情绪化波动;然而左侧大脑却并未参与死亡的生理过程,因而难以找到适当语言对该种经历加以描述。另外,濒死体验当中有关空间疆界感丧失、时间定向障碍、事件排序错乱(即许多所谓的回顾“同时发生”抑或以“摘要的形式”发生)等都可以归结为右脑较之左脑的参与程度高。芬维克夫妇甚至专门论证了大脑右侧颞叶的某些功能障碍能导致类似体验的发生。
不过,彼得·芬维克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并没有像许多将科学实证之名号看得比科学真理还重要的科学界的所谓专家学者一样,莽撞而不假思索地向全世界高调宣布濒死体验不过是大脑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步调错位;即使他本人确实想通过生理学机制,而非类似于“灵魂”等观点解释这一切。芬维克最终向学术界公布的是另外一项研究成果:大脑不可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成功地建立任何足以产生“体验”的神经反射!即便能够在某些极端特殊的条件下建立感知模型,也绝无可能在事件发生后向人们完整地讲述其间的经过——因为记忆不可能在失去意识的条件下形成!
罗梅尔的研究与芬维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罗梅尔在文章中提及了一位40岁的心脏病患者。此人心脏病突发摔倒在路边草坪。路人看到后,立即叫来了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在救护车上,这名患者渐渐丧失了所有临床医学的生命指征,走入了科学意义上的死亡。罗梅尔在该病人心电图和脑电图已彻底为零后,又继续坚持了一段长时间的“无谓抢救”,并在实施心肺复苏术时将患者口中的假牙摘掉。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该患者恢复了血压和心跳,但是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之中。数星期后该患者重新醒来。他见到罗梅尔医生的时候,感谢了罗梅尔所实施的敬业抢救并告诉罗梅尔他很清楚自己的假牙现在被放在什么地方:
我被人抬到医院时,看见你在那里,将我的假牙从我嘴里拿出并放在了一辆小车上。车上有许多药瓶,车下方有个抽屉,你就把我的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面了。
罗梅尔医生万分惊讶,因为他知道在整个抢救过程中,该患者一直都处于深度昏迷或临床死亡状态,绝不可能有认知能力!而通过进一步交谈,罗梅尔从该名患者口中得到了最为标准的濒死体验模型,即俯视自己在病床上的“尸体”和周围忙碌的医护人员。该患者甚至异常准确地详细讲述了他本人“俯视”急救车和抢救室时所曾发生的每一件事,其中还包括极其专业的抢救程序!罗梅尔不知道究竟该怎样解释。
当然,总会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些都是幻觉”,只不过是“恰好符合具体事实”。为彻底消除这些基于统计的妄断,肯尼斯·林联手心脏外科专家迈克尔·萨博(Michael Sabom)共同设计了一套幻想试验:邀请患心脏病及其他重病的一组病人去努力地想象自己在观察医护人员为病人实施抢救,并将其想象的具体细节完整地描绘出来。
而该试验的结果让叫嚣巧合论的人大跌眼镜:这些因患重病而常年有机会接受抢救性临床治疗的试验参与者都在其描述中犯下了明显的错误!没有人(只要参与者本身不从事医学工作)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抢救的正确程序!这项试验说明:若非曾亲眼仔细观察过临床抢救的具体实施方法及一系列复杂而且有序的步骤,仅凭借在影视剧中所曾经见到的救护情节而展开个人想象,绝对没有一丁点可能将专业的抢救过程描述得如此天衣无缝!该试验结果与濒死体验者所能够提供的精准描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关悬浮于房间上方俯视着自己接受抢救的经历,即所谓意识离体经历,是某种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实。
梅尔文·莫尔斯在其作品《趋近光明》中提到了类似事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为一名63岁的女性实施心脏手术。除其女婿外,患者家属皆赶到了医学中心,静静地守候。尽管该项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在凌晨两点一刻左右,患者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手术小组又奋战了三个多小时,才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清晨,患者的家属被院方告知手术取得了最终成功,但是没有透露手术的细节。
当患者的家属打电话欲告知她女婿手术成功的消息时,这位因故未曾出现在医院里的女婿竟然也有好消息告诉他们。他说,大约是在凌晨两点一刻,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了本该在医院的患者坐在他床头,告诉他不要担心,手术很顺利,并请转告他妻子即老人的女儿,有关她一切平安的消息。
这位睡眼惺忪的糊涂女婿在床头贴士上记下了这一切发生的具体时间及信息的内容,就再度睡了下去。而几天以后,患者从漫长沉睡中苏醒过来所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会是: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留下的讯息?
梅尔文·莫尔斯以及保罗·佩里仔细地研究了该濒死案例的有关经过。他们发现几乎每一处细节都有大量客观证据。他们甚至亲眼见到患者女婿在恍惚中留下的那张便签条,上面的笔记虽然显得歪歪斜斜,但是清楚而明确地写有凌晨二点一刻这个时间,其与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手术档案中所报告的患者心脏停跳的时间完全吻合!意识脱体的奇迹,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在科学时代发生了。
应该说,基于现代生物学的西方医学对于人类生命的了解还极其有限。所有机械唯物观点,无论医学工作者们怎样去把握和修饰,都难以用来有效地解读心灵的内容;更何况机械论本身就拥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及漏洞。马克思时常提醒我们:任何理论皆有时代局限性。而恩格斯为后人们留下的这段话反倒是值得试图解码生命的科学家们去好好地品味:
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然而物质的运动,不仅包含粗糙的机械性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热和光、化学的分解与合成,还包括更高级形式的生命和意识的运动。将高级运动形态还原为较低级运动形态,是注定要失败的机械论企图。
6.难以置信的瞬间康复
1998年夏天,《濒死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Death Studies)刊登了一篇重要论文。这篇文章讲述了一名大约30岁的女护士在其濒死体验中所遭遇的奇特经历。这名女护士约八岁时曾经因为尿血而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在做肾脏切片时,其门静脉竟意外破裂;所幸之后没有发生危险。出院之时,她和父母都受到了医师告诫,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然而到家后,顽皮的她竟然去爬树,结果导致门静脉又一次破裂,她也因此而再度入院。住院输血时,这名不幸的女孩感染了乙型肝炎,致使其病情迅速恶化。几天之后,这名女孩在一片恍惚之中告诉妈妈:自己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久后,她的意识就彻底脱离了她的身体。她依稀感到一条漆黑的隧道。她在隧道中穿行的感觉令她感到很舒适。然而,这对她来说很不寻常,因为她最怕黑暗。这条隧道的另一头,她看到了神秘的光。日后,在接受濒死体验调查的时候,她将这种光描述为了神之力量,即使她从没有信仰过宗教。
离开隧道后,她遇到了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男子,他的形象和天主教堂里那些耶稣的肖像很相似。于是她很好奇地问道:“你就是耶稣吗?”那名男子回答“不是”;继而表示说自己在这里是为了“帮助她”。这名男子告诉她:死亡只是一种选择,她可以选择留下来或回到其身体里去。就在这时,女孩的眼睛竟然能透过那条漆黑隧道,看见守候在医院里的妈妈,真切地感受到了妈妈的情感和内心思绪。
紧接着,她被男子告知:她的肝脏其实能被彻底地“修复”了,但是她的肾脏却没有这种运气。因为她那套患有疾病的肾脏是一种宇宙的“业果”(Karmic Carrier),注定是要跟随着她一辈子。(Karmic一词,其实来源于梵语,意思是“修业”,该词汇一般出现于印度教经文;大致的内容有点类似于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然后她苏醒了,肝脏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医生都感到惊诧不已,认为这种情况无法解释。而等到第二天,医院实验室的各项检查均表明她没有丝毫肝炎的症状,好像从未被感染。
该报道彻底轰动了学界。有关濒死体验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被导向了神秘主义领域。虽然濒死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在高度地警惕着宗教神秘主义的非科学倾向,并不止一次试图在客观科学研究和神秘的宗教式传说之间,划出一道清晰而绝对的界限;但是,新奇现象的不断涌现总是将科学的目光霸道而急切地引向最为古老的传说与宗教。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曾留下的这句名言:
没有宗教的科学难行走,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然而,真正引发人思考的细节并不在于诸如“业果”等宗教神秘主义词汇的出现,这些词汇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地方恰是科学可以去证明的奇迹,比如肝炎症状的消失和不可思议的康复。
而且事实上,濒死报告中近乎于天降奇迹般的生理性改变还远不止以上这一例。很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曾经报告说自己的某些缺陷在“死亡之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肯尼斯·林在《走向终极》里记载的这样一则有关于“视觉修复”的濒死体验:
砰!我离开了。接着,我漂浮在天花板上。在向下看时,我看见了医生的帽子和头。我能分辨出我的主治医师是哪位,因为他的帽子上有特殊的标志。那景象十分清晰生动。我近视得十分厉害,别人在400英尺以外就能够看见的东西,我须走到15英尺附近才能看得见,所以这件事(即看见医生帽子上的特殊标志)令我感到非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