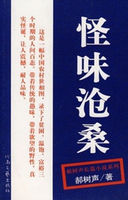如眉听了,暗想她的心思居然和自己一样,世上苦人,原来不是我一个啊。那女子叹了口气,又接着道:“只是这僻静地方很不易寻,不知怎的,心思一动,就决定出家为尼。只又不知尼庵在哪里,便暗地里向张式欧家的仆妇询句。那仆妇以为我要去烧香,使指给一个很有名的尼庵。我去了一看,哪里是清静所在,简直是承宾应客的热门会场啊。我如何住得下去?回到张家,又问那仆妇有没有规矩冷静的庵堂,那仆妇道:”京城里全是这样,便有冷静的,我也不知道,除非我们乡里有个尼庵,倒真清静,可惜太远。”我便问她家在哪里,她说家在郭庄,离京城三十多里呢。我本来愿意远远躲藏,听了十分合意,悄悄问明了路径,谁也不叫知道,个人暗地里投来。这庙名叫普善庵,老尼姑名叫长明,小尼姑名叫能慧,只她们师徒俩同住,倒真正是指佛吃饭,赖佛穿衣,成天际也不念经,也不打坐。有几亩庙产,雇长工种着,收了粮食,足够吃用。再加上村人布施的香钱,倒舒服得很。我来到庙里,那老尼姑原本不收,幸而带着钱,拿出来孝敬她,她才收我作了徒弟,替我取了法名,叫作悦慧。不过总迟延着,还没给我落发呢。”
如眉一面听她说着,一面自己思想:这人和自己是一种来由,她如今总算有了着落,可怜自己尚四顾无家,真还不如她呢。又一转想,自己何不学她,也在这里出家,不为修行,只图得个安身之处。并且看这个人行为颇为爽快,又是同病相怜,若同她一处相守,也可互相解许多寂寞。但既要出家,便须拜老尼为师,听这人的口气,似乎老尼为人不大可亲,应该先把细情询问明白再说,便问道:“悦师姑,你的师傅脾气好么?”那女子道:“说不上好不好,左不过是乡下没见过世面的人罢了。我乍来的时候,她冷淡极了,及至我把钱孝敬她,立刻改了样子,几乎把我当客人看待。那能慧也变成我的丫环,饮食起居全随便极了。方才那情形你还看不出么?”如眉听了,自己沉吟半晌,方才向那女子道:“师姑,我现在飘泊无归,情愿在这庙里修行,求师姑和老师傅指引一下。”那女子望着如眉道;“你何必呢?这家也不是容易出的啊。况且这庙也和人家一样,胡吃闷睡,并不能修仙成佛,你在哪里住着不是一样,何必寻来这苦头吃?像我是为闪开旁人的道路,安慰自己的良心,出于情愿,倒也罢了。像你不过偶然受了刺激,何致平空做起尼姑来?”如眉道:“我实对师姑说吧,我以前造孽太多了,现在件件事都遭了报应,这颗心已经死了,只剩了出家一条路儿,师姑你大慧大悲,千万指引。”那女子道:“只怕老师傅不肯收你,也是本然。”如眉道:“我也依您所说,多孝敬老师傅些钱财,总可以了。”那女子道:“你有钱是容易办,现在她已睡了,到明天我向她说,大约可成。”如眉又深深托付,那女子道:“我们快成一家人了,说话不必客气。我不明白你方才说的造孽太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咱们女子,有什么孽可造?”
如眉想不到她有此一问,若在他时,即便方才失言,经人诘问,也必极力掩饰。但她此际心中似已大彻大悟,对于以前种种,悔恨殊深,正恨不得向人忏悔一下,就很恳切的道:“我说出来你定要轻视我。”那女子摇头道:“咱们都已落到这个场中,谁还能轻视谁?若怕人轻视,我的旧事,也不是说得出的,怎也和你谈呢?”如眉道:“悦师姑,我的名字只要说出,你就知道我的事了。我的名是柳如眉。”那女子愕然立起,瞧着如眉道:“是么?你就是柳如眉?”如眉道:“当日害张式欧的就是我啊。可怜我也落成这般光景了。”那女子只顾看着如眉,却不言语。如眉叹道:“我早料到你听了我的名字就绝不肯理我。”那女子道:“这你却想错了,我并非不理你,只不明白,你真是柳如眉?怎……”如眉情知她是对自己的鼻子和神形都发生了疑问,忙道:“你是瞧我不像么?我本是作恶太多,已遭了劫数。我心中许多苦恼,许多后悔,正苦于没人可说,现在都说出来,也好消些郁气,便是师姑把我立刻赶出门去,我也甘心。”那女子遭:“你若真是柳如眉,我还要替你可怜呢,怎能赶你?你请放心。”如眉道:“师姑真是好人,我若是你,见了我这样混账的人,躲闪还来不及呢。”说着就把自己的身世草草诉说。说到认识张式欧的时节,以及嫁朱上四的前后,就加详了。说到被朱上四凌辱,目下飘泊无归,不由伤心痛哭起来。那女子对她尽心劝慰,等如眉哭住了才道:“你不必伤心,过去的事不想也罢,只要知道以前的事是做错了,立志悔改,就是个好人。你既然无处可去,我定想法教老尼把你收留。不过你方才诉说的,却千万不可对老尼提起,她是不通情理的人,只要晓得你的出身,恐怕一时也不容停留。”
如眉听这女子真是热心,说不出的感激。况且在这穷途之中,更把她看作知心共命之侣。那女子似也自伤寥落,更不嫌如眉来源欠正,倒是十分亲近。二人相对谈心,直到夜午,越觉投缘。那女子又告诉如眉,她原名龙珍,如眉便唤她作珍妹。龙珍也称如眉做眉姐,居然这在尼庵订了交期,直到天明方才同在一床睡了。
次日过午龙珍起床,便去寻那老尼,说昨天的那个姓柳女人也看破红尘,立志出家,要拜在老师傅座下。那老尼不肯道:“她平空前来投宿,谁知道是什么来历。若不是正经人,岂不把咱们的庙都搅乱了?这如何能收?”龙珍道:“昨夜我和她谈了许久,人倒是很规矩,我敢保没有舛错。”那老尼道:“没舛错也不成,咱们庙里通共只十几亩香火她,只够咱们师徒三人吃的,哪能再养活闲人?”龙珍听老尼的话,和当日拒绝自己时一般无二,好似留声机又重唱了一片。不过只有几个字不同,而且也已逼近本题了,当下便道:“我昨夜已和她说过,这这庙里十分清苦,不能再添人口。她说若蒙老师收留,情愿孝敬一笔钱,给庙里置买几亩田地。”那老尼听了,虽然动心,但到底是乡下的老实人,不好意思立刻改口,只可搭讪着道:“不在乎孝敬不孝敬,只是咱庙里地方太小,除了佛殿,只有两间房子,怕没处安置她啊。”龙珍晓得老尼心中已允,忙道:“教她住在我房里就好。她孝敬香火地,虽然是孝敬师傅,实在是孝敬佛爷。师傅看在佛爷面上,也该收留她。”
龙珍这几句话分明是给老尼开路,以为老尼必然就势应允,哪知老尼倒屈了指头算着,自言自语道:“这个年头儿,大贵的地,怎样也得四五十块钱一亩,就算四十块钱一亩吧,买五亩就得二百块钱。啊啊,五亩地真得二百块钱呢。”龙珍听老尼口中捣鬼,明白她这是要价儿,便道:“她也不晓得地价,只说要孝敬二百块钱。”那老尼颜色一变,皱面生春地道:“难得她对佛爷这片孝心,我若不收留她,恐怕佛爷也不容我。徒儿,你去告诉她,只要她守我的庙规,我这出家人本是清静为本,方便为门,一定许她伺侯佛爷。先在庙里住些日子,等我寻出好日期,再一齐给你们落发。”
龙珍唯唯答应,退出通知如眉,立刻拿出二百块钱,送给老尼。那老尼见完全是钞票,还不放心,要和如眉掉换现洋。幸亏龙珍在旁保证,这些钞票绝无舛错,老尼才快快收下,领如眉参了佛像以后,才拜了师傅,认过师兄师弟。老尼又说这不过草草记名,至于正式仪节,还须择期和龙珍一同举行。当下便择定了八月初十日,相距尚有两月,如眉从此才算有了安身之所。虽然未必耽心禅寂,重洗灵魂,但是回首繁华,都成梦影了。
到了次日,那老尼居然入城一次,天夕时才提着个小布包回来,神情欢喜得出奇,龙珍便知她已把钞票换得现洋回来,大约又该安置在炕洞中,一入不可复出了。
果然老尼只当添了一笔私财,绝不再提起买香火地的话。如眉自然更不问她,每日只和龙珍谈谈说说,遣度时光。这庙果然清静,除了每逢初一十五,有乡中妇女结队前来烧香,平常日子,很少人来。便有来的,也是些白发老媪,和老尼谈些米昂盐贵,李短张长的闲话,至于男子,却绝少骚扰,连村中无赖也不肯上门,本来这庙中旧有的老少,两秃生得鬼头怪脸,偶而走在路上,被人遇见,人们还要唾口唾沫,骂声晦气,躲避还来不及。所以这尼庵虽处在寂寞荒村,历来连个造尼姑生儿子的谣言的都绝对没有。由此可见她师徒二人之所以能苦度清修,全由于尊节不堪承教,也就算得天独厚了。及至龙珍如眉到了,又添上一个麻脸,一个缺鼻。加到一处,四副尊容,全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好似在门外挂了一面闲人免进的招牌。
龙珍如眉本不愿见人。因此倒以得其所哉,也不知什么是经,什么是佛,每日睡起便吃,吃完了便同到庙外游览,看看远山,听听流水。或是闲步于陇亩之间,到消遣了许多世虑,但也不免时常勾起感慨。二人虽没有什么诗情书意,不过都是经过磨折的,触景伤怀,却又心情各异。如眉当然入世较龙珍为深,牵缠较龙珍为甚,她有时固也感觉凄凉,但已有些历劫归来,尘心不起的模样。龙珍却只经过一场情劫,脑中只有一个林白萍的影子印着,罔历既少,映象太深,而且她避贤让位,指引白萍和芷华重圆,自己辞甘就苦,离世出家,这些事都是咬着牙根做的。如今回想起来,心头总不免惆帐,也说不出是相思难禁,还是后悔不该,不由地就把心中的百转干回,变成了口里的长吁短叹。
如眉心上聪明,眼中雪亮,又深知龙珍的旧事,自然感觉到她的幽怨无端起先只觉可笑,因为一个麻面丑女,应该自知进退,若再有什么放不下的情怀,自然令人齿冷。但而又很替她可怜,便不断用言语解释。龙珍只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心思,遇有如眉言语说得稍为明显的时节,龙珍还不痛快,说自己已百无牵挂,若是抛不下自萍,当日何必指引他归家。况且现在身在尼庵,岂肯再生杂念?如眉这些测度之言,她认为是诬蔑和侮辱的话。如眉听了,只得付之一笑,以后便不好意思再劝了。
这一日,二人又同到庙外闲步散心。这时已到七月中旬,天气微凉,秋光正好。游览了一会,觉得乏了,便同坐在小溪旁的土坡上面,对着远山遥望,真是苍翠万变,令人游目骋怀。如眉慨然有感道:“想当日我在天津班子里,成天际送旧迎新,哪一件事不用心也不成。生意越好,用心越多,觉得累心极了。有时看见山水画儿,里面的人或是高卧看云,或是抚琴饮酒,就不由生许多羡慕,觉得这种人才算有福气呢,每天无忧无虑,何等舒服,我能修到和画里人一样,就心足意满了。如今我到了这里,地方虽没画里边好,可是身体清闲,不必累心,论理该觉得舒服了。但日子稍久,到了如今,心里已闲得难过,不知什么原故?”龙珍笑道,“你还笑我尘心未净,我瞧你倒有些挨不住了。”如眉“呸”了一声道:“说着说着,你又没好话了。我这是忏悔的意思。提起当日用心虽多,只是没用一些好心,除了倾人害人更无别事。所以如今遭了报应,老天教我落到这种地方,空怀着许多机谋,没处去用。论起我以前所作所为,早就该死。上天只给这等刑罚,还算有好生之德。”龙珍道:“你对于以前的事,能不想起最好。现在咱们虽没落发,也算出家人了,心里若胡思乱想,被人知道,岂不笑话!”如眉道:“我说了什么,你竟赖我胡思乱想?”龙珍道:“你以前听我偶而唉声叹气,就赖我胡思乱想,今天不许我冤枉你一两人说笑了一阵,忽见远远一块墓地中有几座坟都已生了荒草,只一座黄土犹新,想是新埋的。有几个男女,正在坟前烧纸叩拜。如眉看了叹息道:“人家都有父母,虽然死了,还有坟墓可寻。我从小儿就不知道父母是谁,他们是死是活,更不知道,想起来真叫人难过。”龙珍道:“我也和你一样啊,从小就跟着胞姐度日,向未见过父母的面。姐姐又不正经,才落到这般光景。看见人家烧钱化纸,不由起了傻念头,便是我父母死了,能给我留下一个坟头,容我叩拜,也算稍尽孝心,比这踪迹不知的好多咧。”
二人正在叹息,忽见那一般上坟的男女都上轿车走了,只剩下飞扬的纸灰。另有一张没烧的纸,被风吹到土坡之前,挂在树上。龙珍仔细一看,竟是张报纸。便跳下土坡。前去拾取,见那张报纸已很陈旧,上面还有油渍的痕迹。想是包裹祭品来的。看上面的日子,还是前一个月天津的报纸,便拿着走回如眉身边,道:“这些日真闷死,一张报也见不着。这张旧报纸,也可以看着解闷。”说着又坐在地下,看起报来。如眉道:“您念给我听听,别只一个人心里明白。”未说完,已听龙珍惊叫道:“真巧,真巧,这上面还有你的事情呢。”如眉愕然道:“真的么?我不信。”龙珍道;“不信我念给你听,那朱上四正捉拿你呢。”说着就念道:“朱上四悬赏购拿逃妾启事,启者:小妾柳如眉,年才花信,身长腰细,皮肤白色,长眉细目,小口无鼻,天津口音,微带京腔。该妾素不安分。于本月十九日携款潜逃,谨悬赏缉拿。此人缺鼻标识,最易辨认。如有捉护送至舍下者,酬洋二百元。闻风报信,因而拿护者,酮洋百元。储洋以待,绝不食言。”如眉听到这里,想起自己被朱上四害得如此可怜,他还诬赖自己携款潜逃。这样登报张扬,真是恶毒到了极点。自已有朝一日,再遇见朱上四,定要食肉寝皮,才消心头之恨。想着气得一阵发昏,不觉晕了过去。龙珍一看大惊,忙抱她坐起来,从旁高声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