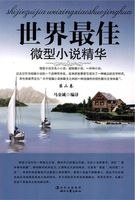尽管匡嘎恩其派出好些士兵半夜三更到城内寻找,答应重奖可以取出杨嘎岩宝喉咙里炮弹的人,但几个小时后,仍然无人前来问诊。匡嘎恩其下令,即使绑也要绑几个人来。人绑来了,但看来看去的,谁也不知从哪儿下手,毕竟生命攸关。杨嘎岩宝终于在大家的一筹莫展中死去。
人巳殁,一帮兄弟在悲伤叹息一阵后,只得准备后事。匡嘎恩其吩咐冥器店老板的儿子,一个名字叫合金的士兵到城里挑选一副质地较好的棺材。棺材很快买来了,四根古木的底,帮子宽大高深,油漆锃亮,有着千年屋的宏大气派和富丽堂皇。大家不禁又一阵悲伤。但有个铁匠铺的伙计,长得圆腰大膀,力大无穷,平时与杨嘎岩宝最要好,喜欢一起赌,赢了也任他泼皮癞输。杨嘎宝应也乐得当他为一种依靠,俩人搭兄结友很是合适,难以离分。此时却是爱极生恨,他怨怼杨嘠岩宝不该撇下他先走,成为没有家园的野鬼孤魂,于是不等大家动手,便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几分蛮力莽劲,一手将他的双脚提起,朝着棺材猛丢。岂知他这一甩一掷的,震动过大,那颗铁丸居然从喉咙滚出口中,掉落下来。田嘎岩应一口气吐出,活了过来。他看着面前的棺木棺盖都欲合了,嚎啕大哭。之后见大家笑得要死,他也破涕为乐,做一个鬼脸,自嘲说阎王嫌他年小,捉住也放回不收了。
“下次干仗老子也不怕了,反正阎王捉住老子也不收!”他又重复地说。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议论一阵,把此事当作了一件奇闻轶事开心。匡嘎恩其并不觉这件事好笑,他接着吩咐大伙,将这口棺材抬到了城楼上,放到了最显眼的一个位置。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一次的战争凶多吉少,而他,也决定要带着这口棺材冲锋陷阵了。
那些炮声、枪声、厮杀声、孔叫声不绝于耳,风声凄厉地上天入地,镇江的天空既使到了夜晚也依然是残阳一般的殷红血色。
天快亮的时候,外面难以捉摸的局势已隐约可见了。敌方如期而至,近万名毛贼踏过成千的尸体,直奔到城楼之下,架起长梯攻城,大有雀占凤巢之势。这时,匡嘎恩其命令各部把守好关口要塞,上来一个杀一个,自已则开率一干人马,从东门和西门冲出,一阵猛杀。敌人不知对方兵力,迫于一种气势,一边应战,一边后退。交战不到半个时辰,巳败退很远。匡嘎恩其知道此时一点不能露出自已兵少人稀的破绽,让对方掌握自己的弱点,又只得号令兵马回城,以备再来再战。
而敌人像在有意地拭探,来来去去,不温不火地交手。匡嘎恩其巳意识到了这样下去的危险性,他开始期待从别处赶来的援兵。但到了第二天,出去搬援队伍的兵勇回来,说后方也是战事吃紧,一时抽调不出兵力,让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守住镇江。这样一来,等于是要他们孤军奋战了。
既然无望于别人,也只能依靠自己了。匡嘎恩其又一次登高察看了一下地形,发现四周宽广平坦,有一些小丘,也不过鲤鱼身上的粼片。敌众我寡,他决定下令,任何敌方的引诱挑战,都一概不理,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进来,就与他们短兵相接,决一死战。他又加固了工事防备,备足弹药以待使用。
午饭过后,那伙毛贼又开始鸣锣击鼓,甚嚣尘上,并将大炮支起,对准城门,似要炸开。如此相侍了一阵,匡嘎恩其觉得有必要发制人,给对方以打击。“有种的就放马过来,给老子打!”他命令道。
一发发开花炮弹在敌人的阵地轰炸,后面的毛贼跟着就倒下去一大片,有些炮弹击中了对方大炮,那些大炮便七零八落,成了哑巴不再开口。对方一时慌了手脚,情急之下也开始对打。战火纺飞,震耳发聩。被炸开的泥土一时间变得焦黑,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此时骄阳似火,热浪翻腾,真让人忍无可忍。而那些毛贼,像受到某种驱赶,仍然蜂拥蚁附一般向城楼靠了过来。
兵临城下,巳有了许多危急,匡嘎恩其只得又急中生智,引燃火药包往下丢去。那些毛贼被炸得鬼哭狼嚎,作鸟兽状又一并散去。但这种情形并未持久,敌人的一颗炮弹打来,正好打到了城门上,炸开了一个天窗,紧接着又有一发炮弹落地,几个士兵倒在血泊之中,饮弹身亡。城内的兵勇一时慌乱,上前去堵,但不济于事。外围的敌人又蜂涌而至,从天窗往里扔石头、砸门、撞击。铁门隆隆作响,抖落着身上的铁尘粉屑。
“也许我们该撤退,”一位将士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又有一个军官报告了匡嘎恩其情况危急,并问他该怎么对策,是否可从另一侧门撤走,暂时放弃镇江。匡嘎恩其沉思片刻,说可以让浴血奋战后幸存的士兵突围,这既不是败退,也不是出于苟且偷生,而是出于自己有责任对家乡子弟的爱惜和保护。但他的士兵却愿意与他一起同甘共苦,孤注一掷,哪怕全部战死!他们这时对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认了,也不再感到惊慌,而是众志成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那天,匡嘠恩其做好了以一挡十伏尸百步的准备。他将所有官兵招集拢来,然后宣布,如果能守住镇江,与镇江共存,侍这一次战斗结束,每人赏银五百两,战死者抚恤一千两。
“但请你们,一定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接着又说,却一边感到了自己生命线的脆弱。
七月里的这一天晚上,敌军终于撞开城门,残酷的战斗已成了可见的事实。匡嘎恩其甩掉笨重的战袍,袒胸露膀,一边喊道:“筸军兄弟们,上!”首当其冲站到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害之地,一边砍杀一边指挥督战。敌人也知道遇上了不怕死不好惹的妄魂之人,真是有些怯阵,因为军中流传一句话:打长毛,还得靠绿营,靠镇筸兵。似乎镇筸兵生来就是他们的克星,遇见他们,就是撞到了鬼。
但这次敌人真是多如牛毛,即使倒下去的尸体,也能堆积如山。而自己的这些将士亦如山上的树,在刀砍斧劈中一根根一排排栽倒下去。
天亮时分,匡嘎恩其清理了一下人数,已死伤两千余人,张嘠文德满身血迹,伤痕无数,致命处为他腹部中弹,肠子流出来了,仍塞了进去,裹伤而战。匡嘎恩其的心已破碎,疼痛如万箭穿肠,他觉得自已愧对他们,很多方面都未达到他们的意愿,却让他们在一次次的憧憬与想往之中为国效命或捐躯。他的牙咬得咯咯咋响,心想不报仇血耻,自己也绝不活着出去。
援军仍然没有到来,城池失守的命运在即,但不管怎样,不到最后一刻也决不放弃,死也要死到最后。匡嘎恩其因为日夜恶战,衣衫被划出许多裂口,血迹斑斑,两只眼晴深陷下去,脱了人形一般,但他的意志更为坚定,目标明确,他再次集中兵力,准备扑向敌人。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炸响,他摇晃着,又强迫站定。有个什么东西穿透着他的胸膛,他觉得痛,汗流满面。一种困乏也席卷而来,他无力支持,在撕天裂地人喊马嘶之中慢慢地倒了下去……
他躺倒在一堆荒凉的瓦砾里。瓦砾突然灌进了淅淅沥沥的雨,炎热似乎过去了,到处飘着冷飕之气。
“大人,大人!”迷糊中似乎听到乃贵的呼喊声。
乃贵在节节败退中仍没有放弃与敌厮杀,但他的马为四周扬起的尘土弄坏了眼睛,不能再战了。他又换了一批马,挥枪砍杀。但敌人源源增兵,他受到重围。他的四周,多有战死的将领,弟兄们更是横尸遍野,力大无穷的铁匠铺伙计也倒在血泊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部。“他们都光荣了,”乃贵哭笑着说,“但老子打了几年的仗,还需要让狗日的敌人架刀脖子上吗?!”他吐了口唾沫,在敌人包抄上来前左手摸着怀里的那对玉镯,感觉一丝微凉的温慰,右手拔剑自戕了。
敌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下来,匡嘎恩其的人幸存者聊聊,但他们在死之前,撂倒敌人无数。最后一个据点是兵营,那些士兵以异常迅猛的动作和弹无虚发的射击,从不同的哨卡和炮楼打完了所有的子弹,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站着,仿佛等待进攻者用大炮将他们与城一起轰平。
但是这次敌人却退出去了,他们突然接到了一个什么命令,说是被援军包围了。有如六月天突然遭到霜降,他们的撤退充满了惊慌与错乱之声:“快走吧!操!”
匡嘎恩其命若游丝。在他模糊的意思中,他想这次定然是逃不过死神的追逐了,曾经,他在死神面前那么嚣张过,不以为然,他想这次会得到彻底的清算。为了对付死神,他咬着舌头,吮吸没有滋味的雨水。不过,他又极度地疲倦,以致很想入眠。隐隐约约,听到曲子的回声,袅袅绕绕,如战后飘动的烟尘。那个吹木叶的兵士在落气之前还用被炮弹炸飞所剩的半片嘴唇为阵亡的将士吹完了最后一支家乡曲。
“呜啊,呜啊,呜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