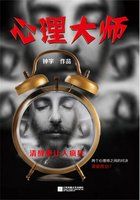瑞年奔下指挥塔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停机坪上,没来得及逃走的十几架日军战机全都淹没在火海之中了,一时间东局子机场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成一片,看着火光熊熊中燃烧着的飞机,官兵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看到瑞年,董山峰赶忙迎上前去,很关切地询问着:
“怎么样,营副,解决啦?”
瑞年点点头,忽然感到周身乏力,腿也软软的,几乎无法自持,要不上手疾眼快的董山峰抢上来扶住了他,他大概早已跌到了。
“营副,你挂彩啦?”
董山峰忽然看到瑞年胸前那一片湿漉漉的血迹,惊叫起来。叫声惊动了营长和官兵们,众人也纷纷围拢上来。
“营副,你别硬撑着,到底伤着没有啊?”
瑞年孤身上塔毙敌的壮举已经将原本对他充满不屑和怀疑的营长彻底服了,也禁不住关切地对瑞年俯下身去。
“我没事,我只是,第一次亲手,亲手杀了一个人。”
营长和董山峰这下全都恍然大悟了,两个人却出乎瑞年,也出乎他们自己意料地没有笑,他们第一次亲手杀死面前的敌人的时候,也有过瑞年今天的感觉,实际上不仅仅是营长和董山峰,在场的很多老兵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战争是残酷的,残酷得让死去和活着的人一样的难以抗拒。
此时机场外围和指挥塔上的敌人已经完全被消灭了,但躲在军营和机修库中的一部分机场守备队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因为敌方火力太猛,而国军突袭机场的部队所携带的重武器又比较少,仅有的一门82迫击炮也只携带了五发炮弹,对于营房和机修库这样比较大的目标根本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加上黑暗中很难辨别目标,因此双方只能这样僵持着,都在等待天明时向对方发起致命的一击。
看看急行军后立刻投入战斗的士兵们疲惫不堪的样子,营长命令除了一部分弟兄负责监视龟缩在营房和机修库的敌人之外,其余的人都撤到敌人火力够不到的停机坪上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1937年7月29日,当国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指挥下,向驻天津的日军发起主动进攻后,除了东局子机场之外,国军同时在天津市内的火车总站、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海光寺、火车东站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最初的战事进展还算顺利,由于日军主力都已调往北平一线,驻天津的日军兵力不足,且事发突然,仓促应战,很快就被国军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日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死伤惨重。但无论是从装备还是部队的战斗力来说,毕竟日军都比国军更胜一筹,所以,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日军开始有组织地向国军展开疯狂的反扑;而与此同时,天津周边的日军部队在接到天津方面的求助信号后,也开始迅速地向天津方向集结增援。拂晓时分,从东局子机场侥幸逃脱的几十架日军战机飞回天津上空,开始对市内各个主要战场和重要战略目标狂轰滥炸,没有制空权的国军一时间暴露在日军飞机的火力之下,战局急转直下。
经过一夜的奔波和战斗,精疲力竭的瑞年和官兵们在梦乡中压根没有想到,此刻,十二架日军飞机正悄然逼近东局子机场上空。当飞机的轰鸣刺破黎明的天空,死神一般降临在东局子机场的停机坪上空的时候,率先惊醒的瑞年还没来得向周围的官兵示警,俯冲下来的飞机已经开始了疯狂的投弹和扫射。一时间,停机坪上一阵阵惨烈的爆炸声和扫射声中,夹杂着受伤和垂死的士兵们的哭嚎和怒骂,硝烟和火光中一片片血肉横飞,开阔的停机坪上,几百国军官兵无疑成了日军战机的活靶子。那是一场让瑞年终身难忘的杀戮。他看到无数的官兵被炸弹撕成碎片,很多人还没来得及从睡梦中醒来,就已经被密集的弹雨打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瑞年被眼前这从未见过,甚至难以想象的血腥场面惊呆了。他跳起身来,挥舞着双枪,大声吆喝着四散奔逃的官兵们,试图让大家尽快寻找掩蔽处,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但却无济于事。瑞年只觉得周身的血渐渐地冷了,在一片弹雨和硝烟中,他茫然地站在那里,声音已经嘶哑,脸上流淌着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双臂还在盲目地、机械地挥舞着,视野中那些倒在血泊里和正在倒下去的官兵们的影子渐渐模糊起来,瑞年绝望地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大吼了一声:“射击!”抬手向一架向着自己俯冲下来的敌机疯狂地扣动了扳机。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在距离瑞年不远处炸响了,一股强烈的气浪排山倒海般地袭来,瑞年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一般飘摇着飞了出去,悠悠地像是一只巨人的手掌拂过,把他抛向半空,又重重地丢在了地上,五脏六腑在强烈的震撼中似乎纠缠在了一起,绞痛却只是一瞬间,瑞年眼前一阵白雾泛起,迷茫、缥缈,掩盖了他的世界,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瑞年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鼻腔中充满了强烈的火药、血腥和人肉焦糊的臭味。当空的太阳正透过尚未消散的硝烟,火辣辣地烤着他的身体。瑞年挣扎了一下,周身几乎没有一处不感到疼痛的,尤其是胸口,针扎一般。瑞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伤了,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一切。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让自己僵硬的脖子能转向一边,去查看周围的情况。瑞年终于看到了倒在自己不远处的营长,半边身子已经被炸飞了,血肉模糊中,内脏洒了一地。瑞年只觉得胃里一阵痉挛,翻滚着有一股黏稠的胃液涌上喉头,一张嘴,“哇”地吐出来一股绿色的胆汁,他一下子闭上了眼睛,不敢再去看那血腥惨烈的场面。稍稍平复了一下,瑞年把头转向另一边,慢慢地再次睁开眼睛,依旧是惨不忍睹:一个士兵倒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胸前凝着一片已经发黑的血迹,大睁着一双充满迷茫的眼睛,眸子已经泛出了浑浊的白色;在他脚下,另一个士兵俯卧着,一动不动,背上刺眼地插着一块黧黑的弹片,很宽,很长,想必是贯穿了他的胸膛;再远一点,一个几乎被削去了半边脸的士兵身体扭曲着,一双脚已经完全被烧焦了,冒着缕缕蓝蓝的余烟。瑞年的胃里又开始翻滚,他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了,紧紧地闭了眼,缓缓地有泪从眼角上伸出来,瑟瑟地爬进了他的鬓间。那一刻,瑞年多想嚎啕着大哭上一场啊!忽然,不远处传来两个巡逻的日军士兵朝着瑞年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瑞年周身的肌肉紧绷了,一时间忘却了刚才的疼,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下意识地去摸腰间的枪,空空的皮盒,盖子敞开着,他那支“王八盒子”却早已不见了,左轮枪也不知了去向,瑞年心里遗憾和懊悔不堪,现在倘若那两个日本兵走到他面前,他真的只能坐以待毙了。
两个日本兵走过瑞年的身边,其中一个忽然停住了脚步,在瑞年面前驻足不前,微微阖了眼的瑞年脑子里掠过一片绝望,如果面前的这个敌人发现了他还活着,那么赤手空拳的瑞年也只能任人宰割,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喂,你看,这家伙的枪套,是我们的南部十四年式!”
听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日本兵这样对他的同伴说,瑞年的心里略微松了一口气,显然敌人还没有发现他是在装死。
“哦?真的,他怎么会有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枪?”
另外一个日本兵在瑞年的身旁蹲下来,伸手拨拉了一下瑞年腰间的“王八盒子”的皮盒。
“这简直是对皇军的侮辱!”率先发现瑞年腰间枪盒的鬼子也蹲下身子,“不行,我要把他拿走,不能让这头支那猪带着我们皇军的手枪去下地狱!”
鬼子的话让瑞年心头的怒火一下子升腾起来,而他那只伸向瑞年腰间的手更让瑞年充满了愤恨,那是一只沾满他的弟兄,他的同僚,他的人民们的鲜血的手,那是一只狂妄着企图奴役整个中华民族的手,那是一只应该被无情地看下来,再剁碎了的魔爪,瑞年终于不能再这么苟且偷生地忍耐下去了,倘若那两个鬼子不是以为躺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具尸体的话,他们应该能够看到面前的这个挎着日军手枪皮盒的国军军官的牙倏然间咬紧了,在腮间鼓出了两道肉棱子,惨白的脸上透露出强烈的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