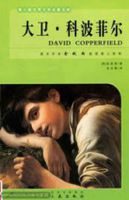江南城的车子还没开到大院门口,警卫就已经自觉的放了行。陶夭夭暗忖江南城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让他的拉风跑车跟挂了军用牌照似的畅通无阻,这也是她为何每次回家都和江南城约好一起的缘故。如果打出租,大院里的一长段路显然是需要她自己走的。
两人从小便一起在大院里打闹撒野着长大,对于这里没有丝毫陌生感。偶尔回来,感念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变化。
江南城把车停在了陶家旧宅门口,同陶夭夭一起进了院落。
“你不先回家?”陶夭夭看向跟她一起下车的男人,眉目带笑。
“先去看爷爷吧。”江南城随口回道,“我给我家老太太汇报过了。”
陶夭夭了然的点点头,环顾四周的一草一木。
宽敞的大院里搭着古旧的白漆木架,色彩已经剥落,葱茏欲滴的葡萄藤蔓却如新生长,宛若顺势倾泻的瀑布。而果实,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尝到。白墙红瓦,就连每一块石砖上都留下过斑驳的曾经,似乎还能忆起那一双小脏手拓印在墙壁的痕迹。青色石缸里早已没了童年记忆中的红色鲤鱼,却依稀可辨那缸底的青润苔藓,好像静默生长了数千年。
“今年的杜鹃花倒是开得比往年旺。”陶夭夭随手摘了朵故作恣意的插在头上,笑眼弯弯的回头望。
江南城眯了眯眼角,看着前方半步的女人。
她几乎见证了他所有的成长历程,穿开裆裤的、剃锅盖头的、握着一根筷子叼炸酱面的、满脸脏兮兮哭着鼻涕的、害怕挨打跟妈妈撒谎的、偷偷藏起一包“熊猫”学抽烟的…所有的他她都见过,对她而言,他没有秘密,反之,亦然。
可是,眼看着她的生活中突然多出个容斯岩,江南城觉得这种原本牢靠得坚不可摧的平衡关系一下被打破,变得脆弱不堪起来。他有些不乐意,或者,只是不习惯。
陶夭夭这个女人,早晚会嫁人的,他早晚都要彻底习惯。
江南城心中暗忖,眉心不自知的蹙了蹙。
“你这孩子,一回来就搞破坏。”刘仪看到女儿随便折了花,张口埋怨起来,转而冲着江南城眉开眼笑,“小城来啦,真是好久都没见到了。”
眼见妈妈对两人的态度过于迥异,陶夭夭似有不满的撇撇嘴,听到一旁江南城大尾巴狼似的恭敬回答他最近有些忙,是有段日子没回家看看了。
发现自己完全被忽视,陶夭夭不甘心的嘟哝道:“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妈,这可是您教我的呀。”
“你这孩子。”刘仪故作生气,“怎么不记得我教你的前两句?”
陶夭夭狡黠的吐了吐舌头,挽着刘仪的手臂就往屋里走,“哎呀,我当然谨记刘主任的教诲,终生不忘。”
随即摇头晃脑的背了起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嘛。”
“那就抓紧时间给我找个好女婿回来!”
陶夭夭下意识的搔了搔鼻尖,随口换了话题,“诶,陶振川同志怎么不在啊?”
刘仪也没揭穿女儿的心思,白了她一眼便没好气的说:“你爸和你童叔叔去钓鱼了,听说你回来,正往回赶呢。”
“唔,那我又有口福了呀!”陶夭夭一脸激动,讨好似的说,“爸跟我有心灵感应,知道我想吃鱼了。”
刘仪故作不耐的扯掉女儿撒娇似的攀附,招呼着江南城随便坐,一面自行进了里屋。再次出来,手中已多了一个小物件。
“妈,您看咱娘两之间还搞这些虚的做什么?”陶夭夭伸手接过妈妈递来的红色纸包,笑得一脸谄媚,“您老能记得我的生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还送什么红包呀!”
“什么红包?”刘仪愤愤的戳了戳女儿的脑门,一脸严肃,“这是我专门在普陀山上给你求来的姻缘符!”
“…”
“本来方丈大师还开示说,每天早晚念七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便定会求得好缘分,可是我琢磨着你肯定没那心劲儿,还是算了。”刘仪恨铁不成钢似的摇摇头,随即摆出一副不容置喙的表情来,“所以,你以后就把这个符给我好好带在身上,不许丢了!”
“妈…”陶夭夭欲哭无泪,随手从茶几上捡了颗杏子塞进嘴里,“您老到底是有多怕我剩在家里拖累您啊?”
“你这孩子,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刘仪充满宠溺的瞪了女儿一眼,随即笑眯眯的看向一旁看热闹的江南城,“夭夭就是这样,多大了还不懂事,都让小城笑话了。”
“陶姨,您对夭夭真好。”
江南城立马欠了欠身子表明立场,眼中虔诚的闪动着羡慕嫉妒恨的光芒,仿佛刚才幸灾乐祸笑得直发抖的人压根不是他。
“你看,小城都明白我的苦心。”刘仪似是欣慰的找到了拥护者,面目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面对老妈永恒不变的说教话题,陶夭夭嘴角直抽,不知是不是被那青黄的杏子给酸到了,“妈,如果您实在闲得无聊,不如也在家里养只小狗吧?你看我家小三儿,又可爱、又听话,不但能给您解闷儿,还能帮您看家!”
“你少来胡闹!”刘仪断然拒绝,嫌弃似的皱着眉角,“瞧瞧你给狗起的名字,简直是自己咒自己。男朋友还没有一个,倒是养了个小三在家里。”
“妈,您这就迷信思想了吧?”陶夭夭不以为然的撇撇嘴,随即摆出事实依据,“如今这个社会,到哪不是小三遍地?如果男人的心想往外跑,就是在家供个门神看着,买个铁笼子把他关住,也没用!”
“就你有歪理!”刘仪不悦的白了女儿一眼,嘴角却不可自持的向上翘。
“陶姨,您也别太担心夭夭的个人问题了。”江南城突然笑容清俊的安慰,陶夭夭刚打算投给他一个感激的眼神,就听他似真似假的继续说道:“如果她真的没人要了,不是还有我吗?”
“大庭广众乱放什么屁!”陶夭夭恶狠狠的瞪了江南城一眼,咬牙切齿道。
江南城笑而不语,一副“好男不跟女斗”的表情。
“一个女孩子家说话怎么这么没个顾及?”刘仪故作严厉的怒斥,随即将目光投向另一边的江南城,已经变为感怀悲慈,“小城也不小了,你妈也成天跟我絮叨着想抱孙子呢。你们年轻不理解,我们做妈的还不是担心孩子们耽误了现在,将来后悔?要是早知道你们两个玩心这么重,还不如当初就在两家结个娃娃亲,倒是省的我们两个老太婆现在操心了!”
陶夭夭被自家老妈的话噎得半天不吱声,口里跟塞了个鸡蛋似的。江南城只是不置可否的“嘿嘿”干笑,陶夭夭心里不免暗骂他没事找事。
刘仪有心无力的摇摇头,转身端起桌上的茶壶去添热水,似是懒得再提让自己闹心的事儿了。这才想起来提醒,回头看向陶夭夭,“你上次带来的六安瓜片你爷爷尝着直说好,问是哪买的,看看还有剩下的没有?”
陶夭夭一愣,恍然反应,心虚的瞟了眼江南城才说:“妈,你当那是菜叶子呀,说买就买?上次给爷爷带的那些可是我削尖了头才找到的。”
“你这孩子,刚做些好事就邀功!”刘仪没脾气的瞪了女儿一眼,“我当然知道现在瓜片难买,所以才问你还能不能托人找到嘛。”
“阿姨,我倒认识个朋友,兴许现在还能存着些。”江南城一脸恭谦的看向刘仪,笑眯眯的说,“我去问问,如果有就让人给爷爷送来。”
“诶,那就麻烦小城了。”刘仪连连欣喜的点头,随即无可奈何的感慨道,“还是我们小城办事稳妥,我们家夭夭啊,成天就知道耍嘴皮子,都要气死我了。”
“妈,您到底是有多口是心非啊?”陶夭夭无力的翻了个白眼,仰天长啸,“天天说我惹您生气,那您还巴巴的盼我回家?”
“你这屁孩子。”刘仪伸手作势要打,虚做了个架势又小心翼翼的将手中托着的茶壶递给她,“你爷爷在后院乘凉呢,把水给他送过去。”
“遵命,老佛爷!”陶夭夭嬉皮笑脸的摆出一副从命的姿势,随即赶在刘仪作势又要打她之前,拉着江南城向后院逃去。
身后传来刘仪故作严肃的嗔怪,陶夭夭不以为然的回头做了个鬼脸。看着妈妈无可奈何的摇头进了厨房,才慢慢正经起来。
“拿着!”陶夭夭将紫砂壶丢给了江南城,恼怒的白了他一眼,“马屁精!”
江南城脸上温润的笑意早就被狡猾所替代,冲着她得意的挑了挑眉眼,“你还好意思说我?借花献佛也就罢了,还不允许我偶尔表现一下啊?”
“是你说做好事不留名,甘愿以我的名义孝敬爷爷的。”陶夭夭伸直了脖子反驳,理直气壮的表情,随即又扯出一抹安抚似的笑意,“哎呀,反正都是为了哄爷爷开心,我们谁送不都一样?”
江南城冷哼一声,也不和她计较,嘴角的弧线倒是更弯了。
陶夭夭远远就看到坐在大槐树下的藤椅上慢慢摇晃的老人,撒腿扑了过去,甜腻腻的唤了声爷爷。
“夭夭回来啦!”陶胜怀抬手摸了摸环着自己脖子撒娇的孙女,乐得眉开眼笑,“怎么好久都没回来看爷爷,是不是都要把我这个老头子忘掉了?”
“爷爷,我这不是来看您了嘛!”陶夭夭将脑袋在爷爷的脖颈上蹭了蹭,猫咪似的欢快,“我昨晚都梦到您啦!”
陶胜怀连连点头说好,看到已经站在一边的江南城,蒙着几分沧桑的眼尾一亮,“小城也来啦!”
“爷爷。”江南城也不似平日里面对其他长辈的有礼有度,倒带着几分难得的孩子气,故作淘气的说:“我昨天也梦到您啦!”
“你们这两个小鬼呦!”陶胜怀充满宠溺的指着面前的两个晚辈,笑着向躺椅背靠去,“就会拿我这个老头子寻开心!”
“爷爷,我是真的梦到您了。”陶夭夭连忙强调,随即摆出一副要跟江南城划清界限的嫌恶表情,“江南城是骗你的啦!”
“你这孩子!”陶胜怀似是责备的点了点陶夭夭的额头,才看向江南城笑眯眯的说:“小城来了就陪爷爷下会儿棋吧,周围那些个老家伙儿水平太差,我都懒得和他们玩儿。”
都说“老小孩”,年纪越大,反而越孩子气起来。有了小孩子的脾气,也有了小孩子的天真可爱。此时的陶胜怀,哪里还像是曾经随便瞪个眼也能让整个军区震三震的老首长?
江南城一听,赶忙将一旁的小木桌子连同上面的棋盘一起搬到了陶胜怀的椅子前,陶夭夭也乖巧的搬了两个板凳过来,如同过去的很多年一样,自己坐一个,递给江南城一个。
在陶胜怀眼中,从没把江南城当做是别家的小孩,跟陶夭夭一样,都是自己的亲孙子。以前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他们四处疯玩。看着两个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都有了出息,他心里乐腾着呢。
陶胜怀端起一旁有些年头的茶壶“呼噜噜”的喝了一口,老树枝似的手指轻轻敲击在扶手上,餍足的闭着眼睛喟叹道:“这样的好茶,现在不好找呦!”
“爷爷,要是您想喝茶,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陶夭夭理所当然的说,拍着胸口保证,“改明儿我就把瓜片送来给您备着!”
“你这个小鬼头,小城帮着忙活,功劳都被你占喽!”
被爷爷当众拆穿,陶夭夭不可思议的瞠大了双眸,“爷爷,您怎么知道的?”
陶胜怀哈哈大笑起来,揶揄的瞅了孙女一眼,才说:“爷爷是老了,可还没傻呢。就你那点小九九,能有本事讨来这样的好货?”
“爷爷瞧不起人!”陶夭夭不满意的叫嚣,随即便心虚的搔了搔脸颊,低头看爷爷和江南城下棋了。
陶夭夭和江南城的棋艺都是陶胜怀教的,可是,如果说江南城是他的得意门生,那么陶夭夭就还处在未出师的阶段上。所以,通常陶胜怀要是技痒,也都是和江南城切磋,向来轮不到她陶夭夭。
用爷爷的话来说,就是“水平太差,我都懒得和她玩儿”。
陶夭夭安静的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个轻轻眯着眼角,一个淡淡噙着微笑。明明是相差了那么长的岁月间隔,可是,举手投足间,却都充盈着相似的淡定与从容。
阳光从绿荫中筛滤而下,落在实木桌上形成错乱的细碎亮斑,明晃耀眼。陶夭夭下意识的眯起眼角,看悬在棋盘上空的两只手如何像将军点兵似的一来一回,指点江山。
落下的棋子撞在棋盘形成“啪啪”的脆响,混合着慵懒的蝉鸣,在这个阳光灼灼的恬静后院里上演了一出交响曲。
陶夭夭看的出神,却突然双眼一亮,如同发现好莱坞大片里的穿帮镜头般惊喜,“爷爷,落子无悔大丈夫!”
陶胜怀一愣,想要悔棋的手臂还停在空中,脸上的窘迫就迅速被不满的冷嗤所代替,“你这孩子,观棋不语真君子!”
“爷爷,我可是小女子,观棋可语呦。”陶夭夭冲着爷爷狡黠的眨了眨眼睛,“而且,就算要重走,也不能放这里啦!你这个车一走,马就危险啦!”
说着,陶夭夭指了指棋子的布局,证明自己所说非虚。
陶胜怀恍然点头,立马抬头去看江南城。见对方不过淡淡微笑,仿佛压根什么都没看到,连忙将手下的棋再次改了位置。然后才故作不悦的瞪了眼孙女,花白的胡子一翘一翘的,“我当然知道不能这么走,你这孩子明明不会下棋,还爱瞎指挥!”
陶夭夭故作委屈的撇撇嘴,倒也不敢拆爷爷的台,连连道歉说自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