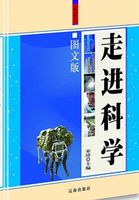叶蕴仪鼻中一酸,点点头道:“还记得,那天知道梅果在我们中间作崇后,我说的那番话吗?我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便连梅果这样的小人,都能无意之中竟令到我们之间的牵系,也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活了下来。如果说,那番话还只是我心中想要为我们能够再在一起,找到一个理由,找到一个安慰自己的借口的话,那么,这个解签人的话,却如醍醐灌顶,令我猛然醒悟!”
她的眼中再次流下泪来:“我们之间的牵绊,何只是孩子?过去种种,办铁矿、开银行、兴经济,振军队,甚至对付日本人,应对南京,应对洋人,哪一样里没有我们共同携手的影子?我们还有着共同的国仇家恨!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爱和恨,都已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去,这样刻骨铭心的牵绊,又怎么能剪得断、忘得了?”
潘启文就那样一眨不眨地,直愣愣地看向叶蕴仪,只见她毫无形象地抹了抹鼻子,含了泪笑道:“启文,当初我找上武辉杰来西南,心底里,何偿不是因着对你的牵绊?爱也好,恨也罢,总是因着这些个东西,才支撑着我能在九死一生中,活下来!如今,随着之前误会的层层解开,我对你的恨也一点点消散,若是连那份爱,你也要拱手丢弃,你让我,还怎么活?”
潘启文眼中的灰霾悄然散去,一丝欢喜滑进心底,迅速地无限膨胀,直至泛滥成狂喜的浪潮,瞬间将他整个人淹没。一层薄雾在潘启文眼中腾起,眼前的人在雾气中恍然虚无起来,他努力地瞪大了眼,想要看清她,然而,那个早已刻进骨血中的身影却越来越模糊,他终是忍不住眨了眨眼皮,两滴温热就那样直直地跌落在她的掌心。
叶蕴仪颤了手,抚上他的眼角,放松了语气道:“潘天一,都说你是混世魔王,怎么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怕了?我还以为,即便是上了天,入了地,为了我跟孩子,你也敢跟老天斗上一斗!这一次,你可真让我失望!”
潘启文猛然低头,虔诚地吻上了她的额头,喃喃地道:“对不起,是我又犯浑了!”
说完,他的唇向下滑去,一口噙上了她的唇,他不敢孟浪,只轻轻柔柔地地吮吻着她,半晌,他抬起头来,眼神晶亮,咧了嘴,吸吸鼻子,笑:“蕴仪,我再混世魔王,即便真的上了天、入了地,还是翻不出你的掌心!”
叶蕴仪撇撇嘴,狠狠地揪了一把他的耳朵,轻哼着道:“我本来还说,等日本人的事过去,我跟孩子就搬回芳华苑去的,现在么……”
潘启文一把抱住了她,胡乱地叫道:“蕴仪、好妞!别介啊,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叶蕴仪口中咝地一声,呻吟着叫道:“疼!”
潘启文慌不迭地放开她,手忙脚乱地检查起来:“哪里疼?是不是我压着胳膊了?”
叶蕴仪小心地看了看胳膊,隐去脸上疼痛的表情,咬牙切齿地道:“心里疼!你这个浑人!”
潘启文的唇轻轻地贴上了她胳膊的伤处,轻声道:“蕴仪,我不要你跟孩子就这样搬回芳华苑,等日本人的事一了,我要风风光光地,重新迎你进门!”
因着药物的作用,叶蕴仪再次沉沉睡去,潘启文趴在床边,轻轻摩挲着她的眉眼,痴痴地看了她半晌,直到这半蹲半趴的姿势令到他腿发麻,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潘启文嘴边挂着一个抑不住的笑意,从兜里掏出烟来,放在鼻下闻了闻,轻手轻脚地开了门,走出去,反身轻轻关上房门。一转身,却发现黎昕倚墙而立,一脸铁青。
一丝不安在潘启文心中升起,他甚至不敢问,只以询问的眼光看向黎昕,黎昕默默地将手中的文件夹递给他。看到那办公常用的文件夹,潘启文心里莫名一松,嘴上不由问道:“公事?”
黎昕低了头,没有答话。潘启文的手虚空一抓,用力地捏了捏,这才翻开那夹子。只一眼,他的瞳孔便急剧收缩,呼吸也急促起来。
文件夹里是一张没有刊头报名的小报,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昨天日领馆门口,叶蕴仪为岩井英一挡子弹的过程,还配发了照片。
小报大肆渲染了陆念迅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并指出井上村一当众承认罪行,强烈呼吁释放陆念迅,惩处凶手井上村一。
这张小报还将当初潘启文发表的离婚声明也原原本本地印了上去,直指叶蕴仪水性扬花,明明当初已抛夫离开,如今却又受人唆使,不知廉耻地再次迷惑潘天一,令到本对日本人痛恨不已的潘天一,竟然转为保护日本人。
报上还大副刊登出偷拍的叶蕴仪在东磨街宅子门口送方宗尧的照片、潘启文抱着孩子与叶蕴仪一起进入宅子的照片,以及前几天方宗尧与潘启文召开记者会时握手微笑的照片,用极具嘲讽的文字,暗指潘天一与方宗尧共用一个女人。
潘启文五指一拢,那张小报被捏成了一团,他对黎昕斩钉截铁却又简简单单地说了几个字:“查!抓人!销毁!”他瞥了一眼病房的方向,眼中布满了绝望的灰霾,他低了声道:“先瞒住,切记不可让她知道!”
黎昕点点头,叹口气道:“已经安排下去了,只是这种无名无头的小报最是难查,尤其是他们在街头到处张贴散发,也没个数,恐怕很难瞒啊!”
潘启文冷笑一声:“再去审上次我们抓的那几个南京派过来刺杀的人!哼,受人唆使,受谁唆使?不就是指的方宗尧父子吗?”
黎昕恍然大悟般:“是,我这就去!”
潘启文步履沉沉地走到大门外,无力地靠在柱头上,掏出打火机来点烟。他的手有些抑不住地发抖,打了几次,才打着火,刚将烟头凑上去,一阵风吹来,将那火又吹熄了。“混蛋!”潘启文狠狠地将打火机往地上一摔,那银色的小方块刹那间四分五裂。
他怔忡地看着那小碎片处出现的一双黑色皮鞋,视线往上,映入眼帘的竟一只捏着与刚刚那张一模一样的小报的手,他猛然抬头,却是蕴杰,正沉了脸站在他面前。身旁的黎黛正一脸惶恐地看看蕴杰,又看看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蕴杰瞥了潘启文一眼,没有吭声,只将那早已皱皱巴巴的小报捏紧了,抬脚往里要走。
“蕴杰!”擦身而过之际,潘启文一反手抓住了蕴杰的胳膊,他没有回头,只哑声道:“我不是想瞒她,只是她现在身子虚弱,受不得这些。”
蕴杰驻了足,并未出声。半晌,他缓缓摊开手,将捏在那报纸中间的一张电报单抽了出来,递给潘启文。潘启文展开一看,那上面赫然写着:“爷爷病重,速带孩子回美国!”
潘启文心里一下凉透,爷爷病重,他没有任何理由阻着她和孩子去美国,还偏偏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她要离开!
他闭了闭眼,无力地道:“蕴杰,再快,也要等她出院了才能走。现在告诉她爷爷的事,并无好处!”
蕴杰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问道:“医生有没有说,她什么时间可以出院?”
潘启文黯然道:“五天!”
蕴杰转了身,点点头,沉声道:“我会买五天后去上海的火车票,还有上海出发的船票。”
潘启文缓缓地松开了蕴杰的手,转身向病房内走去。却听背后蕴杰轻声道:“小报的事,我不会替你瞒着!”
潘启文顿下脚步,回头看向蕴杰,眼中尽是绝望与恳求:“可不可以,你们离开后,再告诉她?”
五天的时间里,除了在叶蕴仪睡着后偶尔出去抽抽烟,潘启文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他将前来照顾的妈子统统赶走,亲手打理着叶蕴仪的一切。喂她吃饭、为她擦身。她醒着的时候,陪着她絮絮叨叨地说话。
晚上,他将病房内另一张床与她的拼在一起,晚晚搂着她入睡,只小心地避开她那只受伤的胳膊。
“蕴仪,我听说,美国有一种可以装碳的暖炉,可以保持通宵都是暖和的,回头,让蕴杰给你买几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冷!”出院的头一天晚上,潘启文将叶蕴仪的手揣在自己怀中,搂着她,轻声地说着话。
叶蕴仪的头贴在他胸口,将手伸进他衣内去,在他胸口抚了抚,轻笑一声:“你可不就是个大暖炉?还冒着热气儿呢,整个被窝里都是暖的!”
潘启文眼中泛起一层雾气,他用了力地眨眼,将那雾气逼了回去,淡声地笑:“是,我可不就是个大暖炉?只是,我要是出差或打仗去了,你还可以让小风或小宇跟你一起睡啊,也暖和。”
叶蕴仪轻轻叹口气:“小风自己还需要暖瓶呢,小宇是男孩子,也懂事了,总不能老跟着我睡。”
潘启文的声音有些僵硬起来:“他们两个,国文一定要学好,可千万别整成个假洋鬼子,忘了本。”
叶蕴仪戳戳他,嗔道:“这又不是在美国!过了年,就送他们进学堂去,国文还是学校老师教得好,外文我在家里教他们就好。”
潘启文心里一抽,又淡淡地道:“小风是女孩子,惯着些没事,小宇,他已经很懂事了,你也别对他太严。”
叶蕴仪笑了笑:“还说呢,自从你跟小宇说了那啥分担责任的话来以后,小宇现在动不动就跟我说‘有爸爸呢!我还小!’”
潘启文眸中的那一层灰白缓缓地撕裂开来,喉中哽痛,再也说不出话来。
半晌没有听到回答,叶蕴仪不由抬起头来看向潘启文,当看到他那几近扭曲的面容时,她不由一惊:“启文,你怎么了?”
潘启文拢了拳放到唇边,轻咳一声,勉强地挂起一个笑来,粗着嗓子道:“可能受凉了,喉咙有点痛!”
叶蕴仪立刻伸手探向他的额头,末了,松出一口气:“还好没发烧!”她一脸心疼地看向他:“你看你,这几天又瘦了,多的是人来照顾我,何必要什么事都你自己动手?”
潘启文将她的头摁在自己胸前,不让她看到自己已然潮红了的眼,下巴在她头顶贪婪地蹭了蹭,哽声道:“这几年,你生孩子,又月月生病,我都没照顾过你,就这么伺候一回,算什么?”他生生抑下心底里那句:“以后,只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的,他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便连黎昕兄妹,也都没有再劝他,只是以那种悲悯的眼光,看着他。而方宗尧,也只是叹了口气:“让她先离开一段时间,也好!”
他却知道,她这一离开,或许,他就真的再没有机会了。可是,这一次,他便连争取的勇气也没有了,一次又一次,是人,都会伤,他宁愿自欺欺人地过上那么几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也不愿看到她眼中的憎恨与绝望!所以,他才会请求蕴杰,在他们离开后再告诉她。
叶蕴仪只道他还为以前的事内疚,心里一阵发疼,她直起身来,径直用自己的唇堵上了他的嘴,却在潘启文来势汹汹的掠夺中,品尝到了那一分咸涩,她心里一慌,想要安慰他,却再推不开他那几近疯狂的唇舌,她只得揽紧了他的脖子,手轻抚上他的背,想以此来给他一丝的慰藉。
东磨街宅子门口,游行示威的人群刚刚被强制驱散,一辆黑色轿车便停了下来,潘启文小心翼翼地扶着吊着胳膊的叶蕴仪下了车,口中叫道:“小风,离妈妈的手远点儿!”
晚饭是一家四口一起吃的,潘启文将头埋在碗中,却一口也没吃下去,两只眼露在外面,痴痴地看着那一大两小,小风一双灵动的大眼忽闪着,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小宇一丝不苟地吃着饭,时不时一脸沉静地应对着小风,叶蕴仪自己吃两口,再给孩子们夹着菜,微笑的脸上,温柔与宠溺尽现。
这一刻,潘启文突然便明白了那以前总觉矫情的“肝肠寸断”是什么感觉,这是他的女人和孩子呵!为什么,命运要如此残忍,明明他们之间的误会,已被重重解开,明明那么难,她也已原谅了他,一步步再次向他靠近,为什么偏偏要在他以为幸福已唾手可得之时,再一刀斩断他们之间那刚刚才建立起来的,本便脆弱的牵绊!
房门被推开,蕴杰神情复杂地看了看潘启文,径直将手中捏着的电报递给叶蕴仪,叶蕴仪打开电报一看,立刻捂了嘴,眼泪直往下掉,蕴杰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明天的火车!”
叶蕴仪突然便明白了潘启文这几天来的不安和反常。
那个晚上,在与他的彻夜欢爱中,她一遍遍地亲吻着他,向他保证:“等我回来!”
他也一遍遍地回答着:“好,我等你!”
火车离开前,他紧紧地拥着她,哽咽着道:“蕴仪,你记得,我会在这里等着你,一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