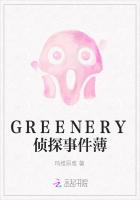“外来闲杂人员禁止进入本大楼!”我的脑袋尽管被怒气包围着,但理智还有一点点清醒,对方估摸着是白撞,若生了什么变故,我必须叫来保安。对了,鼻腔缠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腻香,必定从这女人身上传来。
说来也奇怪了,这个绿衣服的女人竟然无视我眼光的进逼,一副“我很轻松、随意”的状态,好像我的怀疑全然多余,她溜了溜眼珠,说:“天天看别人擦桌子的滋味怎么样?科长颐指气使,工资却高了你们好几倍,可甘心?”咯噔,我心里猛地往后退却小半步,但见这个女人掸了掸衣领,仿佛遇到什么脏东西沾上了她的衣服,而事实什么都没有。一个不熟悉我们公司、甚至本部门的人,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难道真如金庸书中所谓的“扫地僧”?就怕她来头不小,得罪不起。
但是,主任反复擦桌子的样子再次浮现,深深感觉科长的手段有如一道紧箍咒,横加诸我身,下意识微微探身,不失礼貌地问:“你是哪个部门的前辈?我似乎没有见过您。”那人“呵呵”一笑,淡然回了我:“我亲眼目睹你的主任和科长怎样从普通职工爬到今天的地位,至于科长对主任干了什么事情,我更一清二楚。倒用起个‘您’字了?小姑娘,我可担当不起啊,你一个研究生干初中生都能干的活儿,才叫担当得起!”
我多么想反驳她,大鹏尚未展翅,她凭什么贬低我!回心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人不可貌相”,怕她是哪个部门的老资格,知道公司许多内幕呢。我放软口气:“大姐,那您有何指教?”这下,对方似乎感到满意了,悠悠然说;“我哪能教你做事?只跟你说了,开了这道门,里面有让你吃惊的玩意儿。看了以后愿不愿意向旁人提起,悉随尊便了。”
我咽了咽口水,“秘密”两字吊胃口呢,说不定掌握了大人物的把柄,万一因此遭遇上麻烦事,又……那女人靠近我的脸庞,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僵硬的表情,一字一句像锤子敲打着我心脏:“你要是不愿意看,我也不勉强,一辈子做小喽啰,以后受挤压也无所谓,这样的日子你一转身就可以过去了。假如那些事情带着肮脏色彩,你有权知道的,不是吗?”我当时脑袋陷入短暂混沌中,却努力表现出从容:“好吧,请大姐为我指点迷津、揭个秘。当然,希望你明白揭秘也会有风险。”——我决定听从内心呼唤,如果真有值得检举的污泥井底,我今天的所作所为,就值得肯定的。至于那个女人的用心,我小心一点就是了。
那女人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插入锁眼上,左扭扭、右转转,一切看来顺理成章——我更相信她来自公司哪个不知名的角落,可能被我们科科长或科长那一派系排斥,今天的举动出于报复之意。就在我思想没有准备的当儿,她伸出瘦长的五指,顺势拉了我进去,一个趄趔、好不容易我才站稳,睁眼看到四周有序地摆着一排排架子,上面置放着各种箱子。那女人熟练地来回走了一下,若有所指地说:
“这里的东西表面存放着公司弃置不用的物品。仔细搜搜,包你耳目一新……比如嘛,”她想了想,挑中我左边其中一个架子最底层搁着的黑色纸箱。我慌忙吐了一句:“呃……大姐这……”,“不太好”的三个字已经被她堵住:“不要‘大姐’、‘大姐’的叫,我**仁,你可以叫我‘春姐’。就一个箱子而已,不值得你大惊小怪,架上还有许多。”说话间,她已经翻开那个纸箱,里面的物件渐次展现。
诚如春姐所说,箱子上边的东西的确毫不起眼,都是非常老旧的鼠标、数据线等等,即便收破烂的到来,怕对此也不屑一顾,因为它们实在太普通。只要往下继续翻,一点点地变化着,先是丝绒包着的名表,靠下放着一只纯金打造的梅花鹿摆件……这些东西无声地告诉我它们来路不正,否则何必藏在这个生人不得接近的小室内?
春姐顺手拣了件簪子,吹了吹它上面微末的纤尘,往我怀里塞,并凑到我耳边:“姑娘这些东西全是某些人献给你们科长,还有他那个上司的宝物。看,这个簪子可是古董呢!”我低头观察起人生首次碰到的古董,忽然手腕感到一阵尖利的痛,这才反应过来——春姐用小刀划过我的手腕背上的皮肤,即时出现长长的血痕。我吓得想大呼救命,春姐已用闪电般的速度,把沾了我的血的刀往簪子上擦去。
说时迟、那时快,我的身体变得轻飘飘,意志仿佛不再受到控制,周遭越来越陌生,陷入白茫茫的一片,我还是我吗?难道一刀就使我出血过多而休克?我开始后悔自己初始的任性,听信一个所谓本公司的陌生人指使了。但问题是……我的四肢根本无法动、喉头也无法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