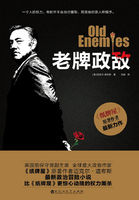一大早就听到外面“铛铛咣”抑扬顿挫的架子鼓声音,我迷迷糊糊睁了下眼,看见蓝布帘后面依然是普蓝色的天——撑死就五点。我翻了个身把棉被往上拉,整个遮住头打算继续睡,可那时而舒缓时而狂乱的鼓声还是一下一下钻进我耳朵,闭着眼睛伸出手把旁边的被子也拽过来扔到头上,造成的结果是险些把自己闷死。
“绍凯!”我坐起来把床边一把椅子推倒,巨大的落地声后是完全纯粹的安静,鼓声如预料般戛然而止。我翻了个白眼又向后倒回枕头,死死闭上眼睛。
隐约听到门被推开,有脚步声慢慢靠近,一直到床边停下。
“又吵醒你啦?”看我还是闭着眼睛不动,那个人俯身下来两条胳膊撑在我头两边,“一会儿有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动了动,把头转正张开眼睛看着正对着我脸的那个人,一头火红火红的短发,上面精心用发蜡抓得很好看,更显得脸的线条硬朗而分明。
“我知道,我要是因为这个生气八百年前就气死了。”
“要不然你怎么是我绍凯的老婆呢,”他在床边坐下,伸手掐我的脸,“不过你刚才那一下真把阿毛吓的够呛,他还以为你真急了呢。还睡么?你要还睡我们就不练了。”
“睡什么睡,醒都醒了,”我伸出胳膊勾住绍凯的脖子,他就顺势揽我坐起来,“你们几点回来?”
“没准,估计得晚上了,你自己想办法吃饭,别等我们。”
“哦。”除了这个字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绍凯他们不到七点就走了,我送他到门口,他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我。每次都是这样,自己连吃饭钱都不留。我踮起脚尖亲他脸一下,“早点回来啊。”然后阿毛和小哲在后面起哄似的吹起了口哨,绍凯笑着回头冲他们挥拳头。
这是我和绍凯在一起的第二年末。
一个人走回院子,离城冬天的天空像是死鱼混沌的眼珠,即使天晴也露不出原有的蓝色。院中唯一的一棵树在不久前的一场雪过后,掉光了上面勉强连着的细小枯叶,只剩下枝干孤零零带着年老的裂痕和一匝又一匝的年轮,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来临。我走进绍凯他们盛放乐器,用来排练的屋子,电贝司已经拿走,只留下一把木吉他稳稳当当摆在架子上,一组敲坏了的架子鼓挨墙放着,蒙了薄薄的灰。拉过把凳子坐下拿起那把木吉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绍凯平时看起来一点也不灵活的手弹起吉他出神入化,而我空长着被他说“天生弹琴的料”的细长手指,却在他手把手教了好久以后,依旧只会弹几段简单的和弦。他们只要一出去有演出我就要一个人待上一整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发呆,经常回过神天已经暗了连饭都忘记吃。来离城的两年并没有让我熟悉它,我无法像从前一样清楚哪里哪里衣服很便宜,哪里哪里馄饨很好吃,我总觉得离城始终用一种警惕的陌生眼光盯着我,好像随时都会请我离开。所以我只能抓着绍凯,我在这里唯一的拥有。
说起绍凯,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比我大两岁的他确实给了我无比厚重的安定感,但有些时候他又更像是个孩子。我总是说他心智不健全,或者叫他大小孩,后来有一次他特认真的问了我一句:“到底是大还是小啊?”我一边笑得要死一边揉他那头红色的头发。无法否认的是,我喜欢看绍凯笑,和他平时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有一种凛冽的——天真,尤其是不好意思或者难过时他笑得愈发幌眼。我知道这样的笑容只会对我,阿毛,小哲这样的家人才会有,在外面的绍凯总是摆出那种坚强的,不可一世的样子。人们把他这样的人定了统称,不良少年或不良青年。
但我就是和这样的他在一起,因为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有血有肉,有一颗滚烫的心。
事实上,我和绍凯没少吵过架,为了生活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再和好。我们两个都是脾气上来就不管不顾的人,他本来就倔得八匹马拉不回,没想到我更胜一筹,用他的话说就是:“八匹马都去拉你都不够,最后还得加上我。”冷战的时候我一个人睡在屋里,他去睡琴房,冬天琴房没生炉子特别冷。有一次我半夜睡不着突然想去琴房看看他,心里想就服一回软把他哄回来,结果刚一拉开门就看见他坐在门口台阶上不要命似的抽烟,红色的光点在黑夜里剧烈的明明灭灭,地上已经扔了快十截烟头。听到门的声响绍凯转回头看我,对视了几秒后他把手上的烟扔到地上踩灭跑过来抱我,头垂在我肩膀上,喉咙里仿佛还有烟没吐出来一样哑哑地说:“我睡不着,想你了。”我抬起手摸他的脸,冰凉冰凉的,也不知道他在这坐了多久。“绍凯,你答应我两件事我就不生气,第一,以后不许抽那么多烟,第二,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
在听到他“嗯”了一声后,我把脸埋进他怀里,第一次觉得极其不喜欢的烟味也能够让我安心。只是我们都清楚这种时候的答应不具备长久效应,就如同如胶似漆时候的“我爱你”和吵闹分家时候的“我恨你”总是出自同一张嘴。烟他确实少抽了,可架还是照吵不误,所幸的是不至于影响感情。有时候阿毛和小哲会在其中捣捣乱,半夜把绍凯从琴房或是他们屋里推出来,然后大声叫我,我强忍着笑透过门上的窗子看绍凯站在院子中央一副小孩子受委屈的表情。
就这样一直到那一次,我们吵得最严重的一次。
事情的起因是我瞒着绍凯去一间酒吧唱了一晚上歌,我没想到他会提前回家,因为他对我说他要天亮才回来。我推开门就看见绍凯阴着一张脸,冷冰冰地看着我。我知道夜不归宿这件事很严重,但满心以为解释清楚就没事了,没想到他看见我递过去的钱并听到我去干什么后,猛的站起来,提高声调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养不起你?”
“绍凯……你别激动,听我说,”我深吸了一口气过去拉他,却发现他身体僵硬的要命,“我不过是唱歌而已啊,我没觉得你养不起我,反而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让你养下去了,懂么?你知道我每天看着你们出去辛苦为了赚那一点钱,甚至受伤回来,我却在这待着什么都不做,我心里多难受么?我们生活需要钱,你们乐器保养需要钱,假如这里拆掉,我们需要另租房子,多赚一点没什么错。我们真的需要钱,不是吗?”
“是,但那不是你的事,你要再敢去,我就去砸了那间酒吧,你信不信?”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火气也上来了,“我要是为钱我何必跟你!”
“你要是后悔随时可以走,”绍凯走到门前,把门往外一推,“我他妈拦你一下就不是人!”
“呵,”我摇摇头突然笑出来,站起身走到门口,转头看着绍凯说,“这是你说的,绍凯,算我看错人。”然后头也不回走出了院子。
其实出来了也不知道能去哪儿,一个人在周围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一家快餐店时走进去买了个汉堡,交钱的瞬间突然就想起了在离城下火车的那个除夕夜,满地泥泞和冰凌,感觉到的是化雪时彻骨的寒冷,在无人的快餐厅绍凯买汉堡给我吃,然后在一片冰天雪地里解开外套将我拥进去,我能够感觉出他明明和我一样充满不安和无措,但他还是轻轻对我说:“别怕,我在。”
可能是我的表情有点怪,收银小姐手里举着要找我的零钱迟迟没动,“怎么了?”我对她笑,这一来她眼神更加困惑,把钱和收据交给我,然后又添了一叠面巾纸。“小姐,你没事吧,你怎么哭了?”我抬起手抹了一把脸,果然有泪水——丢人。我继续笑,一边笑一边擦眼泪。
整整一天都在公园的长椅上消磨掉,汉堡吃完,包装纸揉成团放在身边。公园里的人都是闲适的,心情愉悦的。依偎的情侣,活动手脚的老人,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看着天出神。一直到夜幕降临,公园要关闭,我才发现路灯下只剩下我自己。
其实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争吵,而是争吵背后隐藏着的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可即便这样还是向回去的方向走,不愿也不敢走太远,因为我很清楚,一旦迷失方向黑暗就会变成骇人的野兽。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家酒吧,站在门口就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音乐声,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进去。就在我转身刚走两步时,身后突然传出巨大的声响,好像有什么撞到门上,下意识地回过头,看见酒吧的三个保安在踢打地上的一个人。周围路过的人都一边看一边闪得远远地走,生怕惹上麻烦,我皱了下眉头,却深知自己管不了。那三个人美其名为保安,实则是负责看场,专用暴力对付闹事砸场的人。眼光在收回前自然的向下移,却在撞到地上那个蜷着身子,用胳膊护住脸的人时,猛的定住。
“绍凯!”那个红发少年不是他是谁。
突然听到喊声那三个人停了手不明所以的寻找声音出处,绍凯有些不敢置信的慢慢将胳膊从脸上移开,在看见我的那一刻突然就笑出来,可能是牵动了伤口,又迅速拧了一下眉头。“你站那别动,等我。”他冲我说了一句,我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看着绍凯有些摇晃的从地上站起来,然后……一拳挥到刚才打他的一个人脸上,那个人当即就摔到地上。这一下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了,包括我。绍凯跑过来拉我,说:“快跑啊!”
“你……你……”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最后拐进一条小胡同,看了看后面的人没有追上来,我甩掉绍凯拉着我的手,扶着膝盖大口喘气,“你还真去砸场啊你?!”
绍凯好像支撑不住的样子,干脆直接坐到了地上,头向后倚着墙壁,半天说不出来话。
我转身想去大路上打一辆车,他却好像以为我要走突然站起来想要抓住我,我看他身体晃了晃就要站不稳似的赶紧回身撑住他。“喂……你瞎动什么啊?”182的大个子现在全要我来撑,我只能紧紧抱着他,但感觉却更像是他把我整个裹进怀里。有好一会儿我只能听到绍凯在耳边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渐渐才终于有小声的话传进耳朵:“死丫头……你这一天去哪儿了……我们找你都快找疯了你知道吗?!”
“我就在附近转转啊……”我鼻子嘴贴着他的胸口说话声音瓮声瓮气,“是你找我找疯了吧……”
“知道还说,我以为你和我赌气又去那种地方,可他们不让我去后面找你。要是知道你不在那儿我早还手了……一群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