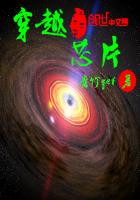21
鱼儿离家又快一年了。玉枝想,闺女这次恐怕是不会回来了。鱼儿在外面能干啥呢?她确实想不明白。但有一点她是坚信的:鱼儿跟过去的鱼儿不一样了。那次回来后,她就看出来闺女已经不是过去的闺女了,比过去能耐多了。
唉,都说儿大不由爷,闺女大了也由不了娘呀。再说,这个家不要说是鱼儿,就是她自己也不想待下去了。这些天玉枝一直都在想,鱼儿出去也好,在外面打工也不是啥坏事,说不定就不回来了,就有好日子过了呢。
此时,鱼儿正在另一个城市里成了真正的按摩女。
鱼儿从大厦的旋转门一露脸,眼就被斜射过来的白光扎了一下,又扎了一下。她连忙抬起纤细而苍白的右手,并拢着五指,罩在左眉的上方。
有多少天没有见阳光了,鱼儿一时还真计算不起来呢。眼下,她只觉得这省城的太阳与自己村上的太阳很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光太白、太扎眼,寡得很,有一种呛人的汽油味儿、灰尘味儿。可这也比大厦里脂粉与男女身体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强多了,但绝没有自己村上的太阳光好。鱼儿想。
自己村上的阳光呢,像三婶嘴里的门牙,白的上面浮了一层薄薄的雅黄渍,像娘给自己扎辫子时吹在发梢上的气,柔柔的。鱼儿走下门前的台阶,用鼻子长吸了一口气,她再次感受到了天上白光的存在。这光就是与村上的阳光不一样,村上的阳光有一种细细的甜腻味儿,阴雨天就是一种草腥味了,鱼儿有点闻不惯的。这城市的阳光味儿,鱼儿更闻不惯,这是她决定出来前没有想过的。不然,昨天老杜再咋说,她也不一定准备走出大厦门的,更不要说到街上了。
鱼儿走在街上轻飘飘的,就感觉到自己像街上的布标语,在风中摆过来摆过去。但她心里却很扎实,“你明天出去见见阳光吧”,这句话像铁柱子一样立住了鱼儿。鱼儿老在想,人的一句话咋就比家里的牛还有力量呢,能拉着人向前走。
昨晚快十一点了,客人却出奇地少,她与十几个姐妹都挤坐在发着白光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就在休息大厅的旁边,过来休息的客人都能瞅见她们。小房间的门从来都没有关过,姐妹们没有活做就很浮浪地笑着、闹着,春儿和小莉正比着大腿的粗细。当然,她们主要是想引起过往客人的注意。
这时,一个胖胖的人向门前走来,眼只向小房间一瞄,就扭头走了过去。鱼儿什么也没想,就从小房间里挤了出来,她想问一下刚才那人做不做按摩。她刚出门就听春儿说:“傻,眼浑着呢!”鱼儿也真的没有想这人做不做,但她就是跟在了他的身后。这人躺倒后,鱼儿就站在了他的前面:先生,做做脚摩吧。她声音很低,好像自己也没有听见,她就又问了一声。这人折起了半个身子,说:“不想做,我想休息一会儿。”鱼儿的身子向前倾了一下,笑笑说:“谁叫咱是老乡呢,大哥,照顾俺一次吧。”
这当儿,又来了一个光着背的瘦男人,眼却发着亮光。他向鱼儿瞅了一眼:“小妞不错的呀,老杜做一次吧。”说罢,又肋骨一动一动地喊,“上茶,再来个小姐。”
鱼儿坐在这个叫老杜的男人的脚前,心里甜滋滋的,谁是傻,你才傻呢,人家不是做了吗!她两只手先握了一下老杜的脚,轻轻地在脚上拂了个遍,她觉着老杜一颤,就细细地说:“先生咋了?”老杜笑笑,虽然没有出声,鱼儿也是知道他笑了,她看到了他那嘴白牙了。鱼儿的手就更柔了,她往脚上抹大宝的时候,手指肚碰了一下手中的脚心,老杜嘴又一白,接着说:“你哪县的?”鱼儿就笑笑,捏着老杜的小脚趾说:“我不说,反正咱是老乡。”
这当儿,鱼儿就与老杜一声慢一声紧地说起了话。老杜也问鱼儿一些诸如在这里收入情况的事,中间也与旁边的瘦男人搭着话。他与瘦男人搭话的时候,鱼儿也没有闲住,她就与手中的脚说:“你看你多周正呀,软软的,一摸俺就知道不是出力的脚。”她一遍一遍地说着,竟出了声。老杜就又笑了,这次不仅脸上一白,而且出了声:“姑娘你说啥呢?”
鱼儿没有吱声,她是不好吱声的,自己说了什么,她也不知道。老杜还认真起来了,追问着:“你说啥周正呢?”鱼儿这才知道刚才自己心里的话出了声,笑笑,还是没有回答,她是想用笑回答的。然而,老杜也真是,竟折起了身子,又问了一遍。旁边躺着的那个瘦男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折起了身子说:“小姐好好地做啊,他可是我请来的客人,他不舒服我不埋单的!”
鱼儿突然觉得很委屈,有点生气地说:“我说你的脚长得周正,不是出力的脚!”折着身子的两个人都软了下去,相对着笑了笑,声音很大的。鱼儿就觉得更委屈了,真是,脚能摸能捏不能说不能想呀!
鱼儿一生气,做起活来手上的力就不匀了。手中的脚猛地一颤,她心里就一紧,赶忙用手心在脚面上拂了拂,像娘拂自己的头一样,心里也是娘曾说的话,别怕,别怕呀。鱼儿觉得这人不一定会满意的,可她提出要给他再做腿摩时,他只是向右边的瘦男人看了看,然后就答应了下来。鱼儿当然很高兴了,做起活来一下连一下的,像在跳舞。鱼儿与老杜更投机了,一句接一句地说着话。
说的什么呢?鱼儿记不住,但她今天分明很高兴,老杜不像其他人一样说些让她脸红的话,而说的多是家乡的事儿。有半年,鱼儿没有这样用家乡话跟人说话了,更不说家里的家长里短的。鱼儿真的太高兴了,说着说着,自己的手也开始说话了,她的手是与他的腿在说话,一句一句地应着,很合拍的。
腿摩做完的时候,鱼儿的心里话还没有说完。她就说:“先生,你干脆做一套吧。”说着她就站了起来,似乎是老杜已经同意了。老杜说:“太晚了,想休息了。”
鱼儿就声音变小了:“我给你做,你不是能更好地休息吗?”老杜也没有再说什么,就随着鱼儿,向里边的单间走去。
鱼儿给老杜踩背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了。她想眼前的老杜,这人咋就与其他人不一样呢?她想起了许明,心里美美地笑了,这世上的好人咋都让我摊上了呢?两个多小时了,竟没动自己一指头。鱼儿真的觉得对不起老杜。人家花两百八十元钱呢,连摸都没摸自己一下,与其他人相比,真是个好人呢。
鱼儿心里这样想,手就慢慢地向男人舒服的地方滑去,手是听心的话的。老杜两腿一夹,说话了:“姑娘你别胡想啊。”鱼儿就生气地说:“我不是做那事的,可我也会让你高兴的,不然我对不住你。”
老杜就说:“搁到其他天我做的,今天不。”鱼儿就停了下来。
按摩头时,鱼儿仍是觉得对不起这人,对不起这人的两百八十元钱,就让自己的前胸碰这人的脸。虽然她的前胸并不大而且又还有点硬,但老杜还是感觉到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鱼儿的前胸感觉到了那气的力量,竟被这气吸了过去,她的那两个不太大的硬乳压在了老杜脸上。老杜依然吸着气,当鱼儿的脸也被这气吸下去的时候,老杜猛地坐了起来:“我该走了。”
鱼儿的眼里一下子湿了,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其实,那个瘦男人早把单埋过了。鱼儿送这个被称作老杜的人到吧台时,老杜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沓发着响声的票子,递给了鱼儿。鱼儿想说我不要,她今天真想这样说的,但她就是发不了声来。
自从到这儿,她就改用手说话了。老杜向鱼儿笑笑,握了鱼儿送过来的手。老杜突然觉着手中的手太细了,就说:“明天就出去见见阳光吧!”鱼儿没有吱声,但她已用手答应了老杜。老杜也靠手听到了,又说,“我信你的!”
22
坐在阶梯教室里的华子,把手中的书合上又打开,打开又合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书就不耐烦地发出哗哗的声响。听到书的抗议,华子心里更烦了,索性站起身子,用胳膊和肋骨夹着它,恨恨的,脚步很重地走了出来。
华子把左身子靠在操场旁边的双杠上,软软的,可他一抬眼,腿竟不由自主地硬了起来。原来是前方的白光斜照在了他的眼上。这感觉咋这么熟悉,但又这样陌生,是哪里有过这种感觉呢?华子脑海里也和眼前的光一样,白白的。
华子终于想起来了,那是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有着白光的下午,光白白的,有些刺眼,人的身子也软软的,只不过那是在县一中墙外的沟坡上。华子的心一下子紧了。那个下午,曾一遍遍地在他心里生长着、生长着,每次都把他的胸膛塞得实实的,他真担心胸膛会炸开,但那种胀的感觉却十分美好。
怎么个美好法呢,华子还真说不清楚,有时是甜甜的带有笑声,有时是那种缺氧后的感觉,心跳得厉害,脸也红扑扑的,有时也是一种疼痛后的快感。可最让华子难忘的那种感觉,却是浑身上下都发热,有想拥着鱼儿的那种想,刻骨的想。
想什么呢,华子更是说不明白了。与鱼儿拥在一起的感觉很复杂,软软的、甜甜的、香香的、痒痒的、酥酥的、麻麻的,心里就像小蜜蜂在爬,千百只小蜜蜂在爬,但所有这些都是肉与肉贴在一起才能产生的。华子总是这样坚定地想,从没有动摇过这种想法。
有了这种想法后,华子心里就后怕,怕失去这种感觉,失去对这种感觉的记忆。华子这样想不是没有他的理由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与鱼儿已经十几次地拥在一起了,但所有的感觉都没有那次好,甚至加起来也没有那一次好呢。这怎么办?
华子有点儿焦急,他想寻找一种使这感觉永驻的办法。但这种焦急又不能与别人说,只能是自己心中的秘密。秘密就是一个小刺猬,一旦钻你心里去,你就不得安宁了,华子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他从报上看到了克隆技术,他暗喜了一段时间,他坚信只要人能克隆,人的感觉也一定能克隆的。
那是前年春天的下午。这个春天的下午,华子正坐在高二(1)班教室的第一排。坐在第一排的华子正聚精会神地听语文老师讲课。讲课的语文老师正在忘我的情境中。“华子,你出来一趟。”突然,一个姑娘特有的甜音,直直地钻进了华子的耳里,也钻进全班四十一名同学的耳朵里,当然也钻进老师的耳朵里,而且这声音在老师的耳朵里钻得还更深。要不,语文老师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声音:“快出去!”华子没有来得及想,也不敢想,就按老师的命令走出了教室。
走出教室的华子像光着身子一样,头也不抬地向学校大门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向大门走去,而且到了门口也不停,向西一拐继续向前走。鱼儿傻了,但她只有在后头追,边追边骂,这人、这人真是!到了校外的沟坡上,华子仍然像挣断了缰绳的牛向前走。鱼儿真的生气了:“你这人!你疯了呀!”华子听到鱼儿带有哭声的怒吼,才停了下来,停下了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鱼儿几步走到他的跟前:“我这次回来,家都不打算回了,只是来向你告别的,我丢你的人了,咋的!”
华子这才转过那张红红的脸:“鱼儿,你、你这半年多又到哪里去了!”鱼儿没有再理华子,一屁股坐在了沟坡的草地上。她确实有点儿累了,但更多的是气。人气的时候是特别有劲头的,但这种劲头过后,就会特别的乏。
照在脸上的、身上的片片阳光,不再那么白了,也不再那么寡了,说红就红了起来,说酽也酽了起来。华子和鱼儿都感觉到了那种柔柔的、暖暖的、和着草芽儿的气味,那是他们村边小河边的气味。回到村边的小河,华子和鱼儿就又回到了十几年前。这时鱼儿和华子的心是舒展的,像春天空中飞舞的蒲公英小白花,像夏天池塘里盛开的荷花。两朵花就这样并排着在空中飞,在水中漂,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甜蜜。
鱼儿就是那朵蒲公英的小白花,在飞呀飞的。
眯着眼、靠在双杠上的华子,全身燥热,是那种生长着的燥热。他心里只有两个字:鱼儿!鱼儿!他想喊,但他喊不出声。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向前边的IC电话走去,他要打鱼儿的传呼!早已掉在地上的书,被风一吹,哗哗地唱着歌。
华子打鱼儿的传呼时,其实鱼儿已到了科大的门口了。
23
客人喜欢鱼儿,其他姐妹就不服气。
她鱼儿有什么吸引人的呀!眼是不小的,但没有媚气也没有水色;身子该长的没有长出来,胸也就是两个大西红柿那样吧;腰是细,却像刚扬花的玉米棵子一样;嘴呢,是长得有形有款的,是那种红红的嫩,可从没见她张开着,也就是一个冷天的花骨朵……简直就是发育不良啊!
姐妹们虽然这样想、这样骂,可客人却指着名要她。几乎每天都有专叫鱼儿的:我要81号那妹子!春儿每一次听到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小骚货,妖着呢,谁知道她有啥招啥式呀!”
鱼儿有时听到了装着听不到,扁扁嘴就算了。有时她也气,但她来得晚啊,哪地方不欺生呢?何况自己整天忙着,挣的钱比她们多。想到这些,鱼儿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怪。她很委屈,自己没碰谁惹谁,咋就得受骂呢?可她有时也觉得姐妹们骂得有理,来这里的就这么多人,都找我了,她们就挣不到钱了。可她不能不干呀,一是自己需要钱,而且这些男人来这里找你了,你能不做吗?
她弄不清是怨自己还是怨别人,反正她认准了一条:只要有人叫她,她就是要一下一下地做,一下一下地都做到点子上,才不能用哄骗客人的小伎俩哄人呢。碰碰男人、摸摸男人;让男人碰碰,让男人摸摸,这有啥呀?能有按着舒服吗?她有时自己也碰自己,也摸自己,是那种专门的碰和摸,她一点也感觉不到好在啥地方。她天天都在男人身上摸呀、捏呀、按呀,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一样呢,跟和着一团白面也差不到哪里去。每到这时她都暗自发笑,笑谁呢,笑那些傻男人,也笑自己。笑过之后就更坚定了她的想法,认认真真、一手一手地做,不讨巧、不骗人。
做得认真就累,这是不言自明的事。鱼儿觉得这正常,就像锄地一样,锄得深了,胳膊就酸就累。可这几天,鱼儿特别的累,啥原因,说不清,身上没来呀。越是想不明白越要想,鱼儿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认死理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娘老这样说她。有时想着想着就走神,有几位客人明显的没有先前对她满意了。她也想下劲按,可手软呀。手咋这么软了呢?她想怕不就是打华子打的吧。每想到这时她就后悔,那天打华子咋就用这么大的劲呢?她想起来就后怕,怕把华子打重了。
这些天华子也不呼她了,他生气了?鱼儿就在心里骂自己,手真狠,他是谁呀,他再错,说说不就好了,咋就打了呢?她想去找华子看看,一是没时间,再说了,她心里也矛盾,乡下的男人咋就没有城里的男人对女人好呢?鱼儿心里又长了一个秘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秘密。
那天鱼儿真的好高兴。她正站在学校门外,理着自己额前的头发,在这之前她先左右前后地拽了拽、抻了抻身上的衣服,她还很认真地瞅了瞅脚上的猩红皮鞋,要进大学校园呢,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呀。一切都觉得可以了,鱼儿心里仍在打鼓,一下一下,就像戏就要开场的那阵紧鼓,越来越厉害了,脸都红了呢。门岗会让自己进吗?进去能找到华子吗?鱼儿甚至都有点打退堂鼓了,正在这时,她突然感觉到大腿上的肉突突地跳了起来,原来是裤兜里的传呼机响了。